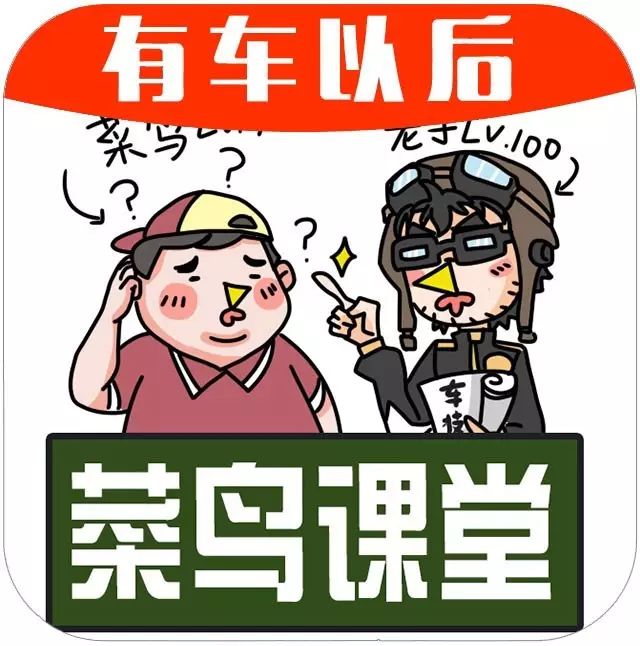本文作者
黄志雄是浙江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文章
使用政府会计实务人员发表的文献和报告作为数据源,从政府综合财务报告试编阶
段的问题提炼出会计基础问题,论述了政府财务报告编制中的困难和后续改革路径。
此外,进一步深入到财税体制和行政管理制度层面的缺陷,以支出责任与事权在我国地方政府上的矛盾为根源,试图将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嵌入到整个财政体制改革大环境中,保持政府财务会计的改革与财税体制改革步骤相协调,从根源上改进政府财务报告试编阶段体现的缺陷
与不足。

一线编制人员在具体涉及政府综合财务报告资产和负债的填列过程中主要出现了以下问题:
行政事业单位所辖资产缺乏必要监管,“经管资产”统计成为重大挑战;
公共基础设施数据采集存在相当大的难度,账面价值与折旧信息缺失;
资产项目填列随意片面,主观性较高;
政府债务内部划分不清晰,仅列示部分显性债务;
隐性债务规模庞大,确认核实困难;
政府间债务往来复杂不清晰,抵消不充分。
这些试编阶段反映出来的编制问题与中国现有财税体制背景密切相关,一味地夯实会计基础可能已经不是现阶段的主要问题。
在公共职能部门责任划分不清晰的基础上,试图通过政府财务会计准确可靠地计量政府运行成果与财务状况是不现实的。
二、
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基础薄弱根源辨析
(一)财政事权划分不清晰
1. 同一对象多项事权被分配给多个政府层级与部门,缺乏明确的核算责任主体。
核算责任主体不明确,尤其是省级以下事权划分不尽规范,各级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职责交叉重叠,共有事权范围过大,这一方面不利于事权的执行与操作,造成多方沟通实施中的困难;
另一方面也导致财政事权的报告主体分散,造成核算责任不断转嫁推诿。
2.同一事权的管理方式在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做法,导致类似的公共基础设施行政管理与会计确认缺乏可比性。
3.财政事权不断下移,县、乡镇政府在财权事权配置上出现实际事权庞杂、职责不清等问题,致使许多基层政府活动未在财务报告中列示反映。
基层政府成为政府综合财务报告试编阶段中的核算关键,但是受限于编制人员与行政能力配置的限制,梳理核实如此多的事权远超出其行政负荷,最终出现众多公共基础设施未得到公允列报的现状。
(二)支出责任不匹配,财权财力保障不均衡
1.资金缺口大,支出责任不匹配,地方政府通过承担隐性负债来发展地方经济与建设公共基础设施,造成了地方债务负担越来越重的恶性循环。
2. 转移支付机制不合理,不同税收来源分配比例和调整能力不足。
此外,筹资途径多元化,各部门债权债务往来频繁,又缺乏清晰的政府管理体制进行保障,直接导致会计核算与编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中的资产负债填列困难。
三、基于财政事权划分、支出责任匹配为依据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基础改革路径
(一)以梳理财政事权为契机界定报告主体边界和范围,改进经管资产的核算列报基础
首先,以财政事权划分为切入点,梳理政府间和职能部门具体的责任边界,为财政制度有效运转提供基础和支撑,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逻辑起点和内在联系。
明晰财政事权改革方向与顶层设计,包括明确财政事权的归属层级。
其次,在事权划分原则基础上,改进政府管理体制,明确清晰的责任报告主体。
最后,夯实报告主体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会计基础,包括会计工作基本条件,信息系统,编制人员素养与培训等。
会计工作基础条件是政府开展会计核算的基础物质条件和保障,但是相对于会计准则的制定而言,会计工作基础条件受到的关注很少,大多集中于发展中国家的文献研究中。
会计人员是另一争议较大的会计基础,从客观现实角度考虑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编制毫无疑问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潜在要求数以千计的政府工作人员参与进来编制数千张部门财务报告,但是问题是是否存在如此多的合格会计人员。
(二)在财政事权划分基础上规范匹配支出责任,规范报告主体的负债支出
《基本准则》对会计主体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包括各级政府及与“本级政府财政部门直接或间接发生预算拨款关系”的各部门、单位,但是鉴于政府事权分割、预算拨款关系相互交织的状况,在实际工作中报告如此广范围和如此多的债权债务是极具挑战的。
因此首先需要在明晰事权划分的基础上,界定支出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