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英东
真实的中国东北是什么样的?
Michael Meyer
《东北游记》
—
“我很清楚,在东北,
能够对中国的过去一探究竟;
但没有料到,在荒地,
我能一瞥这个国家的未来。”

梅英东,美国人
旅行作家,“东北女婿”
1995年首次来华
7 年前,梅英东住进他的中国妻子出生的东北村庄,在黑土地扎了一年根。在这本问世不久的《东北游记》中,他记录了那一年的东北见闻,以及自己亲身考察的远东历史。
梅英东笔下的东北与赛珍珠的《大地》一脉相承——“我们从土地上来的,我们必须回到土地上去。”在他的笔触下,东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与土地紧紧联结。
“东北一直以来被当做一块试验田。皇帝、军阀、殖民者和干部都试图将这片土地纳入他们的计划之中,但几乎所有人都失败了。历史告诉我们,在东北真正‘行得通’的是耕作。”
而村庄中各种悄然发生的变化也喻示着,这个村庄,乃至这个国家的未来也都将被人与土地的亲疏关系所深刻影响——村中几乎所有的土地都已被当地一家民营企业所承包,世代耕种的村民也将搬入新建的楼房,但“眼下,同意搬迁的人寥寥无几”。

我们很少读到西方作家对中国农村地区的记录,他们的目光大多投向经济重镇,或是政权中心。而似乎只有在报道强拆的时候,那些住在北京高级公寓中的外国记者才肯屈尊来到农村。
正因如此,能在一个美国人的非虚构写作中读到一个平实而厚重的东北,在当下是一件弥足珍贵的事情。书中讲述的一切都那么真实,只是我们不曾观察到而已。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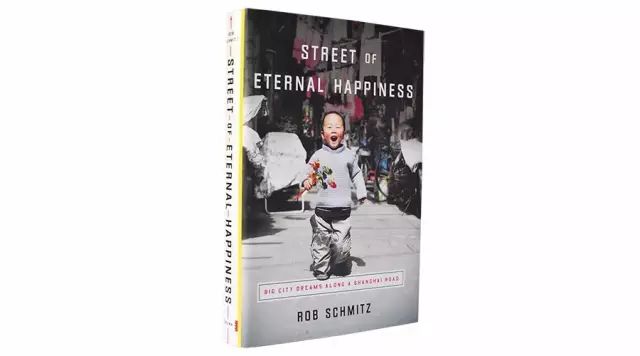
罗勃·施密茨
上海老洋房里的文艺青年在想什么?
Rob Schmitz
《长乐路:上海路旁的大城市梦想》
—
“他们是中国五十年来第一代人,
有机会获得一些时间和金钱,
来学习存在主义的人。
在我眼里,他(们)是中国未来的象征。”

罗勃·施密茨,美国人
NPR 驻上海记者
1996 年初次来华
长乐路这个地名,我们太熟悉了。作为一个时髦的的地标,它频频出现在那些探讨城市生活方式的报道里,显得既市井又前沿。
但我们所不熟悉的是它的英文译名:Street of Eternal Happiness,“永恒幸福街”,听上去意味深长。罗勃·施密茨将这条自己安家 6 年的街道选为书名,或多或少地借用了这层微妙的双关。
罗勃·施密茨选择了一位在长乐路开三明治店的年轻人,陈凯(音)作为主线。他是八零后,从一个四线小城市的国企“逃”到外省,靠销售意大利手风琴赚得第一桶金,如今则跟朋友合开了这么一家时髦的小店。
施密茨将陈凯划分为中国的第一代“文艺青年”。 他认为,长乐路的主人不是满街林立的时髦小店,而是小店楼上,这些文艺而愤怒的年轻人。

在罗勃·施密茨的观察中,这批出生在八十年代初的年轻人通过西方文化的摄入,生发出了父辈少有的自由意志,进而有能力去自主地认识这个世界,并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而在看似悠闲而“文艺”的生活表象下,陈凯们也同样面临着来自社会现实的重压。他们对社会既有体制中不合理的现状有着敏锐的感触,同时又不具备改变的能力。“他们想要过舒适的生活,但与此同时他们希望有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
但在施密茨看来,无论这些年轻人的本质是文艺还是愤怒,他们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中都是至为可贵的角色,因为他们能看清自身处境,并试图寻找未来的方向,“这是其他地方的年轻人都会做的事”。
✍️

何伟
如何记录一个不断变化中的国度?
Peter Hessler
《奇石》
—
“你会有种感觉,
一群人正跟在后面,
紧追不舍。”

何伟,美国人
记者,作家
1995年初次来华
《奇石》是何伟最近一部在中国出版的作品,以文集的形式继续他此前的“中国三部曲”未来得及记录的边边角角。
事实上,在何伟看来,哪怕每年出一本书,也不见得能跟上中国变化的速度。这个国家就像一块“奇石”,站在每一个时间点和每一个位置坐标,都能看到截然不同的面向。
在中国最早出版的《寻路中国》中,何伟便发出过这样的感慨。“新发现差不多每天都有。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中国人普遍具有这种感觉:一切都在快速地变化着,没有几个人敢自夸自己的知识够用,人们随时都会面临新的情况,需要去琢磨透彻。”
中国的一切都在一股无形力量的推动下,不断发生着惊人的改变,几乎呈现出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图景。而身处这种图景中的我们往往却犹豫过度沉醉于变化本身,远远比不上何伟这个外国人看得真切。

五六年前,《寻路中国》和《江城》在中国的出版帮助国人找到了一双来自外部的清醒平和的眼睛,也将“非虚构写作”的概念带入了国内出版界的视野。某种程度上,他正式我们所描述的这场风潮的始作俑者。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前文提到的两位作家,梅英东和罗勃·施密茨与何伟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上世纪九十年代,他们三人都曾跟随美国“和平队”前往四川支教。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层经历,才使得他们无论在书写中国哪个面向的故事时,都保有一颗难得的同理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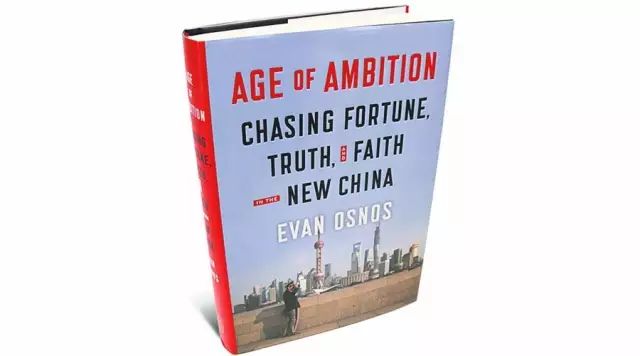
欧逸文 :
中国,你的梦想是什么?
Evan Osnos
《野心时代》
—
“经济勃兴有如一列座位有限的火车,
对那些已经找到座位的人进展超乎想象;
但其他人只能靠自己双脚所及,
能跑多远多快,就跑多远多快,
只是最终,他们只能望着火车消逝与远方。”

欧逸文,美国人
记者,作家
2005年首次来华
在国内有机会读到的读者中,欧逸文这本《野心时代》获得了两极分化的评价。一部分人认为他精准地把握住了中国当下的乱象,直击痛点;一部分人则认为,他的视角太过偏激,远不及何伟的普世情怀。
撇开评价,我们来看看欧逸文笔下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在欧逸文的描述中,他在北京的社交生活是这样的:白天与达官显贵攀谈,晚上与被软禁的“异见人士”为伍。“你很容易把他们看待成代表新中国、旧中国,泾渭分明的政经领域,只是到最后我归结认为,他们是同体合一的。”
在这样的观察下,欧逸文眼中的中国由两个宇宙组成:既是世界局势中的新贵,同时也依然是一个落后的非民主国家。在两个宇宙的夹缝间,欧逸文用“野心”两个字来概括中国人的国际心态——一切都在蠢蠢欲动,一切又似乎都没有切实的保障。
这种野心,如今被中国官方称为“中国梦”。

距离《野心时代》问世已过去两三年,书中记载的 2008-2013 年间发生的社会热点大多已经被人淡忘。脱离事件本身,欧逸文对中国的观察是否依然有被反思的价值?这似乎才是值得讨论的部分。
✍️

洪理达
中国真的有那么多“剩女”吗?
Leta Hong Fincher
《剩女时代》
—
“有的女人为了爱情结婚,
有的女人为了金钱结婚,
但是在中国,有一批女性
却是为了摆脱羞耻感而结婚。”

洪理达,美国人
清华社会学博士
1994 年首次来华
大概从 2007 年左右,中国媒体开始大规模使用“剩女”这个词。当年年中,这个词汇被教育部纳入了汉语新词的列表中,相当于官方认证了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这样的舆论浪潮被当时在清华研究中国性别不平等现象的洪理达注意到,她进而展开了研究。
在最终成书的《剩女时代》中,洪理达提出了两个基本的观点:在因的一面,“剩女”只是舆论引导下形成的莫须有问题;在果的一面,这个莫须有的问题却进一步加重了中国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给女性造成了更多的社会压力。
中 国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带来了极大的社会隐忧,而在洪理达看来,舆论对“剩女”问题的鼓吹实质上是在掩盖中国男性人口过多的事实。通过对官方媒体在这一问题 上发声强度的考察,洪理达指出,这种舆论导向的目的便在于强行引发女性的羞耻心,进而贬低女性的价值,从而转移矛盾的焦点。

“房产”争端便是这一矛盾所导致的最明显的表征。在洪理达研究的 280 余个案例中,大量女性由于遭遇“剩女”舆论的压力,在家庭财产的归属上遭遇了极不公平的待遇——她们为了“不被剩下”匆忙结婚,甚至妥协到放弃房产证上的名字。
除了房产,中国的职业女性为了嫁人,还作出了多少牺牲?“剩女”这个群体真的存在吗?这些都是中国当下最易引发口水战的本土议题,从一个美国博士的论文里读到,也许能给你新的思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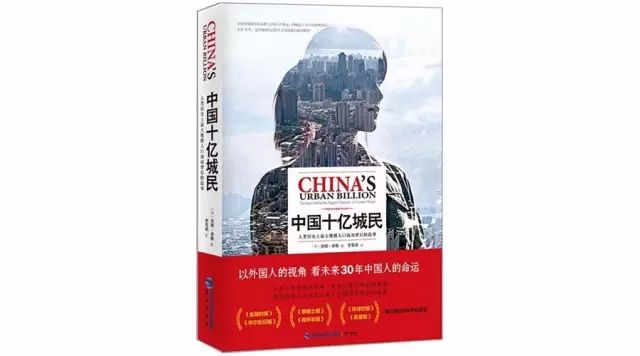
唐米勒
农民工会给中国的城市带来什么?
Tom Miller
《中国十亿城民:
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移居背后的故事》
—
“他们在自己的国家,
却像非法移民一样地生活着。”

唐米勒,英国人
记者,现与家人一同居住在北京
这本书的繁体版标题可能更为直接:《十亿民工进城来》。
过去三十年间的中国,超过 5 亿人从农村迁入城市。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人口总和。到 2030 年,中国的城市人口预计将达到十亿,占全球总人口的八分之一。这个惊人的城镇化前景被英国记者唐米勒选为了他的标题。
与我们想象的不同,关于中国这股惊人的移民潮,米勒是带着乐观的心态去记录并审视的。他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即在于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里来。
在他看来,中国目前城市的规模还是太小,远远没有发挥出城市的潜力,而眼下包括“鬼城”“城中村”之类的怪象都将在城市化推进到一定程度后,都将逐渐得到解决。

米勒更关注其实是移民的户籍问题。通过将社会福利限制在户籍所在地,中国的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民工在城市永久安家。
在这个问题上,案例,数据,加上亲历者的采写,都构成了唐米勒笔下中国故事的一部分。虽然你在社会新闻中读过太多这样的人间喜剧,但从一个英国人的笔下,你或许能获得一个旁观者清的视角。
编辑:梁珂
来源:elleme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