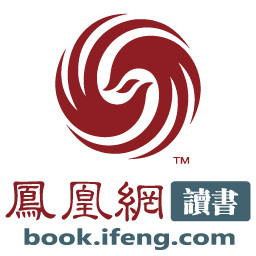>>> 人人都有故事,
这是[有故事的人]发表的第589个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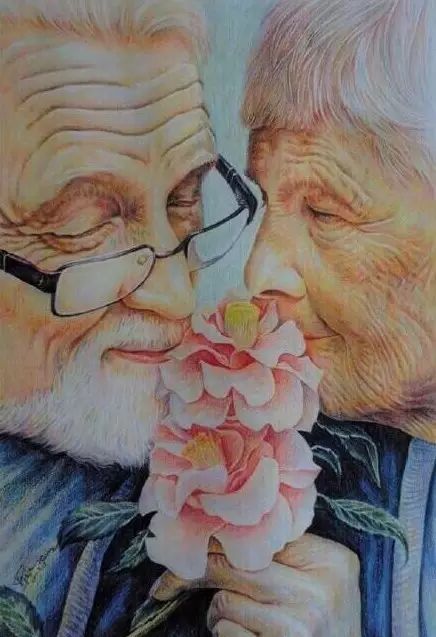
一个国民党老兵的异国情缘
◆ ◆ ◆
文 | 曾凡义

他是一个不应戴帽管制的国民党兵油子,也是一个农村老百姓生产生活须臾不可短缺的能工巧匠,还是风月场中一颗多情的种子,演绎出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异国情缘……
一、吹牛皮吹出了一顶反革命帽子
文革初期,我“投亲靠友”来到京山县永兴区王家岭插队。
安顿下来后的第三天,被队长通知到大队部参加批斗大会。我去的比较迟,刚刚踏进土木结构的礼堂,就看见当作舞台用的土台上站着七八个头戴纸糊高帽,胸挂硬纸壳做的大牌子,脸上涂着墨汁的“人不人鬼不鬼”的“牛鬼蛇神”。中间那个最高最瘦的40来岁的中年人最惹眼,牌子上写着“历史反革命分子王爱振”,还打了一个大红叉。两个红卫兵小将“伴随”左右架着他的飞机,其他几个还没有资格享受如此殊遇,看样子今天他是主要斗争对象。在一阵阵“打倒反革命分子王爱振”口号声中,造反派勒令他交待杀害了多少革命战士。只见他说:“我是个小炮兵,一炮打出去,炸死了几个人我怎么能知道呢?反正我没有亲手杀过人。”“这家伙不老实!”主持会议的粗脖子司令给了他一顿雨点般的拳头。就这么折腾了几个小时,也没斗出什么名堂,此时已经日傍西山,斗争会便草草收场了。我就像看了一曲颇滑稽的小品。
第二天,队长安排我去打扑磙,那是一种在一个木框架内安着一排连着轴的木轮子农具,框架上还有一个“奓开”着四条腿的木凳子。人坐在凳子上,牛拉着走,轮子转动,将水田里翻耕过来的泥巴轧烂。队长作了一番技术示范后便让我开始作业。我坐上凳子,挥动牛鞭,扑磙“扑通扑通”地转起了圈子,溅起的泥浆就像汽车的尾气,不时溅到我的身上。“驾!”我使劲挥动牛鞭,像驾驶着一辆小坦克,神气十足。由于速度太快,在转弯处突然“咔嚓”一声,“坦克”抛锚了,那排轮子从框架内脱落,我立即“哇”住牛去找队长汇报。队长看了一眼,见轴轱辘破了,对我说:“这是木东西,牛不能赶的太快,弯不能转的太急。你去仓库门口找王师傅来修一下,他在那里修农具。”
我来到仓库门前,只见一个高个子师傅正在修一部风车,边挥动斧头凿子,边与几个不能参加生产的老人高声大气地谈论着什么。我按队长对他的称呼喊了声“王师傅”,他回头对我微微一笑。啊,这不就是昨天斗争的那个王爱振吗?只见他洗净了墨汁的面孔还比较白净,花白的头发只剩下周围的一圈,中间谢顶的那块小抛物面油光水亮。身材高挑,面目和善,像一个见过世面的教书先生。他亲切地问我:“小知青,什么事?”,我说明了原委,他拿起锯子斧头立即随我来到田里。他把车轱辘看了一下,说:“不要紧”,拿出几个钉子钉上,又用铁丝打了几道箍然后说道:“这东西常在水里泡,都朽了。牛要慢点赶,转弯不要急,欲速则不达啊。”还摸了摸我的脑袋。咦,这乡里人竟然还知道“欲速则不达”,肚子里还有学问呢!
从他与老人们谈天时的那种神侃胡吹和与我交谈时的那股亲热劲来看,昨天的事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是啊,运动一来总是将几个四类份子盘来倒去像玩猴把戏,如家常便饭,他们都搞油气了,便也毫不放在心上。干部和贫下中农也见怪不怪,会上上纲上线地斗,会后依然礼尚交往。只有那几个别有用心的二杆子才较真劲下狠手。这就是当时的阶级斗争啊!
修扑磙让我近距离接触了这个并不可恨倒觉得十分随和的“历史反革命”。从斗争会上了解到他只当过几天小兵,为什么要戴帽批斗呢?不是说连长以上才够杠杆吗?我又犯了“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毛病。唉,我也成了被贫下中农教育的对象,何必“咸吃萝卜淡操心”啰!
不久,终于从50来岁的望九伯嘴里知道了王爱振的传奇经历和这顶帽子的由来。
队长见我干农活的能力太差,出于照顾知青的好心,安排我到小队养猪场给老饲养员望九伯当下手。望九伯读过多年私塾,是这个生产队文化最高的人。听说解放初期在乡政府当秘书,由于日伪时期当过几天伪军,清队时被清退回家了。
望九伯为人厚道,寡言少语。每天与望九伯一起剁猪草煮猪料,喂猪食,时间一长磨合得挺知心了,话也多了一些。一天,我问他:“王爱振挺好的一个人,怎么会成了反革命?”望九伯不屑地撇了撇嘴:“这叫‘叫花子背捆草一一自讨’是他吹牛皮吹出来的。”。
真稀奇,吹牛竟吹出了一顶帽子。
从望九伯嘴里我了解到,王爱振出生于1925年,家里是当地的富户。他精明灵光,还读过几年私塾。从小就喜欢出风头说大话,乡邻们都说他是丝茅草——“从小棘人,到老棘人”。
1946年春天他结婚了,没过几天,他说保长将他家的“田亩捐”算多了,就跑到保长家扯皮。保长也不是善茬,两人争吵起来,王爱振竟打了保长一顿。保长是有来头的人,立即报告给乡长卢继道,当晚便派了两个乡丁把他五花大绑抓去了。走了约半里路,当踏上小河的“磴子桥”时,趁着伸手不见五指的“月黑头”,人高马大的王爱振飞起两脚将乡丁踢翻在河里,飞跑着钻进了黑松林。他在石头上磨断了绳子,不敢走大路,翻山越岭连夜跑到了60里外的皂市。第二天搭下水航船一天一夜到了汉口,投奔了他的表叔一一在武汉驻防的71军88师炮兵团长刘在义,当上了炮兵。71军是著名将领陈明仁的部队,不久开到东北参加四平战役。1948年底,四平解放,他成了解放军的俘虏,进“感化训练班”学习了几个月。不少穷苦出身的俘虏自愿报名参加了解放军;他家生活优裕,加上新婚妻子的诱惑和报复那个保长的愿望,因而说什么也不愿留下。于是军管会给了他路费并开了一张“还乡证”,于1949年初回到家里。
他回来时可风光了,穿着一套用两块银元买的旧将军呢制服,因为战争期间眼睛落下了“见风流泪”的毛病,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活像一个年轻英俊的军官。这时,那个保长已被镇压,他无仇可报了。但年轻气盛的他仍不务正业,整天东游西荡,牌场进赌场出。有时候输急了还耍赖讲狠话:“老子当过炮兵连长,还怕你?”活是个兵油子。
他爱沾花惹草,人长的还算帅气,一些农村妇女也原意缠他,还沾染过几个黄花闺女。他特别爱吹牛,逢人便天南地北南京上海海吹一通,分明是被俘虏的,却吹嘘是与陈明仁一道起义的。还说见过杜聿明和东北督战的蒋介石。他爱“玩人”,有时候闲得无聊,就拿出一把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日本东洋刀,站在禾场上舞来舞去,别提多神气了。
那时候还没土改,人们对这个当过大兵傲气十足的年轻人虽然讨厌但也不十分在意,都说他是一个能吹死牯牛的“黄表灰”。
到了1953年镇压反革命,由于他说自己当过连长,正好够杠杠,便被抓进了监狱。这下后悔了,鼻涕眼泪都来了。他说他只当过上士班长,当连长是吹牛,人家岂能相信?要他找保人。他父亲虽然讨厌这个“日白扯谎说大话”的儿子,但也不能眼睁睁地看他坐牢,就找望九伯去作保。望九伯在乡公所当秘书时见过他的“还乡证”上确实写的是“上士班长”,于是出面作保,上面又调阅了档案,将他放了。
被释放后的他终于老实了一些。这时候,他家里被划成了地主,“五大财产”没收,又有了几个孩子,家大口阔,开始安心种田学手艺。
到了1962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阶级斗争的弦又绷紧了,贫下中农都说王爱振南京上海都到过,还见过蒋介石,又有将军制服东洋刀,绝对不是士兵,于是抄了他的家,没收了剩下的那把东洋刀,一次斗争会后被戴上了反革命帽子。望九伯介绍到这里不无感慨地说:“你说这不是吹出来的一顶帽子吗?自作孽啊!”
二、一个有多种手艺的能工巧匠
王爱振是一个心灵手巧的聪明人,傲气磨钝后,在生活的磨练中,学会了好几种手艺。
1、木匠。大木、小木,盖房子、打家具都行。木匠手艺没有拜过师傅,是瞟学的。
2、箍匠。水桶、脚盆、饭甑都做的像模像样。1958年公共食堂的大饭甑就是他箍的。
3、盖匠。就是将圆木锯成木板的工匠,他也在行。
4、砖匠。山区农村都是挖土砖盖房子,挖砖时一人掌锹十人拉。哪家挖砖都得请他掌砖锹,这种活不仅要力气,更重要的是技巧。他当师傅喝酒坐上席,还多得一包“大公鸡”香烟。
5、裁缝。他有两男四女六个孩子,加上老母亲,家大口阔九口人。大人小孩的衣服裁新的改旧的缝缝补补,都是他在那台旧缝纫机上“踩”出来的,外人休想赚他一分钱。
6、硝皮匠。他能将人家丢弃的狗皮、猫皮、獾子皮捡回来用什么药水浸泡脱脂后制成裘,大人小孩都穿毛皮背心,戴狗皮帽子,挺神气。
7、雕匠。那时候男婚女嫁打床和柜都需要刻花雕朵,他的镂刻技术很过硬,家家都请他。
8、油漆匠。他会做油漆,还精于彩绘,他油的床、柜、衣箱明光闪亮,画的花鸟活灵活现。
还有什么补雨伞、修电筒,补胶鞋,熬糖煮酒做篾活等,农村生活中凡是需要花钱请人的事他几乎全包揽了——这也是生活逼出来的,他家只有两个劳力,要养活一大家子人,不想办法行吗?也是他聪明,无师自通地学会这么多手艺的人在农村是很少见的,怪不得他脑壳顶上的头发都掉光了,因为他“聪明透顶”。当然“艺多不精”,有些手艺也只能算过得去。
他讨了这些手艺的光,与队里签合同包副业交提留。那年头农村的生活很饥馑,他常年在外吃百家饭,有酒有肉有烟抽,省下了口粮,家里的日子稍微好过一点,“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啊!
有时候上水库,人家热汗淋漓拉板车,他坐在树荫下敲敲打打修车厢,胡侃日白挺悠闲,不少人嫉妒鄙夷地瞟他一下:“哼,四类份子倒比贫下中农快活!”。咋样呢?人家有手艺,你也只能干瞪眼。
三、炫耀隐私成了日本特务
农村社员搞生产都爱说流氓话,好像是一种打发疲劳,减轻劳累,寻求精神刺激的灵丹妙药,故有“干活不说B,日头不偏西”之说。最爱说这类话并且很露骨的是王爱振。他虽然包副业,农忙时也回来搞突击。男女在一起干活时,他经常瞅着年轻妇女的敏感部位,眼里射出两股邪乎乎的淫光,眉飞色舞,说些“挑不上口”的挑逗性荤话。这时候他不像教书先生了,倒像一个流痞光棍。妇女们知道他的特性,也不十分讨厌。现在说来是性骚扰,当时怎么会有这种概念呢?
有一天,我们都在扯夜秧,他又讲起了在四平的快活日子。说日本婊子既文明又讲卫生,与你干那事之前给你打一支消毒针。因为说的活灵活现,小青年东平问:“你嫖过日本婊子吗?”他笑而不答。连狗立即附和:“这还用说,他这个骚鸡公还有不打水的?”王爱振哈哈大笑:“骚鸡公咋样?孔子还说‘食色性也’哩!”这时望九伯忍不住道:“爱振,你别毒害年轻人,不要用‘登徒子好色’来强词夺理。”这段话我还朦朦胧胧听得懂,之于那几个农村青年好似听外语。爱振立即拱手道:“九哥赐教,九哥赐教,嘴快活而已。”。
反正不论干什么活,只要有爱振在场,就有一股荤味骚味,都爱听他讲男女风流事儿。
这一年正清理阶级队伍。一天,大队又开斗争会,我们乐得休息不干活,纷纷来到大队部,只见横幅上几个大黑字:“斗争日本特务王爱振!”啊,怎么反革命又变成了特务呢?看样子又该他倒霉了。
人到齐后,粗脖子司令宣布“斗争会开始!”,几个民兵将绳捆索绑的王爱振从化妆室里推出来。
“把他吊起来!”粗脖子下命令,几个喽啰立即动手将他反吊在横梁上。
司令恶狠狠地踢了他一脚,问道:“今天老实交待,你是怎么当上日本特务的?搞了哪些破坏活动?”
王爱振被吊的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地回答:“我,我不是特务。”
“你有日本老婆,还能不是特务的?”
“我没,没有日本老婆。”
“冬狗子,你来揭发!”粗脖子又下命令。
二流子冬狗走出来,指着爱振的鼻子尖说:“你亲口对王老幺讲的,还不认账?”
王老幺是爱振的堂侄,也是个流打鬼,两人臭味相投,老缠着爱振讲那些当兵时偷鸡摸狗的事。一次说得兴起,爱振竟炫耀出玩日本女人的隐私。王老幺嘴不稳,又对冬狗讲了,并嘱咐他千万别乱说。冬狗子曾因为调戏王爱振的老相好吴幺儿被爱振痛打了一顿,因此怀恨在心,屁股一车就告诉了粗脖子。
经冬狗子揭发,事情是这样的。爱振曾吹嘘,那年在四平时他因病住进了陆军医院,为他打针护理的是个年轻漂亮的日本护士。他这种见花就想沾的人岂能不动花心,于是眉来眼去好上了。他只是个士兵,一无地位二无钱,可能只是偷偷相会云雨巫山了几次,连同居也说不上,就是农村所说的那种“露水夫妻”。
他认为玩过日本女人是件爽心体面事,没想到嘴痒惹祸成了日本特务。
斗了半天,人们听了一个男欢女爱的故事,像看了一曲花鼓爱情戏,一个个心里挺滋润,粗脖子也憋在心里好笑。
说他是特务又拿不出证据,捆绑吊打一阵后,决定取消他包副业的资格回生产队交贫下中农监督改造。
在散会的路上,望九伯说:“听他瞎吹牛,玩没玩过日本女人只有天知道。又是自作自受啊!”
四、日本来信
流光容易把人抛,无情岁月催人老。转眼到了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了,自己吹出来的反革命、日本特务和客观存在的地主分子这三顶压了王爱振几十年的帽子终于摘掉了。他头高颈旺,一下子轻松了。但人也老了,特别是不让包副业后的这十几年,没日没夜地干苦活重活,里里外外操心磨难,还不到六十岁几乎老态龙钟了。人瘦的像劈柴,腰也弓起来了,可是日白扯谎的习性不改。人们都恭喜他摘了帽子,他却将那秃顶摸了摸说:“没帽子不好,我这光脑壳最怕冷。”。
其时,我已在农村结婚安家,招工到了公社党委办公室写写画画;家里是半边户,经常回家种责任田。一天,王爱振拿着一封信来找我,问我懂不懂日语。我看了一下信封,上面用中文和日文并排写着“中国湖北省京山县王家岭王爱振先生收,落款是日本国东京××医院”想必邮局费了很大的周折才送到他手里。信的内容是日文,只有很少的几个中国字。他认为我读过高中,可能认得,可我怎么懂日语呢?于是我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我听说京山卫生院有个护士长是日本人,他的丈夫是东北军的一个师长,在郧阳战役中被日本飞机炸死,以后流落到了京山。你去找她看看。”“谢谢指引。”他非常满意地走了。
不几天,他十分高兴地来到我家,说那个护士长很热情,将信的内容翻译给他听了。原来写信的就是在四平与他相好的那个日本护士,叫片山尚子。解放后,日本侨民全部遣散回国,她回到东京老家,在一个医院继续当护士,这次写信想联系一下,没有说很多话。
想不到这个满口白话的王爱振竟说了一次真话,还真有一个日本相好,果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风月情种。他再三嘱咐我保密,事关家庭和睦,我当然守口如瓶。
过来约半年,公社公安特派员到办公室找我,要我带他去王爱振家。说是县里通知,一个日本友人要来拜访王爱振。我心里不禁一惊,肯定是片山尚子。
特派员来到王爱振家看了看,虽然分田到户,生活有了改善,但家里依然十分寒酸。第二天便派人送来了新床单、热水瓶和电视机等,准备迎接外国友人。
可是一天天过去了,始终不见外国友人光临,原因却不得而知。
五、北京相会
到了1986年,县委统战部通知永兴公社,日本友人片山尚子将于6月5日抵达北京,邀请王爱振到北京相会。特派员又来到王家,告知日本友人下榻的是华夏宾馆,请按时赴约。这下子家里人有的高兴有的愁,高兴的自然是王爱振,忧愁的是那个相守几十年的糟糠老妻。这一年王爱振已61岁,佝腰弓背,满脸皱纹,见风流泪的眼睛眨巴眨巴,成了一怂头怪脑的农村老头。他一个人是不宜长途旅行的,由大儿子四平陪同。大儿子是他回来后第二年生的,为纪念四平战役故取名四平。四平已分家,30多岁了,也有很好的木匠手艺,于是掏路费与父亲一起来到了北京。
下火车后,北京城已灯火辉煌。从未到过大城市的四平和几十年没出过远门的爱振,在人生地不熟的北京到哪里去找华夏宾馆呢?只好先搞饱肚子,在一个小摊上胡乱吃了一点。农村人是穷怕了的,都很苟简,不想花钱住旅馆,想找一个避风的地方将就一晚明天再说。火车站附近是郊区,找来找去看见了一辆弃置的废面包车,就钻进车内斜靠在破沙发上胡乱地凑合了一夜。幸好是夏天,没有冻着。
第二天经交警指引,搭了几趟公汽,转了几道车,好不容易找到了金碧辉煌的华夏宾馆,却怯生生地不敢进去。倒是四平年轻人胆子大一些,磨蹭到服务台前对女服务员吞吞吐吐地说:“请问,日本客人,片山尚子,住在哪?”服务员翻了翻记录簿说“306”。他们来到三楼,轻轻地敲了一下“306”的门。一会儿,房门开了,出来了两个人。一个是穿着一身洒花连衣裙戴着钻石项链涂着口红,看上去只有40来岁的珠光宝气的女人。另一个是高挑身材西装革履约30多岁的年轻人。年轻人用生硬的中国话问道:“你,你们的找谁?”四平结结巴巴说:“我,我们是京山,来的。”那女人立即热情地伸出手:“是王爱振吗?我是片山尚子。”尚子对那个年轻人说:“这是我的中国朋友。”几十年没见过面的“露水夫妻”双方都不认识了……风云变幻,悲欢离合,一衣带水,两情依依。千言万语竟不知从何说起。
中午,片山尚子在富丽堂皇的宾馆餐厅宴请王爱振父子。红木餐桌,洁白的台布,玻璃转盘,十分气派。落座后,服务员拿出点菜单,片山尚子推给王爱振:“爱振,你爱吃什么?点吧。”爱振擦了擦眨巴眼推说字小看不清,又推给尚子:“客随主便。”尚子点菜后,鸡鸭鱼肉生猛海鲜茅台香槟上了一大桌子,竟将王爱振吓住了,不禁失言道:“这,这要花多少钱?”四平轻轻地用脚踢了他一下,小声说“少说话”。那个年轻日本人略带鄙夷地瞟了爱振一眼。片山尚子非常热情,不停地给两位客人夹菜,年轻日本人频频筛酒劝饮……
爱振和四平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后,跌跌撞撞地回到“306”隔壁房间,因旅途劳累一觉睡到日偏西。
吃完晚饭洗漱后,片山尚子来到“307”,四平知趣地借故离开了。两人面对面坐着,百感交集,心潮难平。
无情的岁月拉开了难以逾越的差距。一个是脸色红润细皮嫩肉穿着阔气风韵犹存的贵妇人;一个是瘦骨嶙峋瘪嘴秃顶皱纹满脸,穿着一身自己缝制的白衣黑裤的土里土气的乡下老头。就像一个玲珑精致的玉雕花瓶旁边放着一个瘦长干瘪的老茄子。40年前一对年龄仿佛风华正茂的情侣,竟然被岁月磨砺出如此巨大的反差。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经历和环境的影响,似乎也是遭受文革灾难的中国与亚洲四小龙的历史误差。
暌别40余年,万言千语不知从何说起,两个老人竟喉头哽咽,哑然相对,这真是“悠悠生死两茫茫,一朝相逢泪千行。”
还是片山尚子先开口,打破了尴尬的沉寂,开始讲她回国后的经历。
片山尚子于1941年与父母一同来到中国东北。父亲片山繁雄是关东军某师的参谋长,在一次战役中阵亡后,母女两滞留于四平。片山尚子进了护士学校,毕业后分到了陆军医院,以后认识了王爱振。1949年初回到日本时却不料已身怀六甲,不久生了一个儿子。孩子没有父亲必然受到社会歧视,也将影响再婚。于是将孩子给了她婚后几年没有生育的妹妹抚养,取名伊藤一郎。为了孩子不受到心理伤害,决定保守这个秘密。片山尚子后来到东京某医院当了护士,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十多岁的教授。由于年龄差距,夫妻关系不怎么融洽,不知是什么原因没生个一男半女。日本女人大都比较多情,加上身边没有孩子,自己亲生的儿子又不能视作亲生,经常思念昔日的情人,才有了这次北京之行。她带伊藤一郎来中国,借口是带他来旅游,目的是为了让爱振看一眼这个他“无意插柳柳成荫”播下的“中日友好”的种子,让嫡脉骨肉有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分享爱情的结晶。但叮嘱他只能看看,千万不能感情用事戳穿这个秘密。
爱振也讲了回家后被打成反革命、特务,几十年挨整的灾难性痛苦。
“好了,终于云开雾散了,过去的事到此为止。”片山尚子一挥手,十分大度地给他们的相互倾诉予以了结,回房休息。
劳燕分飞几十年的情人重逢,却再也没有了当年鱼水交欢的兴致了,不仅是因为体内的荷尔蒙所剩无几,更重要的是他们已不需要肌肤之亲了,只想将漫长的情思划上一个句号,了解相隔万里的两颗跳动的心就心满意足了。
第二天,片山尚子和伊藤一郎陪同爱振父子游览了故宫、颐和园。第三天早晨上了回国的飞机,爱振和四平到机场送别。在机舱门前,尚子向爱振父子挥手告别,却没有流一滴眼泪。倒是爱振的眨巴眼总有泪水溢出,不停地用手绢擦来擦去。和自己的亲生儿子相处了两天,却不能相认,够痛苦的。
六、郁郁而终
从北京回来后,爱振又风光了好一阵子,大小队干部和乡邻都好奇地找他问这问那,打听那个日本老婆的情况。爱振就抬起手腕炫耀片山尚子送的那块银光闪闪的手表,还从口袋里掏出馈赠的日元,让人们欣赏“洋票子”。人们都说日本女人真是重感情,只是几夜的夫妻还漂洋过海万里寻夫,难能可贵,爱振艳福不浅,为他高兴。
不高兴的人是他的老妻李幺儿。以前她对爱振也曾有过怀疑,每年农历六月初六“龙晒衣”这天,爱振都要将一件从来不穿的黄毛线背心拿出来晒一晒摸一摸。她当然不知道这是在四平时片山尚子为爱振织的,没有真凭实据不能下结论。特派员第一次来通知说有日本友人来拜访时,也以为是爱振的什么朋友。这次北京回来后四平说是一个日本女人,一下子就动真气了。一看见那块手表就骂他:“老砍头的,都快入土了还到北京会情人,你眼里还有没有家里人?”
这个对他从来没有好言语的李幺儿,爱振愈来愈看不顺眼了。见到了那个依然如花似玉的半老徐娘,再看这个老得如蔫黄瓜的为他生了六个孩子的糟糠之妻,确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觉。一个心猿意马成天沉浸于昔日的欢乐和北京相会的美好回忆中;一个醋气掀天不依不挠砍头割脑地数落谩骂,水火不能相容,终于分居了。通过家庭会议,四平赡养母亲,小儿子五平负担爱振生活,爱振搬到五平新做的楼房里去了。
2008年,李幺儿去世,四平安葬了。以后五平夫妇外出打工,爱振一个人烧火做饭,看管房子。人老了,不能做木活了,就拿起篾刀编几个筲箕提篓到集镇上换点小钱。每天抽点低档烟喝点小酒倒也自在。只是仍然忘不了那个日本女人。没事了就翻来覆去地数那几张日本票子,轻轻地抚摸日本手表,还将那件黄毛线背心翻出来晒一晒摸一摸。睹物思人,思绪万千。可片山尚子回国后再也没有音讯,在通信如此发达的今天竟连电话也没有一个。是那个老教授有所风闻严加管束了吗?是她觉得见了一面心愿了却而释然了吗?还是对这个满脸沟壑纵横两眼黯然失神的如“土蛤蟆”般的农村老头心灰意冷了呢?
2010年,爱振突然休克,像死了一般。四平立即将他送进医院进行抢救,可是怎么也醒不来。胸口还是热的,心脏还在微弱跳动。一天一夜后,竟奇迹般地醒过来了。一星期后出院,不久又恢复了打篾活晒毛衣的生活。
一天,我回家时顺便到他家门口坐了一下,闲谈中突然想了解一下人初死时的感觉,于是问他。他说像做梦一样,飘飘忽忽到了一个孤岛,片山尚子迎接了他。两人在花园似的岛上玩了一整天后,片山尚子告别,像飞天般地拂袖而去。这时候,他醒来了。
“唉,”他轻轻地吐了一口烟雾,对我说:“她可能死了,不然我怎么能看见她呢?”我说:“她比你年轻,身体又那麽好,不会吧。”因为我见过他们在北京相会的照片,片山尚子确实年轻漂亮,否则,我怎么会有描写的依据呢?
2012年,王爱振去世,享年87岁,五平负责火化安葬。他的不尽思念化作一缕轻烟,从火化的烟囱里悠悠地向东方飘去,可能到东瀛蓬莱寻找他的老相好了。
五平体谅老人的心,买了一个较大的骨灰盒,将日元、手表和那件毛衣装进去,埋在了后山上李幺儿坟墓的旁边,一辈子“生同寝死同穴”的还是这对老妻。
2016.12.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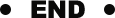
作者:曾凡义,湖北京山县永兴镇水管站退休干部
责编:严彬,笑笑
插图:源于网络
版权为有故事的人所有,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关注“有故事的人”
后台回复以下关键词,看更多故事系列
情感 | 传奇 | 青春 | 幽默 | 鬼故事
匠人 | 职业 | 路上 | 动物 | 家往事
调查特稿 | 苏丹往事 | 殡仪馆 | 缅甸纪实 | 边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