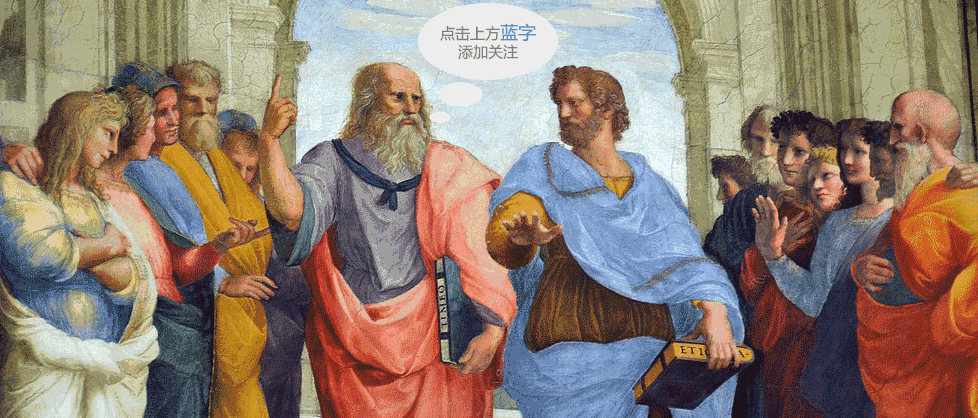
“政治科学”之“家园”——北美访书记
《政治思想史》书评,2011,04,
一、
“
自由基金会
”
礼赞
20
多年前曾在《读书》上读到叶秀山先生的一篇《英伦三月话读书》,谈到作者在伦敦访书的情形,并以在牛津讨论班上所见
“
同学
”
手中彼得
·
斯特劳森的《意义的界限》为例说明英国书价之令人咋舌的程度。
2007
年春夏之交,在时在佛光大学任教的张培伦兄陪同下,我来到几乎可称为台北文化地标之一的诚品书店,并在那里平生第一次不是用人民币买了一本外文书
———
这本书乃是哈贝马斯的晚期弟子雷讷
·
福斯特
(Rainer Forst)
的《正义之语境》
(Contexts of Justice)
。记得培伦兄当时还感叹了一句:以大陆人民教师之
“
低端
”
收入水准,要自费购买牛津剑桥之
“
高端
”
学术产品,委实是太过离谱了。不错,对于像我这样以访书为第一要务的
“
访问学者
”
,书价乃是第一现实的问题。所谓的二手书店在这方面并没有多大的帮助,一者熏染成习、经营有方的店主自然心知肚明于旧书之
“
性价比
”
,从而使
“
捡漏
”
之空间几乎为零
———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我在
STRAND
见到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初版,本想留一册作纪念,但那近
60
美元的价格还是让我望而却步了;二者在纽约这样的
“
世界之都
”
,只消把消费对象部分地定位在像我这样的过客身上,就必定会在相当程度上拉高书价了。在这样的心境下,当我快要离开普林斯顿,在刚搬来
NASSAU
街上的
LAYRINTH
书店见到定价相对低廉的
“
自由基金会
”(Liberty Fund)
出版物时,欣喜之情自然就不言而喻了。以奥克肖特的作品为例,牛津克拉伦顿
2003
年重印的《论人类行为》索价
59.95
美元,而
“
自由基金会
”
版共计
556
个页码的增订版《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及其他论文》却只需
12
美元,这个
“
比例
”
就足以说明这个基金会的出版物对于像我这样的
“
穷书生
”
之吸引力了。
话说《控制国家》是我在翻译生涯的
“
早期
”
主译的一本西方宪政史著作,我曾在此书的译后记中提及黄仁宇先生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主要从经济史角度对威尼斯和荷兰共和国的探讨可与斯科特
·
戈登在《控制国家》中对所谓低地国家的讨论相互比观。其实我在翻译此书题为
“
立宪政府的发展与
17
世纪英格兰的对抗理论
”
之第
7
章时,也时常想起仁宇先生在其大著题为
“
英国
”
的第
4
章开篇的话:
“
英国十七世纪的内战,是历史上一个令人百读不厌的题目。也因其事迹牵涉广泛,各种机遇错综重叠,各方面的记载细腻详尽,所以极不容易分析处理。
”
也许正因为我的英国史素养几乎为零
———
记得在翻译这章时我还特意借来蒋孟引先生的《近代英国史》做参照,我觉得戈登此书对这一个
“
令人百读不厌的题目
”
却是处理得颇为细致精到的。至少自此以后,我就一直对这个议题保持着一种质朴的兴趣。因此,当我在
LAYRINTH
书店见到自由基金会版的《为主权而斗争:十七世纪英国的政治小册子》
(The
Struggle for Sovereignty: Seventeenth-Century English Political Tracts, edited and
with introduction by Joyce Lee Malcolm,1999)
时,我脑中跳出来的就是当年挥汗翻译《控制国家》一书时的情景;或者反过来说,正因为那种磨灭不去的记忆,才让我一下子注意到了这本书。
《为主权而斗争》一书分为两卷:第一卷始于詹姆斯一世登基之初,终于
1660
年的王政复辟前夜;第二卷始于王政复辟,终于由光荣革命引发的争论。编者马尔科姆教授是一位历史学家和宪法学家,她在此书编序中开篇就有句与黄仁宇先生几乎
“
同曲同工
”
的话:
“
一句古老的咒语说: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 an old curse goes)
。十七世纪的英国是个不折不扣的乱离之世。然而与大多数乱离之世不同,它并不是个黑暗时代;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取得伟大智识成就的时代。
”
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政治思想领域,而如书名所示,马尔科姆教授把
17
世纪英国政治思想的核心主题界定为
“
关于政治主权之来源和性质的一种根本的智识论争
”
。她尤其强调,在
“
一个声称具有一种统辖着有限君主制的
‘
绝对
’
君主制王国
”
中,关于混合政体中主权来源的争论不但在学者、政治家、法律家之间展开,而且在教士、政府宣传人员以及相关人士之间展开,他们
“
奋笔疾书、开动脑筋、下笔千言
”(snatched pens,racked their brains,and
wrote),
而小册子无疑是最适合这种争论之紧迫性的书写形式,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当然是
“
议会首屈一指的宣传家
”
亨利
·
帕克回应查理一世之《答复》的《对国王最近之庄严答复和文件的评论》、支持议会的清教史学家菲利普
·
亨顿的《论君主制》,以及一位匿名作者的被誉为
“
宪政话语成为英国人政治思想之一条主要渠道
”
的《政治问答集》(也称《关于这个国家的政府的某些问题,答国王之堂皇言辞》)。
马尔科姆编纂此书是为了扩展广大读者对于
17
世纪政治思想的一般知识,她也相信这些文本提供了
“
评价洛克、弥尔顿、霍布斯和费尔默之思想的一种更为可靠的语境
”
。在谈到此书的编选原则时,她着重指出,这个选集将把焦点集中在所争论的问题,而不在于展现雄辩的政治写作样本。换句话说,选择文本之标准
“
不但在于提出对议题的最佳论证,而且在于有说服力的和简洁的论证
”
。还是以帕克为例,之所以在这个文集中选入他的《论船税案》一文,而不是他的其他卓越的和富有影响力的文章,就是基于这个篇章
“
最好地刻画了他同辈中的许多人从强加他们所谓不法之税中看到的严重宪政后果
”
。同样,
“
平等派
”(levellers)
之所以被忽略,并不是因为他们不重要,而是因为他们的文本被频繁重印,从而得之甚易。仅从此点即可看出,这个选本不但富有思想史的旨趣,而且深具文献学的价值。
“
自由基金会
”
出版物中有一套
“
自然法与启蒙运动经典
”
,这无疑是一套大书,不过我只得到了这个丛书中普芬道夫的三本书,分别是《从自然法论人的全部责任》
(The Whole Duty of Man,According to the Law of Nature,translated by Andrew
Tooke, 1691, edited and with introduction by Ian Hunter and David Saunders, and
Two Discourses and a Commentary by Jean Barbeyrac, translated by David Saunders,
2003)
、《与公民社会相关的宗教之性状》
(Of the Nature and Qualification of
Religion in Reference to Civil Society, edited and with introduction by Simone Zurbuchen,
2002)
以及《神圣的封建法:或与选民之约》
(The Divine Feudal Law: Or, Covenants
with Mankind, Represented, edited and with introduction by Simone Zurbuchen,2002)
。这其中最为中文读者熟知的是普氏的第一种著作,此书目前的英文
“
标准版本
”
是昆廷
·
斯金纳为总主编、詹姆斯
·
塔利为分卷主编的
“
剑桥政治思想史文本
”
版,不过这个版本略去了自由基金会版中巴贝拉克
(Jean Barbeyrac)
的《两个对话和一个评论》。据译者桑德斯介绍,普芬道夫的拉丁文著作在
18
世纪的传播在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巴贝拉克的法文翻译、注释和评论;而且,作为一个政论家和护教学家,巴贝拉克对于由后经院哲学的新教自然法所引发的智识争论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是有他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的。事实上,《一个匿名作者的意见》和另两论(《论法之所许》以及《论法所授之利益》)从
1718
年起就作为附录出现在《从自然法论人的全部责任》之法文译本的第四版中。前者实际上是莱布尼茨、普芬道夫和巴贝拉克的三方对话,在这场对话中,莱布尼茨作为一位匿名作者出现,普芬道夫被称做
“
我们的作者
”
,而巴贝拉克则以第一人称发声。这个三方对话颇有助于我们如临其境地把握这场关于自然法的早期现代争论之智识氛围。
最后还是要回到我前面提到的奥克肖特,我所收的自由基金会版的奥氏作品,除了《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及其他论文》
,
还有《论历史及其他》
(O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foreword by Timothy Fuller,1999)
以及《霍布斯论公民联合》
(Hobbes
on Civil Association,foreword by Paul Franco,1937/1975),
不过装帧最为雅致、其内容也给我留下最为深刻印象的却是一册我初见之下不知怎样翻译书名的
The Voice of Liberal Learning(foreword and introduction by Timothy
Fuller,2001)
。此书其实并非自由基金会首版,而是根据耶鲁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的版本重印的。据奥氏的学生富勒在为自由基金会版所撰序言中介绍,他是在
1987
年动念编辑这个选集的,其时,阿兰·布鲁姆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和赫希
(E.d.Hirsch)
的《文化这回事》分别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的前两名,并支配了关于美国教育问题的争论。富勒和他的出版人认为把奥克肖特论述教育问题的文字编为一帙面世,能够为关于教育的争论提供一种不同的和补充性的视角。行笔至此,我不禁想起在去年的博士生面试上,我问一位硕士论文做奥克肖特的考生这样一个问题:在目前中文政治哲学的甚至更为宽泛的公共领域的讨论中引入奥克肖特的思想资源具有怎样的意义?大概由于这位考生面对我的
“
劈头一问
”
过于紧张,没有能够领会我的
“
微言大义
”
。话说我虽非奥克肖特的研究者,但貌似在这个问题上,竟确是有
“
不已于言者
”
,这却是要稍费周章才能说明的。
大概是
2009
年的
9
、
10
月间,我收到高雄中山大学曾国祥教授寄赠的《主体危机与理性批判:自由主义的保守诠释》(巨流图书公司)一著。国祥教授从奥克肖特任教过的伦敦经济学院以关于奥氏思想的研究取得博士学位,此书汇集了他在政治思想史和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的
9
篇论文,而其基本的宗旨和归趣,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乃是从
“
一位奥克肖特主义者
”
的立场对保守主义的
“
正本清源
”
,提出所谓
“
哲学的保守主义和实践的自由主义
”
。特别引起我注意的,乃是此书中有一篇题为《教育典范与国家形态:奥克肖特思想中的自由与自我》的文字,这可能是汉语学界对奥克肖特之教育思想仅有的系统论述
———
作者在文中采取陆有铨所译赫钦斯
(R.M.Hutchins)
《民主社会中教育上的冲突》的译法,把
“liberal education”
一语译为
“
博雅教育
”
,于是奥克肖特前述的那本书可译成《博雅教育的声音》。作为中文世界极少数的奥克肖特专家,国祥教授论述之绵密和精深自不待言,不过令我感到稍有憾意的是作者通篇中竟未有一处使用
“
古今之争
”
一语。
两周前,一位我相交甚久的近年名声颇振的法政哲学学者来本校参加一个有关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学术会议,由于这位学者正在京中某校司职
“
博雅教育
”
,我于是请问他对这个议题的见解。我的这位朋友一向
“
阶级斗争觉悟
”
甚高,于是一语道破
“
天机
”
:大体
“
博雅教育
”
有偏重文史,也有偏重法政的;就国内格局而言,大体前者是反现代性的,后者是现代的
———
或者用他近年雅好使用的一个词,就是早期现代的。我在这里并不想用我在其他场合
“
批评
”
他时用过的语言来批评他,我只是想起了,如果富勒在为自由基金会版的《博雅教育的声音》所撰序言中所谓奥克肖特要在
“
无远弗届的抱负
”(progressive aspirations)
和
“
亘古不变的真理
”(perennial truth)
之间走出
“
第三条道路
”
的说法所言非虚,那么奥克肖特的
“
博雅教育
”
乃正是
“
不古不今
”
的。
二、从文化政治到政治文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
“
按图索骥
”———
按照事先开列好的书单去
“
手到擒来
”
不是完全取消了至少也在相当程度上减损了访书的乐趣,特别是如果我们把这种乐趣主要界定为如
“
艳遇
”
般的总是有
“
意外之喜
”
的
“
不期而遇
”
。
虽然一个中国学者或许总是会对《文化绝望的政治》这样的书名感到
“
似曾相识
”
,但老实说,以研究
“
德意志意识形态
”
著称的哥伦比亚大学老牌历史学家弗兰茨
·
斯特恩
(FritzStern)
的工作长期以来并不在我的视野之内。不过,也许正是拜自己生长于斯教养于斯的文化为我们塑造的
“
敏感
”
之所赐,当我
2008
年
4
月在
LAYRINTH
的书架上见到斯特恩的这本书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 A Study in the Rise of the
GermanicIde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1989)
时,就仿佛自己的某根神经受到了猛然的触动,于是同一个架子上的《非自由主义的失败:论近代德国政治文化》化》
(The Failure of Illiberalism:Essays 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Modern Germa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New
York:Knopf,1972)
也顺带着被我收入行囊中。说起来,我对于
“
德国问题
”
之关注既不是由于高全喜兄
“
中国问题就是德国问题
”
之高论的
“
误导
”
,当然也不是从在异国他乡
“
邂逅
”
斯特恩的著作后开始的。事实上,有关德国史的中文译品,从梅尼克的《德国的浩劫》到最近温克勒的《永远活在希特勒的阴影下吗?》都是在第一时间就被我关注和阅读的。记得在《批判的踪迹:访
MIT
出版社书店》一文中,我曾经
“
自爆
”
:
“
我虽不专事德国哲学研究,批判理论也非我所长,但从大学时代开始,我就一直对它们有持续的关注。
”
在我后来
“
阴差阳错
”
地有机会翻译与哈贝马斯亦师亦友的韦尔默之著述时,我就注意到他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今意义:五个提纲》一文中谈到以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为代表的
“
西方
”
马克思主义在战后德国智识和舆论界的几乎
“
一枝独秀
”
的地位时,曾经颇为动情地说:
“
从对于联邦共和国的文化影响上说,阿多诺不只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批评家和哲学评论家,他还是在反动政治的损害后恢复德国文化传统的本真性,并使之进入在道德上受到困扰、其认同被动摇的战后一代人意识之中的第一人。就仿佛被纳粹驱逐出去的这些智识人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维护德国的文化认同。阿多诺再一次使德国人用不着在智识上、道德上和美学上仇视康德、黑格尔、巴赫、贝多芬、歌德或荷尔德林。就这样,阿多诺在赋予
‘
另一个德国
’
以正当性上比任何人做得更多,而这个词本来常常是带着抱歉的口吻使用的。
”
在经历了与形形色色的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特别是所谓
“
决断论
”(decisionism)
与
“
机缘论
”(occasionalism)
的毕生奋争之后,哈贝马斯最终把现代性规范内涵之锚泊定在它的政治维度上,这尤其表现在作为《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之附录发表的《公民身份和民族认同》以及此后的政治哲学文集《包容他者》和《后民族的格局》中。按照童世骏教授的阐释,哈贝马斯所有这些论著集中围绕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理解现代社会的集体认同问题,在区分了
“
以建制为中心
”
的集体认同观、
“
以文化为中心
”
的集体认同观(如中国近代的文化民族主义)和
“
以人格为中心
”
的集体认同观(如中国近代的种族民族主义,或许还可以包括世界主义)之后,童教授还着重指出,在对于理解这个问题至关重要的政治文化概念中,至关重要的又是这样一个区分,即与政治物相关的文化与以政治的方式做成的文化之间的区分。确实,对于一方面要重新回到西方(温克勒的代表作即为两卷本的《迈向西方的长路》),另一方面又要保持德国文化认同之本真性的柏林共和国来说,这个区分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
话说回来,虽然弗朗茨
(Constantin Frantz)
早在
1866
年就有言:
“
德国问题是整个近代史上最难解、最纠结和最全局性的问题
”
,而弗朗茨此语也曾在
1945
年被罗普克
(Wilhelm R pke)
用作他关于德国问题的同名文章之题铭,但在我有限的视野中,最明确地标举
“
德国问题
”
的仍然是在
1990
年《东欧革命反思录》中指陈
“1989
年的意义不在于一种特定的制度战胜另一种特定的制度,而在于
‘
开放社会
’
战胜
‘
封闭社会
’”
的德裔英籍社会学家达伦多夫
(Ralf Dahrendorf)
。虽然达伦多夫早早就退出了德国社会学界,移居英伦并以殊荣终老
“
日不落帝国
”
,但从学理深度和精神气质上,他可谓哈贝马斯终生的
“
对手
”
和道友。
1965
年出版的《德国的社会和民主》
(Gesellschaft und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R.Piper&Co.Verlag,München,1965;
英文版由作者本人翻译:
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1967)
一书第一部分就题为
“
德国问题
”
。我是在前节提到过的普大那家二手书店发现达伦多夫此书的英文版的(和威尔第的《弄臣》还有王尔德的配有比雷兹亚插图的《莎乐美》一起)。记得收完此书带着一种无比满足的心情在校园内闲逛时,还在哲学系和人类价值中心所在的
MARXHALL
附近遇到了佩蒂特教授,由于
“
无话可讲
”
,我只好从背包里拿出此书向他
“
炫耀
”
,引得他频频点头,并露出一丝爱尔兰人的
“
狡黠
”
微笑。
毫不令人意外地,达伦多夫在此书中不时把自己的工作与托克维尔之论美国的民主相比照,他简洁明快地把德国问题理解为德国的民主问题。不过颇为耐人寻味的是,在此书德文版的序言中,达伦多夫写道:
“
我们所谓民主,与托克维尔所指稍有不同,是自由派的
(liberté)
民主,而不是平等派的
(égalité)
民主,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治社会,而不是一个平等主义的社会。
”
在这篇序言中,他还特别指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