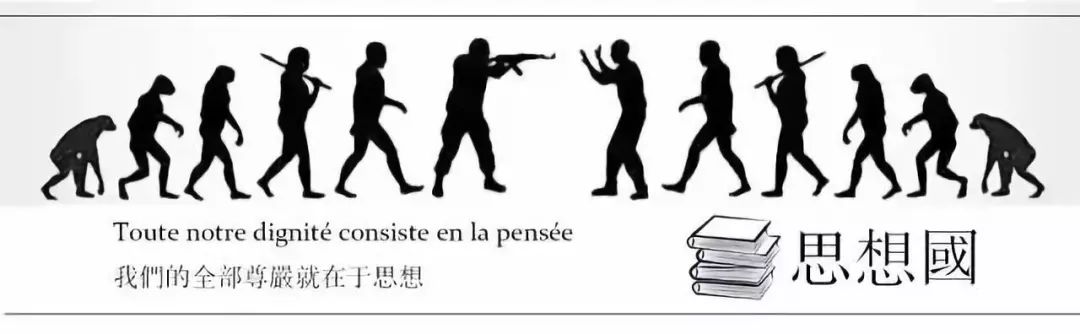

点击进入
《寒山》(《我是一个连环杀手》)——熊培云首部诗歌电影短片观赏
有些事情并不能决定于一个人的意志或奋斗,比如政治自由。有没有投票权不是你能决定的。它需要整个时代的合谋或者共同努力。
而有些自由却可能直接通过个人奋斗
解决,比如时间自由、身心自由或财务自由等等。前提是,这个社会要足够开放,并且不因某种倒退让崇尚个人奋斗者束手束脚,甚至日日挑雪填井,终于空欢喜一场。
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当然是既有时间自由、身心自由,同时又有财务自由。而事实上,很多时候为了一种自由
我们不得不
牺牲其他自由。这是人的逆境。比如,为接近或实现财务自由,我们将时间自由与身心自由都抛弃了。或者,只是为了身心自由,而不得不过上某种穷困潦倒的生活。结果可能是,作为物质的人少了物质的支撑,最后连身心自由都一起失去了。
在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时人谈论最多也最焦虑的当属财务自由。
何为财务自由(Financial freedom)?通常的解释是指人无需为生活开销而努力为钱工作的状态。甚至,有人还画出了一个简单而枯燥的公式:
财务自由= 被动收入 > 花销
所谓被动收入,也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做,钱就能够进到你的口袋里。
理论上,一个人有了财务自由,也就更接近于时间自由和身心自由。现实是我们总有赚不够的钱,而且在心理上最好还能翻倍。有一万想两万,一百万想两百万,一千万想两千万,一亿想两亿。总之,无论有多少钱最后都会回到那个计数的起点一。
当每日继续被大量的事情填满,想一想有多久没有悠闲地下一局棋,读一本书,看一次落日,做一次漫无无目的的远行。

最近几日返乡,见了一些朋友,也让我对财务自由有了更多思考。
首先,我承认有绝对财务奴役的存在。比如,最基本生活保障的缺失。如果一个人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守不住,却说自己拥有财务自由,这显然有些自欺欺人了。
而接下来我更想说的是,在满足基本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绝对需求之外,人们经常讨论的财务自由更多可能只是一个相对概念。
在个体层面,我们难免会以自己在所处群体中的财富地位来衡量是否拥有财务自由。比如生活在年收入1万的人群当中,一个年收入十万的人会感觉自己在财务上是相对自由的,因为他明显比他人多出了9万。而他在年收入百万的人群中,则会有一种相对剥夺感,财务也是不自由,因为不吃不喝也赶不上人家。
此时,财务自由甚至被直接换算成了购买力。在一个只能买自行车的世界里,如果你有买摩托车的欲望并且有能力自我满足,你会感受到相对财务自由的存在。而如果继续向上看,情形就变得不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