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正厉害的,
不是那些可以随口拿来夸耀的事迹,
而是那些在困境中依然保持微笑的凡人。”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好报"(ID:haobaonet)
知乎网曾举办过一个讨论,叫做:
“你觉得自己牛逼在哪”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把他的自身经历写在网上,
瞬间让其他网友的回答都弱爆了:
“我吃过猪都不吃的药,
扎过带电流的针,
练过神乎其神的气功,
甚至还住过全是弃儿的孤儿院。
二十年间,
我的病危通知单,
厚厚一沓纸,
老妈用一根十厘米长的钉子钉在墙上,
说很有纪念意义。”

我们都追求与众不同,他却十分渴望与别人“相同”,
我们随意挥霍的今天,曾是他渴望的明天。
2013年8月21日,
这个自谑为“宅界巨子”“职业病人”的小伙子,
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数十万网友自发哀悼,
东东枪、于莺、章诒和、李开复、蒋方舟、任泉等名人明星,
也都在微博上感动留言。
“跟他比,我们大多数人都活得太轻薄了。”东东枪在微博写道。
演员任泉评论说:“你在这个世界上,有人知道你牛过!我算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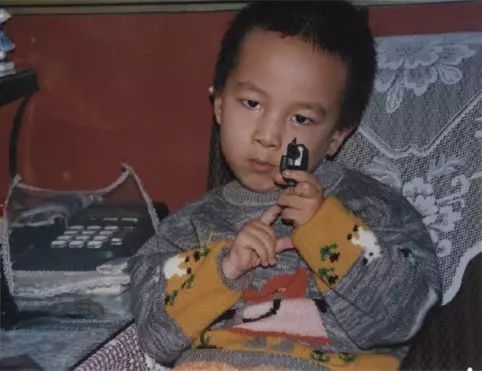
他叫程浩,
1993年出生在新疆博尔塔拉一个普通家庭,
六个月的时候,家人发现他跟别的孩子不同,
他不踢不蹬不翻滚,
辗转多家医院检查,从石河子到乌鲁木齐,从北京到天津,
医生都无法查出明确的病因,只断定他活不过五岁。
医生建议家属放弃他,族中长辈也劝他母亲再生养一个。
他母亲说:
“不管孩子怎样,
既然我把他生下来,我就要把他养大。
老天夺走他多少,我就用爱来弥补他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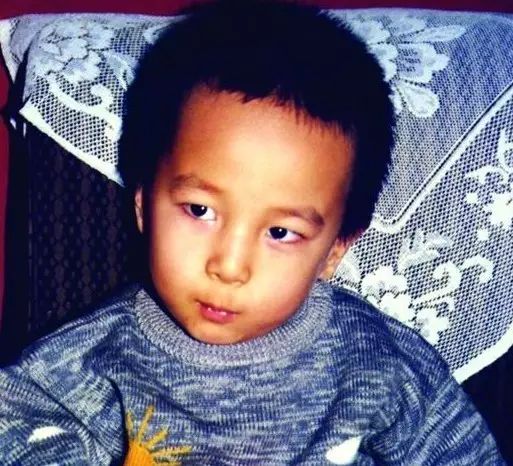
他母亲带他到处求医问药,
直到三四岁都没有结果也没有效果。
他母亲看他胖乎乎的,没什么不正常,
也就暂停了折磨人的看病过程。
他父亲是一名旅游司机,每年大江南北四处奔波,
他母亲身兼数个公司的会计,地点相隔数百公里,
每月有一半时间要花费在路上,
五岁之前,他多由爷爷奶奶带着,
五岁之后,他母亲把他接回身边,一边工作一边带着,
并给他请了家庭教师,弥补他不能像同龄人那样上学的缺憾。
老师教完他拼音就辞职了。
他母亲给他买了字典,母亲做饭,他就自己翻字典,
遇到不懂的吃饭时再问,他母亲边给他喂饭边教他。
他饭量小,但每顿饭都要吃一个半小时,
“他嘴巴只能半张,要是不会喂的话,根本送不到嘴里,
吞咽的肌肉好像也有点萎缩,你稍微急点,他就会呛着。”
他母亲边给他慢慢喂饭边教他认字。
对于常人来说毫不费力的吃喝拉撒,他一辈子都要仰仗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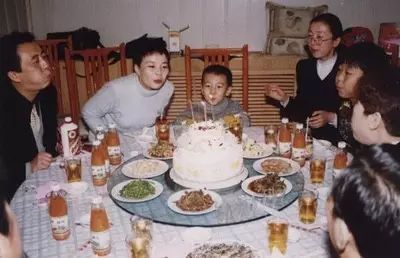
六岁,在石河子的酒店过生日,那时的他还能自己坐在凳子上
六岁后,母亲给他添了个妹妹,
作为一个哥哥,不能保护妹妹,反倒要她照顾自己,
这让他感到愧疚。
去世后,他的墓碑上写的是“哥哥程浩之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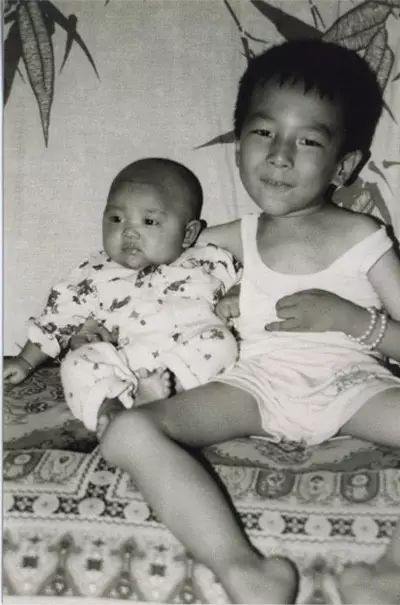
八岁那年,他第一次和家人去石河子南山滑雪,
那时已不能自己坐,所以爸爸抱着他玩的爬犁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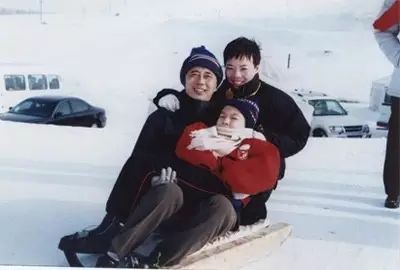
电脑刚出来时,他母亲给他买了一台,那时他九岁。
此后,电脑便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朋友。
也在九岁那年,他父母收到他第一张病危通知单,
之后,基本每年病危两次。
十二岁那年,他第一次胃出血,
八天八夜水米未进,吃进去的东西原样吐出,
医生断言:“再这样下去不是病死的,也是饿死的。”
他母亲守了他三天三夜,
他求生意志强烈,逃过了死神,护士笑说他又活过来了,
他说:“阎王嫌我太善良,上帝嫌我太混账,
他们都不肯收留我,没办法我只能回到人间。”
此后出院,他能活动的范围更小,
除了医院,常常三四个月才出一次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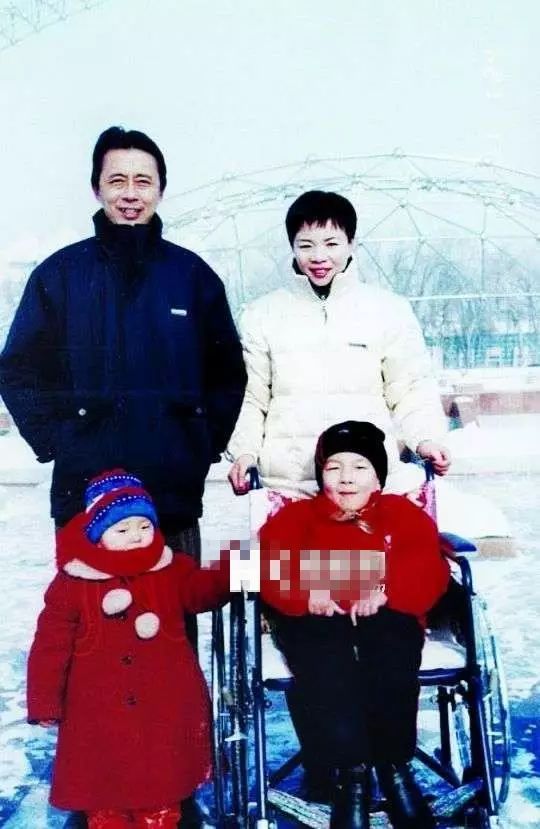
他没有抱怨,还常笑说是他父母一生跑了太多路,
最后使他“无路可走”。
有句话说:“上帝关了你一扇门,他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他没法像普通人那样出门,没法像同龄人那样上学,
但他有更多时间读自己喜欢的书。
他从十岁起第一次独立阅读长篇小说开始,
便保持着每天不少于四个小时的阅读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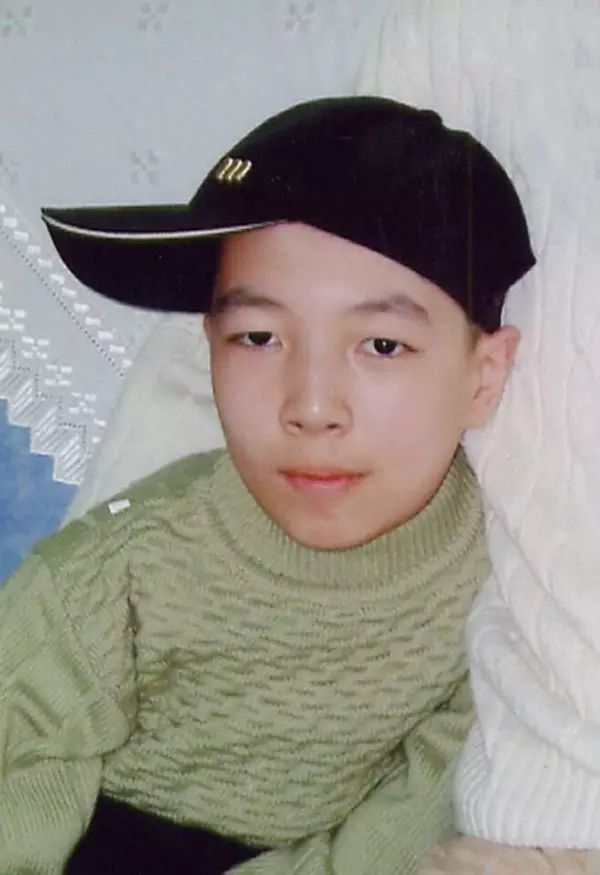
十四岁的他,已经成长为多思的少年,
经常出入医院的他把死看得很轻很淡,思想比同龄的孩子成熟。
家人曾说命运对他不公平,
小小年纪的他反倒安慰说:
“运命嘛,休论公道。
不幸与幸运一样,都需要有人承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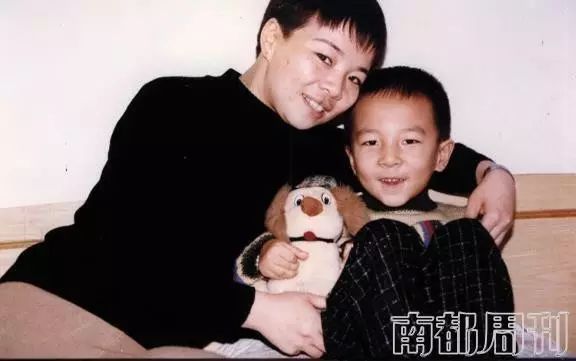
他不惧怕死亡,
但害怕上帝丢给他太多理想,却忘了给他完成理想的时间。
他的理想是做一个像斯蒂芬.金那样善于讲故事的人。
“生命之残酷,在于其短暂;
生命之可贵,亦在于其短暂。”
他给自己制定了更严苛的计划——每天必须阅读十万字,
阅读的内容已从早期的韩寒郭敬明七堇年笛安,
转变成《1984》《胡适文选》《民主的细节》等。
上午阅读,下午写作。
他已无法承受一本纸质书的重量,
只能在网络上阅读或读电子书,
他写作是用鼠标在软键盘上一个一个点出来,
写得很慢,很吃力,
他不想经常麻烦别人,长时间保持一个动作,
直到累得扛不住才叫母亲帮他翻身、换个姿势。

读书是他认真生活的表达方式,
写作是他寻找到的一条“自我救赎”之路。
他把尼采的话当成自己的格言:
“凡是不能毁灭我的,必使我强大。”

程浩的微博
“我未必能成为作家,未必能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
但是我必须坚持写作这个行为,
因为我不想让自己身上的伤痕变得毫无意义。
看着这些淤青,我就能想起曾经的日日夜夜,
想起曾经的自己。
若放弃写作,
则是对之前付出的一切表示否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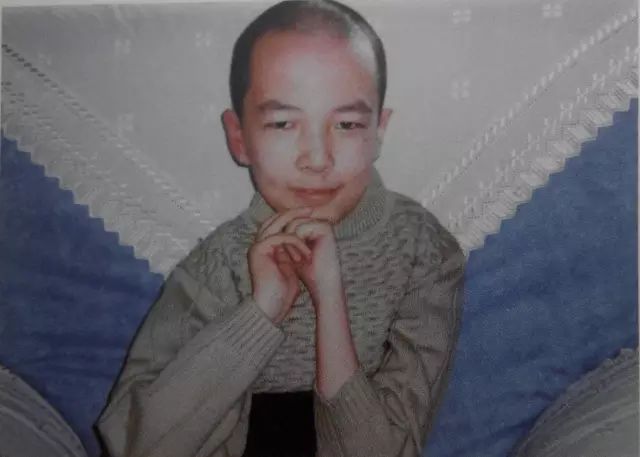
他的不甘心,他的坚持,让他在2013年二十岁生日前,
看到了希望。
他的《昂着头的艺术》被刊登在《全球商业经典》,
他在知乎对“你觉得自己牛逼在哪儿?为什会这样觉得?”的回答
刷新了知乎的纪录:
24小时获得2000+点赞、500+评论,
私信和留言像潮水般向他涌去。
“真正牛逼的,不是那些可以随口拿来夸耀的事迹,
而是那些在困境中依然保持微笑的凡人。”
这是他在知乎的那个著名的回答。
他在知乎拥有了个人专栏,
有人被他的文字感动了,
也有人在他的文字中获得力量。

他去世第二天,他母亲接到一个男孩哭着打来的电话:
“阿姨,我真的对生活都绝望了,
是程浩把我从病魔手里拉了回来,让我对生活恢复了信心。
我没想到他竟然走在我前面。
我心里真的特别特别难受,
要不是他,我可能会走在他的前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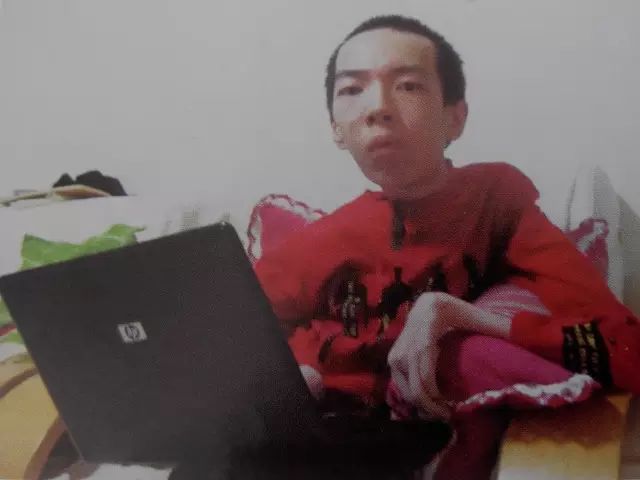
有网友说他很励志,
他觉得自己只是做了该做的,能做的,
他反感别人给他贴“身残志坚”“自强不息”这样的标签。
“难道因为疾病,每个人就要活得垂头丧气、萎靡不振吗?”
他想活着,活好,爱人,被爱,被需要,
尽量不麻烦别人,最好还能帮助到别人。
他经常跟他母亲说:
“妈妈,要是我死了,把我的眼角膜捐出去。
把我的遗体捐出去做解剖。
解剖了我,找出病因,找到疗法,能救好多人。
不然你把我埋掉,跟垃圾有什么区别。”
捐眼角膜,让需要的人重见光明,
这是他的愿望,
另一个愿望是,
去北影导演系听课,哪怕一天。

但是,这些愿望都没能实现。
对我们来说一个小小的感冒,
对他来说都有可能是一次致命伤,
他的左肺只是一个扁条,只要感冒,“呼吸都是一种奢侈。”
2013年8月18号,在一次感冒之后,
带着呼吸机依然微笑的他,
三天后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去世前一个网友给他写了一封邮件,
问他:“一个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为什么要忍受那么多痛苦?”
他没有直接回复网友,写了一篇《地狱在身后》贴在知乎上,
这成了他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章。
“也许我们无法明白‘活着’的意义,
但是我们已经为‘活着’付出太多代价;
也许我们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
但是我们已经为梦想流下了太多泪水。
我们能做的,仅仅是在这条路上
走得更远,
绝不回头。
天堂未必在前方,但地狱一定在身后。”
程浩走后,
他母亲帮他整理电脑里遗留的文字,
没上过一天学校的他,
写有专栏文章,有日记,有读书笔记,
更有大量未完成的作品,
大概44万字。
这些作品,
都是他在生命最后两三年用鼠标一下一下点出来的。
他生前最大的心愿是出书,
“你看别人都说自己惨,
等他们看到我,就不会觉得自己惨了,
我没有白出生。”
“如果有一天,我出书了,
我会取名叫《站在两个世界的边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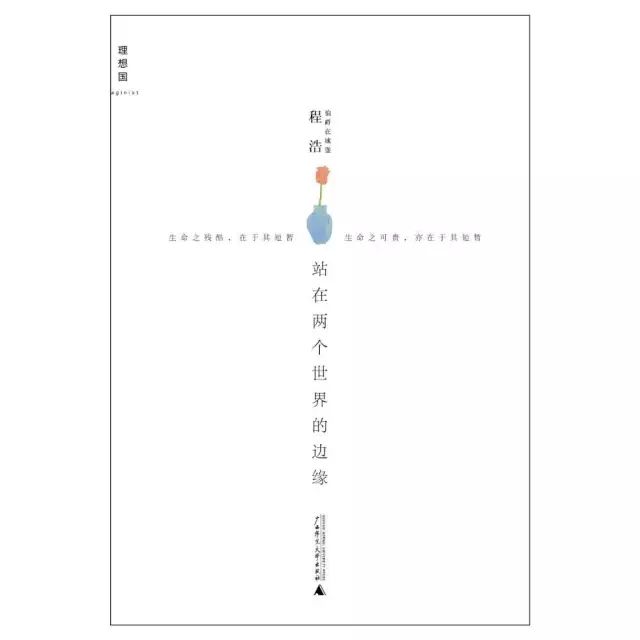
他母亲帮他完成了这个心愿,
我们看到了《站在两个世界的边缘》,
封面上这朵梵高底色的玫瑰花是他生前所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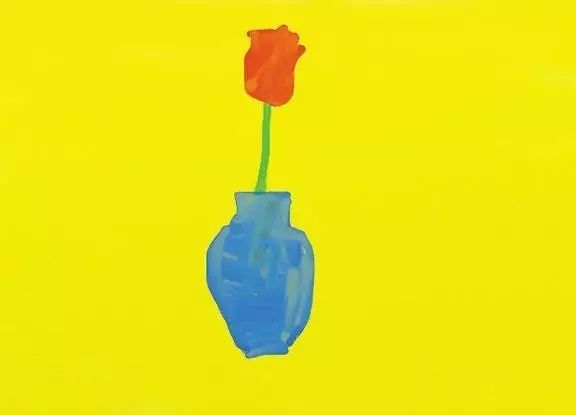
还有一部十余万字的日记——《生命的单行道:程浩日记》。
有人问:“人终有一死,现在的奔波劳累有什么意义?”
他反问:“难道因为死亡是人生的终点,我们就要放弃生命的过程吗?”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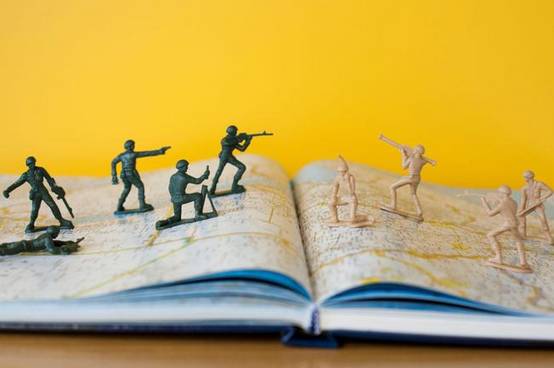 点击图片阅读 | 当罗尔成为网络上的权力者,他不是骗子很重要
点击图片阅读 | 当罗尔成为网络上的权力者,他不是骗子很重要

点击图片阅读 | 少扯没用的大道理,人生其实就八个字

点击图片阅读 | 高房价究竟在制造中产阶级,还是在消灭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