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标志,美国政坛掀起了新一页。被公知粉饰的各种高大上外衣被一层层撕去,露出党争、内斗、阴谋、倾轧的政治大戏,让人应接不暇。
如果将表现美国政治内幕的电视剧《纸牌屋》与现实一比,不禁让人感叹:
艺术来源于生活,居然tm还不如生活精彩。

其实,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坛,才是“民主政治”的本来面目。美国政治制度继承自其前宗主国英国,在英国这种以党划线,党同伐异的残酷政治倾轧更是历史悠久,其中一个典型时期就是都铎王朝,特别是本篇主角托马斯·克伦威尔登上历史舞台之后。让我们来看看都铎时代的“纸牌屋”都发生了什么。
托马斯·莫尔执掌大权后,露出比沃尔西更加凶恶的面孔。新教徒们甚至有些怀念沃尔西的时代,虽然他贪腐,但是他还有些人性;而莫尔私德高尚,清廉如水,却穷凶极恶地烧书烧人,更衬托出他没有人性的恶魔本质!
在宫廷上层,亨利八世则对于莫尔的不为己用和辜负信任,深感恼怒。而安妮·博林目的是要将英国变成新教国家,莫尔上台后却大肆迫害新教徒,成了比沃尔西更强硬的障碍,必须将其粉碎。
在朝野上下强大的压力之下,莫尔被迫于1532年辞去大法官职务。安妮·博林借机将自己的盟友托马斯·克伦威尔扶上首席国务大臣的位置,成为英国政坛的权力核心。以克伦威尔上台为标志,英国宗教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
中国人通常熟知的那个克伦威尔,砍了国王查理一世,自己当“护国主”,叫做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年),比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约1485年-1540年7月28日)晚了一百多年,是十七世纪清教革命(或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关键人物。
这两个克伦威尔都是著名权臣,都曾在英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可能有人会好奇,这两个克伦威尔之间有关系吗?

“护国主”奥利弗·克伦威尔
还真有。托马斯•克伦威尔的外甥理查德,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曾祖父。理查德是托马斯•克伦威尔的姐姐凯瑟琳和其丈夫摩根•威廉姆斯的儿子,1528年那场险些使得安妮·博林挂掉的汗热病瘟疫,夺走了克伦威尔的妻子和两个幼女以及姐姐姐夫的生命,于是理查德被克伦威尔收为继子。克伦威尔还有一个亲生儿子,他不忍儿子沾染政治的肮脏,始终没有让儿子从政。
有一次他自嘲地与儿子对话:“有个给安妮·博林跑腿的傻小子,我听他说我看起来像个杀人犯。”儿子的回答是:“你难道不是吗?”可以看出,克伦威尔的儿子完全不理解其父的内心世界。
但是理查德则不同,他被克伦威尔当作助手,并被作为其衣钵继承人而着力培养。理查德把自己的姓改成了克伦威尔。托马斯•克伦威尔死后,理查德继承了其主要遗产和爵位,并一直传到奥利弗。从家族传承的角度来说,说奥利弗是托马斯的后代也无不可。奥利弗从小将托马斯·克伦威尔作为榜样,其行事风格,也处处存在着模仿着这位先祖的痕迹。
托马斯·克伦威尔从政期间,历任财政大臣、掌玺大臣、首席国务大臣,获封艾萨克斯伯爵,亨利八世身边第一权臣,被誉为亨利八世的“右臂”。他是英国宗教改革的坚定拥护者,是英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甚至有人称其为第一位近代政治家。他才是英国宗教改革的真正操盘手和掌舵人!

托马斯·克伦威尔
1485年,也就是亨利七世击败约克家族的理查三世,定鼎江山的那一年,
托马斯·克伦威尔生于伦敦的一个平民之家。托马斯的父亲沃尔特·克伦威尔是个白手起家的工厂主,他拥有一家啤酒厂,并在一家缩绒机厂或者也可能是一家铁匠铺有点股份,相对富裕的家境使得克伦威尔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
然而,他父亲是一个典型的酗酒后爱发酒疯的英国男人,克伦威尔小时候一言不合就要被他爹揍,特别是在他爹喝酒以后。克伦威尔一方面继承了父亲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其生活环境又造就了独立、叛逆的性格,而他骨子里又被打上了崇尚专制暴力的烙印。
大约在他十五岁的时候,大约是再也受不了专制暴力的父亲,克伦威尔离开英国去外面闯荡,这段时间他的经历是个谜,据他自述,是作为法国的雇佣军赴意大利参战,并随军在意大利参与了政治活动。对于这几年的黑暗经历,他曾用一句话概括:“年轻的时候我是个恶棍”。
随着法国的战败,他作为一位佛罗伦萨银行家的随从留在了意大利。很快,克伦威尔因为头脑灵活和表达能力出众获得提拔。三十岁之前,他已经在威尼斯、罗马和安特卫普崭露头角,成为一个银行家、实习律师以及羊毛交易经纪人。当他在三十岁左右返回伦敦后,很快就因为精明能干,得到同样出身平民的大主教沃尔西的赏识,被他选作助手并作为接班人着力培养。
在克伦威尔同时代人的眼中,他有着天然的魅力和敏捷的社交手段,并且思想前卫、乐于取悦别人,言谈举止风趣得体,他的精力似乎永无止境。
在优雅风趣的面具之下,隐藏着一颗强硬、多疑、冷酷的内心。
克伦威尔在国外漂泊的这些年,使他见识了人世间的各种险恶,塑造了他狐疑善变、冷酷无情的性格;而他从商过程中接触到很多持新教思想的人,在他们的影响下,克伦威尔成为一名坚定的新教徒。
新教与天主教的对抗,绝不仅仅是宗教信仰不同那么简单,而是新兴而又雄心勃勃的资产阶级新贵 ,向行将没落却又专横跋扈的老贵族发起全面挑战。像沃尔西和克伦威尔这样的人,拥有巨大的金钱与权力,却因为出身低贱,被那些拥有悠久历史的老贵族肆意轻贱,甚至当面出言侮辱。在克伦威尔看来,这帮纨绔子弟不过是一帮依靠祖宗荫庇,自命不凡却又眼高手低的废物而已。
致力于推动宗教改革的安妮·博林,到处物色得力帮手,很快注意到大主教沃尔西身边的这个精明强干的助手,在接触和试探的过程中,发现他和自己一样是坚定的新教徒,于是向他伸出了橄榄枝,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同盟。
当时安妮·博林已经是亨利八世的心头肉,很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王后,克伦威尔自然看出,这是一个绝佳的向上爬的机会。尽管他也知道,博林家族在扳倒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沃尔西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错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因此他仍然接过了安妮抛过来的橄榄枝。
于是,安妮·博林、托马斯·克伦威尔和托马斯·克兰麦结成了三头同盟,成为驱动英国宗教改革的核心力量。安妮·博林身后站着的诺福克公爵、安妮·博林的父亲兄弟等人,也因为利益捆绑加入进来,共同形成了国王身边的改革派集团。
其中,诺福克公爵虽然是旧贵族又是天主教徒,但由于他是安妮的舅舅,为了权势,只能暂时忘记自己的信仰,成为改革派的一员。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新教改革派”的这些人能走到一起来,除了为了“志同道合的理想”,更多的是为了共同的利益。理想固然重要,但是共同的利益基础,才是干事业的基石!
在沃尔西失势的1529年,克伦威尔当选为国会议员。克伦威尔还来不及为沃尔西的凄惨下场感到悲伤,就马不停蹄地投入激烈的政治斗争中。
当时旧贵族已经式微,上议院被天主教会的高层把持。以罗切斯特主教约翰·费舍尔为首的上议院坚决反对国王亨利八世的离婚案,认为国王没有得到罗马教皇的批准一意孤行与王后离婚,最终只能导致英国教会和罗马教廷的对立,亨利八世的做法将毁灭英国教会。
这些人如此反对国王离婚再娶,其实并不是对国王的性生活有多大意见,或者对天主教有多虔诚,出发点还是自身的利益。
都铎王朝建立以来与新兴资产阶级结盟,大力打击旧势力,旧贵族在亨利七世手下哀嚎遍野,人被杀得七零八落,财产被没收充公,幸存下来的旧贵族无不对都铎王权恨得咬牙切齿。
亨利八世上台以来表面上比他爹宽厚,但是白金汉公爵突然倒台让旧贵族明白,亨利八世平时和蔼可亲的面孔,随时可能变成令人不寒而栗的另一副模样。天主教士阶层对于旧贵族的遭遇本就有兔死狐悲之感,再加上亨利八世对修道院财富的垂涎之心已是昭然若揭,他们无不心存强烈不安。
因此,旧贵族和天主教士们心中都巴不得天杀的都铎王朝赶紧倒台。现在居然出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机会能让都铎王室绝嗣,这么好的机会还不赶紧抓住?说什么也不能让国王诞下男丁!
这样一来,大家就没得谈了。在英国国会的框架之下,不能“友好协商”,那就只能党同伐异,肉体清洗。
用政治铁腕搞人,正是克伦威尔最拿手的的本领。
克伦威尔的第一步任务,是打击天主教士的特权。
一直以来,教士之所以这么牛,就是在于他们是世俗法律管不到的一群人,是拥有“治外法权”的特权阶层。克伦威尔在下议院展开活动,广泛联系对教士特权早就心怀不满的新兴资产阶级议员,对天主教士的特权宣战。
克伦威尔是英国历史上首位玩弄议会政治的高手,通过暗中串联、操纵选举、控制提案和表决程序通过符合己方目的的提案,否决对方议案的目的,成为国会的实际操纵者。
从1529年开始的英国国会被称为“改革国会”,一共存在了7年之久,召开了8次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宗教改革法案。
天主教会包办了婚丧嫁娶的一应事宜,并从中大肆敛财。克伦威尔首先从民愤极大的乱收费项目入手,打击宗教界的财源。
在“改革国会”的第一次会议上,颁布了《遗嘱检验法案》、《丧葬费法案》、《兼领圣俸法案》,限制了教会揽收遗嘱检验费和丧葬费的权力,对兼任圣职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并禁止教士领有土地和经营农业。
在1529年底,国会通过了《剥夺教士司法特权法案》,从此,天主教士犯罪将与普通平民一视同仁。教士的法律保护伞没了,就可以进一步对其下手了。
在克伦威尔的大力推动下,1530年国会进一步通过了《藐视王权法案》,其中规定了藐视王权罪,任何英国人若是企图请求外国势力干涉英国本土事务,将触犯此法案。
用现代话语来讲,该法案就是宣布国家内政不容外来势力干涉,外来势力不得以“人权”等借口干涉英国“主权”(王权)。在当时的背景下,这部法案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打击那些承认罗马教廷至尊权威的人。也正是这部法案,使得时任大法官的托马斯·莫尔感受到空前的压力,从而加强了反宗教改革、迫害新教徒的行动。
与此同时,教士们也展开了反击。他们联合部分律师,宣称从法理上国会无权授权大主教违背教皇的命令。这些律师对于英国法律体系浸淫多年,论证严密,无懈可击。如果克伦威尔也从法律上进行反击,以英国习惯法盘根错节的先例法案,双方将会陷入旷日持久的司法扯皮与文字游戏中,没个十年八年搞不出个结果。
这种政治伎俩在民主政体中十分常见:我要反对你的议案,但又找不到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就想办法把它拖下去,最好拖到地老天荒海枯石烂。
别说十年八年,国王连一天也不想多等,办事不力的沃尔西的下场大家心知肚明,克伦威尔也不可能被这种花样绊住。议会辩论解决不了的事情,那就放在议会之外解决好了。
正在教士们弹冠相庆之时,一桩离奇的投毒案发生了。罗切斯特主教约翰·费舍尔的仆人吃粥后中毒身亡,主教大人则躲过一劫。这本是一桩普通的下毒案,但是查来查去,完全找不到头绪。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政治恐吓,其意思是:费舍尔与国王意志作对,将会随时死于非命,这一次只是警告,下一次就来真的了。
就在教士们人人自危的同时,1531年,亨利八世宣布所有反对他离婚的教士犯有藐视王权罪,将会受到严惩。不过他又表示,如果坎特伯雷教士会议愿意拿出十万英镑的罚款,教士们就可以免受处罚。
亨利八世这是赤裸裸地耍流氓!这等于是警告教士们,再与国王作对,有得是办法整死你们,“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嘛!亨利八世之前一向还是顾及面子的,突然使出这么流氓的招数,不用问,肯定是有人教唆的,而那个人十有八九就是诡计多端的克伦威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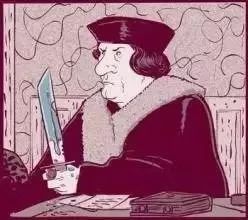
托马斯·克伦威尔漫画
经此一役,天主教士们终于认清了“人为刀殂,我为鱼肉”的严峻现实,教士代表与克伦威尔等人通过一番讨价还价,草拟了一份谅解协议。协议中规定,坎特伯雷教士会议五年内付清10万英镑,并且承认亨利八世为英国教会的至尊首脑,英国教会将服从国王的领导,教会付出这么大代价,国王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撤销对教士们藐视王权罪的指控。
当协议被拿到教士会议上讨论时,与会的教士们都义愤填膺:这就是赤裸裸的强权压迫!但是下毒案的阴影还在每个人的心头萦绕,于是所有人都沉默以对,没有一个人发言。
主持会议的沃汉姆大主教事先已经被克伦威尔“打过招呼”,他说:“不说话就表示同意”。结果全体教士齐声说:“那我们就不说话。”于是,这份协议就在诡异的沉默气氛中通过了。
1531年克伦威尔由于功勋卓著,进入当时英国的权力中枢枢密院,成为国王的智囊团成员,并很快取得核心地位。1532年托马斯·莫尔被迫辞去大法官职务后,克伦威尔接替了莫尔成为国王身边的第一权臣。
随后,在克伦威尔的运筹帷幄下,安妮·博林小三上位与宗教改革同步展开。
国家推动的宗教改革,也算是有史以来开天辟地第一遭,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弄,克伦威尔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打算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既要稳步推进改革,又不至于导致社会矛盾过于激化,酿成不可挽回的全面动乱。
1532年3月,克伦威尔代表下议院草拟了《反教区主教请愿书》,谴责了教会独立的司法权力,主张废除与世俗法律精神相违背的所有现存的教会法。在1529年废除了教士特权之后,这次是更进一步,要彻底废除所有的教会法律。
这就是宗教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前奏。克伦威尔的目的是就是在舆论上先投石问路,探探大家对此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