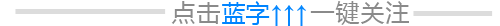

温德尔·威尔基在1940年代表共和党竞选美国总统,败给罗斯福,他于1942年作为总统特使访问中国,图为他视察中国军队
原载于《凤凰周刊》2017年第7期,经公众号“香港凤凰周刊”(微信ID:phoenixweekly)授权转载。
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成为盟友,大量美国记者涌入中国,他们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军民抗战之勇敢坚毅,但也因为带着有色眼镜而给中国军队带来许多麻烦。
台军近来流年不利。从宪兵清理军营吊死流浪狗引发民众抗议,“国防部长”、海军司令出面道歉开始,“金江”舰雄风导弹误射、电讯部门女少校自杀、汉光演习战车翻覆等事件先后成为全民话题。军方面对民意代表和社会舆论一退再退,态度卑微,退役军官感叹“军人的尊严不如狗”。
实际上,在民国时期,军队也在多重压力之下,长期也处于“弱势”地位。
1926年4月28日凌晨4时,北京天桥突然传出两三声狂笑,接着一声枪响,一片寂静。惊醒的民众互相打听,才知道是“奉军杀记者”。死者是《京报》社长邵飘萍,死因是该报评论触怒了入关称雄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半年之后,《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也因同样的理由被奉军逮捕枪决。
报刊与军队的纠葛,可以追溯到晚清新军创建之初。1905年10月,直隶总督袁世凯操办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近代军队联合演习“河间会操”时,就颁布了《报馆随观员应守规则》,要求将“每日一切命令及已经判定之战斗情形”发给记者做报道参考,也命令记者将报道文稿事先交给军方审查盖章,“不准擅行登报”。

晚清新军训练
军队为报刊提供丰富素材,也要制约后者发表意见,本不足为奇,但是,即便是当年被毛泽东控告存在纵兵扰民、盗卖公产、私贩鸦片等“十大罪”的湖南督军张敬尧,也只是一面查禁《湘江评论》等省内报刊,一面对省外媒体婉转回应,声称指责他的人是“摭报纸之谰言,作攻击之通电”。张敬尧不敢直接出手杀人,生怕再引出波折。
社会变革的大潮前,张氏父子不过是螳臂挡车的小丑,本以为靠杀人就能使舆论闭嘴,却收获了无数恶评,被视为国贼,军事失利后只好夹着尾巴逃回关外。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也曾以“训政”为理论加大对报刊出版的管制,却从未禁止对政府和军队的评论。当时的报刊或许无法对日常的军民纠纷实施媒体监督,却能左右将领和部队的声誉。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报刊更成为引领民众情绪、分辨忠奸是非的风向标。
上海是近代中国的媒体中心。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爆发后,大小报刊记者依托租界一线观战,对中日两军战况紧密跟踪、大肆渲染。指挥作战的粤军第19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戴戟等被誉为抗日名将,大出风头,战后每到一地访问都是“万人来迎” 、“应酬不暇”。所获捐赠之丰,支撑起他们在此后十余年间接连开展反蒋运动。在战况报道中被多次提到的第19路军阵亡少尉潘盛益,更是备极哀荣,出殡之日连孙科、何应钦等党国要员都专门致送挽联。
同样参战的中央军第5军将校就没有受到同等待遇,甚至很多人指责国民政府坐看第19路军孤军奋战不予支援。税警总团的总团长王赓,在战斗期间前往上海公共租界,遭到日军伏击被俘,被小报渲染为“为幽会前妻丢机要陷敌手”而身败名裂,连他前妻陆小曼出面辟谣都无济于事。
这种状况下,掌握宣传诀窍的军队便能获得全国关注,热河长城抗战时候的第29军大刀队就是一例。同一个战场上,“东陵大盗”孙殿英更是获得了“洗刷我军污点的大好机会”,在接受采访、发表战报时竭力迎合。《申报》关于孙殿英部“粮弹援绝,孤军迎敌,腹背均受胁,而士卒精神不稍畏怯,振臂一呼,踊跃杀敌……风雪并厉,时而汗流浃背,时而遍体结冰”的报道为其赢得全国赞誉。一年后孙部与青宁马家军起冲突被击溃,舆论还指责南京政府蓄意打击抗战英雄,南京政府躺着中枪。
抗战全面爆发之初,是记者与军人的“蜜月期”。从卢沟桥打响抗战第一枪的吉星文团长、死守金山的姚子青营长,到死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长和八百壮士,都得到充分报道和热情赞誉,就连习惯以美女做封面的《良友》杂志都出了抗日专号。相反,平津沦陷后一度留下的张自忠、在山东不战而逃的韩复榘,都被指责为国人皆曰可杀的卖国贼,结果韩复榘遭到处决,张自忠直到战死襄樊还被认为“血洒疆场只为自证清白”。
随着抗战长期化和保密防谍的需求,国民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实施战时新闻审查,媒体对战况与将领的负面报道、监督评论逐渐减少。记者探不到多少新鲜消息,只能唯行政院新闻局和军委会军令部战报组马首是瞻。直到抗战胜利后政府结束新闻出版管理体制,情况又为之一变。
战后初期,社会上有“四大害”之说:军官总、青年从、国大代、新闻记。即需要安置转业的军官总队编余军官、需要安排复员的从军青年、需要回应提案的国大代表,以及无所不在的新闻记者。实际上,他们影响社会有限,却令军方头疼不已,尤其以新闻记者为甚。
这一时期,不仅是民间报刊,连国民党的党报《中央日报》里,也有一群年轻人秉持“先日报,后中央”的主张办报,追踪民众关注的政府和军队事件时不遗余力,风格活跃大胆。参加军事调停的国民政府代表、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上将,拒绝接受《中央日报》记者陆铿采访,后者直接发消息称“徐永昌失踪”。胡宗南部攻占延安后,前往采访的记者更是当面质疑战俘是国民党军人假扮。
记者与军人的较量中,军人逐渐落入下风。记者面对涉军重大事件往往死缠烂打、追问到底,引领舆论迫使军方让步。1945年12月,昆明爆发编余军官围攻大学校园的“一二·一”事件,致使4名师生死亡。事发之后,各报严厉指责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征处置失当,又为他量身定做了一句“学生有游行的自由,军人有开枪的自由”,逼得这位抗战老将只能承认良心不安,自请处分,最终被撤销职务。
今天的台湾军队高层将接受民意代表质询视为畏途,他们在内地时期的前辈也面临类似情况。监察院的监察委员、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和国民大会代表,都有权对军方提出监督弹劾、质询纠举。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现实是将军遇到民意代表时却难以招架。
监察院是按照孙中山先生“五权宪法”理论建立的最高监督机关,管辖范围涵盖文武两班,直至政府首脑。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以行政院长汪精卫主持签订停战协议告终,监察院便提出《弹劾汪精卫破坏十九路军抗战案》,坚持“设不严予惩处,则以后国家主权疆土有此成案可援,皆将断送于协定二字之下”。后经国民党中常会否决,又慰留各自要求辞职的汪精卫和监察院长于右任,才把风波平息。

1943年冬,常德会战刚落幕,外国记者采访中国军队
同期,监察委员高友唐等人还提出《弹劾海军案》,指责海军在上海抗战期间“不独未开一炮,且避匿无踪”,存在通敌嫌疑,也在高层顾全大局的思路下被冷处理,不了了之。1933年热河失守,监察院接连弹劾华北军政最高负责人张学良、热河军政首长汤玉麟,结果前者通电下野,后者投置闲散,一众监察委员才觉得扬眉吐气。
监察院毕竟不是专门的军事监督机关。全面抗战时期的1938年到1945年,对军官弹劾51人、纠举124人,不及弹纠文官数量的十分之一,但比1936年之前五年间仅弹劾军人27人,不及弹劾文官百分之二的情况已经进步许多,而且其中颇有大案。1944年豫中会战失利后,监察院以第1战区正副司令长官蒋鼎文、汤恩伯作战不力、纵兵扰民提出弹劾,结果蒋撤职免官,汤撤职留任。第8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的亲信兵站总监班淦,因贪污公款及借赴新疆宣慰之机走私违禁物资,遭甘青宁监察使高一涵弹劾后经军法审判枪决。
与作为“官”的监察院呼应,战时最高民意机关即国民参政会同样对军队颇多关注,尤其集中于军风军纪和兵役问题。1938年,梁漱溟等提出《改善兵役实施办法建议案》,指出壮丁征集、入伍受训两阶段种种弊端,要求当局加以整饬。1939年2月,黄炎培等提出《协助改善兵役建议案》,提出壮丁可以“纳金缓征”,以“谋人力财力支配适当,适应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之原则”。
参政员多为学界名宿、社会贤达,毕竟与军事实际颇多隔膜,不仅所提建议难以立即实施,所论问题也经常片面失实。例如,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蒋梦麟视察各地壮丁押送情况后,认为“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却未曾想到壮丁在押运途中除了死亡还有逃亡一途,而且为数甚多。
兵役问题是战时后方社会的热点,不仅中央民意机关瞩目,地方民意机关也十分关注。1944年7月,驻陕第80军派大队长徐正辊到川北接收壮丁,因克扣米油,不予医药,虐待致死105人,其部下又有强拉、卖放壮丁问题。宣汉、开江两县参议会联名告到军事委员会,结果徐正辊及部下军官共5人均被枪决。
国共内战期间,情况又有新变化。1948年2月,蒋介石的爱将陈诚将东北行辕主任的职务交给卫立煌代理后,躲进上海的医院,数月称病不出,不仅因为在东北指挥战事接连失利,也与抗战胜利后“国民大会代表”的活跃直接相关。这些人作为各省市地区直接选举产生的民意代表,对军队施压能力远胜监察委员和国民参政员。
第1届国民大会在1948年5月正式开会,几百名代表联署临时提案,要求政府枪决败将陈诚。听取国防部长白崇禧做军事报告时,代表们又打断发言,以“我们不愿听军队的伙食怎样?要听各战场打得怎样”打开话题,“请杀陈诚,以谢天下”、“不许陈诚逃往美国”、“到上海逮捕陈诚,解京法办”的呼声不绝于耳,还被在会记者一五一十地报道了出去。
陈诚身为土木系领袖,却对这些国大代表及造势的报刊毫无办法,只得向国民政府要求辞去本兼各职。国大代表当然不能满意,东北代表反应尤其激烈,“九·一八”事变后领导抗日义勇军的松江省安图县代表孔宪荣愤而自缢。
同是国大开会期间,解放军攻下河南省会开封,在南京的河南籍国大代表群起请愿,气势汹汹。蒋介石不得不强令刚刚做过肾切除手术的杜聿明飞临战场指挥,夺回开封,才化解了军事与民意的双重危机。
败退到台湾之后,军事将领的责任问题更成为监察委员和民意代表们清算的重点。1950年5月,46名监察委员联名弹劾代理西南军政长官胡宗南丢弃部队,逃往台湾。幸亏又有人组织起100多名立法委员联名求情,胡宗南侥幸逃过一劫。
军队是社会的一部分,自然不可能隔绝于民众。带兵将领是社会公众人物,也不愿无故承担军纪败坏的恶名。抢粮食、抓壮丁、强征民夫、强买强卖、强奸妇女,都是军队扰民的经常情况,即使是国民党军也很少对此放纵不理。
孙中山的爱将、粤军第1师师长陆铿自称,其军队过处“夜不闭户,鸡犬无声”,因为门板都被军队拆走使用,鸡犬都被宰食一空。不仅粤军,聚集在孙中山麾下的建国滇军、建国桂军、建国湘军等各路部队也大略如此。等到黄埔学生军创建之时则大不相同,军纪严明,行军不拉民夫,作战不据民房,得到民众热烈响应。
北伐结束,面对派系林立的百万军队,国民政府开始大举扩充作为军事警察的宪兵以维持军纪。1930年代,国民政府设置宪兵司令部统管政令,开办宪兵学校培养干部,并出台《宪兵令》明确宪兵职责,从军人服装仪容到军民往来、地方治安,均可一体承担。宪兵纠察军风军纪,可以羁押违纪官兵,自称“法治之兵种”、“革命的内层保障”,见官大一级,也因此颇得罪人。
宪兵第3团在1930年中原大战后进驻北平,既严厉处置入关东北军的风纪问题,又对平津一带的日本“中国驻屯军”进行监视,支持抗日活动。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方提出的要求之一便是将宪兵第3团调离。1936年西安事变当中,原宪兵第3团团长蒋孝先遭东北军枪杀,理由是此人“阻碍抗日”。多年之后,张学良的侍卫副官赵维振披露,蒋孝先被杀是因为他在北平时曾指挥宪兵查封东北军的海洛因工厂,断了部分将领的财源而遭到报复。

蒋孝先
军纪不仅靠宪兵维持,各部队长官也颇为重视,甚至不乏极端行为。1941年,中央军第71军进驻龙云治下的云南,军长宋希濂为避免与当地民众冲突从而给龙云以反对驻军的口实,对军队纪律要求极为严格。他的部下伍蔚文回忆,某个夏日傍晚,宋希濂在洱海散步时听到枪声,亲自前往查明是部下一名士兵打死了老百姓的一条狗。“当时他火冒三丈,从卫士身上拔出手枪就把那个打狗的士兵枪毙了,并查明了他的单位,给所属官长予以管教不严的处分”。宋希濂升任集团军总司令后,所部移驻大理,总部副官周某发现驻地附近的和尚晚上聚众赌博,他经常前往勒索,被告发后也遭枪决。
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浚回忆“军校学生犯罪,均由委座令交审讯,本部从未直接检举一人,即判罪亦无一不引用最轻条文,且必须呈报委座核示”。但蒋介石并不会对黄埔学生比杂牌将领更手软。
1938年11月长沙文夕大火后,各界批评极为严厉,蒋介石下令将长沙警备司令、黄埔一期生酆悌枪决以平息众怒。1944年豫湘桂会战,中国军队败得最惨,高层对作战不力将领的惩处也最为严厉:河南战场枪决了擅自撤退的第97师师长、黄埔五期生傅维藩,广西战场枪决了弃守全县的第93军军长、黄埔一期生陈牧农。
1944年10月,因后方勤务部运输第29团一名士兵被毒打致死,牵连出该团一年未曾发饷,官长对所部士兵极尽苛刻,甚至死亡之后任意抛弃野外的惨况,更令蒋介石震怒。兵役署署长程泽润因此撤职下狱,在抗战胜利前数罪并罚遭到枪决。在此之前,运输第29团团长、黄埔六期生钟士铮早已成为军法审判下的亡魂。
抗战胜利之后,崩溃的国民经济尚未缓解,国共内战又告爆发,国民政府内外矛盾极其尖锐。各地高校接连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与军警发生冲突,经常落得“两败俱伤”。一旦学生出现伤亡,政府无法置若罔闻,军警方面也难逃其咎。1947年6月,军警进入武汉大学抓捕中共地下党员,与学生发生冲突,导致3人死亡。事后武汉警备司令彭善被撤职,现场指挥军警的稽查处长胡孝扬投江自杀。
从当时到1980年代,始终有人声称胡孝扬自杀是“金蝉脱壳”,本人隐姓埋名仍在人世。但从胡氏投江这一举动,也可看到当时军人对外界压力的畏惧。国民党军自建立到退守台湾的二十多年间,头上的罗网日渐严密,面向社会退让已成趋势。只不过内地时期国民党军派系繁杂,地方部队割据自雄,面对舆论批评和民意监督,尚有敷衍塞责乃至置之不理的空间,如今的台军已经没有这样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