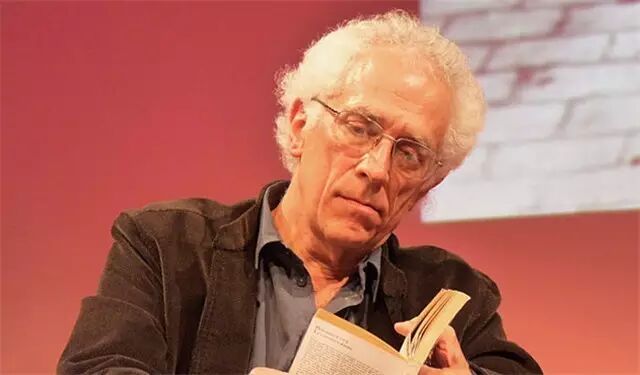
文 | 云也退
茨维坦·托多洛夫只来过一次中国,在上海,我的朋友袁莉教授,也是托氏《我们与他人》的译者,陪老先生去逛了朱家角和豫园。她说,返回法国那天,她和先生送他去机场,站在机场大厅门口,托多洛夫朝着他们不停地挥手,直到他们的车开走,他才进去。
远在学府和学界之外,我只能间接听听朋友转述的印象。托多洛夫是保加利亚生人,主要是法国人(1963年后到法,后来入籍),但更是欧洲人,这是我从他的书中得来的印象。法国就是欧洲,至少也是欧洲的代言人,而保加利亚不是——所有东欧国家都只是东欧而已,所以从东欧走向世界的著名文化人,比如米沃什、赫贝特,都带有“欧洲价值”的光环:“欧洲人”成了他们立足的身份。

▲ 茨维坦·托多洛夫(1939—2017)
在法国待着,比在保加利亚强(毋庸置疑),而在欧洲待着又比在美国待着强:托多洛夫在一次访谈里表达了这个意思。他是个喜欢普遍胜过个别的人,他觉得美国太讲究个别了,美国人都奉行相对主义的价值观,搞什么多元主义,弄得大家都只认同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但是在欧洲,这么多国家和民族,在停止互相征战之后结为共同体,这就是走向普遍的重要一步。进一步说,在美国,不管你是什么肤色什么信仰,你的认同顶多也就抵达“美国”,不能更远了,你要和美国的荣辱、美国的利益捆在一起;而在法国,你却很容易认同“欧洲”,一个开放的、一直在变化的概念。
眷恋普遍的人,能够从相异的现象里找出相通之处。托多洛夫生于二战爆发的那一年:1939。后来,因为人生的头三分之一在保加利亚度过,斯大林主义在这个贫穷、悲惨、被人忽略的农业国闷声不响地制造了许多血案,他自然会去关注、去研究从纳粹集中营—苏联古拉格—极权主义这一被无数人嚼烂了的历史脉络,他注意到,众多写集中营、劳动营的亲历者都在写个人经验的极端性,特殊性,不管是德国人摧残囚徒,还是囚徒们为了争取生存而互相陷害,总之就是极端。《面对极端》这本书,就是托多洛夫读这些作品的心得,他说:不,我还看到了另一面,集中营里并非不能共同生存,也有很多幸存者是靠着互助活下来的。
分析家跟道德家(moralist,有道德关怀的人,中文里的“道德家”多少有点贬意),是两个很难统一的身份:分析像大屠杀那样的事,你怎么告诉读者,其实道德的价值一直在那里,没有被湮灭?可托多洛夫偏要这么做。他说,你研究历史也好,思考政治也好,都得负“道德义务”。
到底扛过“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法国人尤其热衷于期待一个人类共存的未来,并且研究共存的可能性和方法——在托多洛夫的预设中,这可能性永远存在。他的另一本早期著作,考察的是另一段人类的血腥记录:西班牙人征服美洲。从哥伦布发现大陆开始,到柯特兹率领的殖民军残忍灭绝北美的阿兹特克土著,如此残酷的历史,哪里还能找出人与人可以共存的证据?托多洛夫找出来了,他取得了一个惊人的结论:欧洲人赢得了战争,是因为欧洲人之间彼此能更好地理解,沟通能力更强,于是,善于理解他人的欧洲人征服了“他者”。
《征服美洲》或是托多洛夫最受诟病的一本作品,他强要在历史中找出正面的、普遍的东西,反而暴露出一种欧洲中心论的傲慢;他也不是历史学家,免不了要扭曲史实,或者有目的地采择证据,来为自己的道德结论服务。不过,结合后来评论卢梭的《脆弱的幸福》来看,托多洛夫总在追寻一个信念:欧洲是一个庞杂的思想—文化传统,它能同时孕育近现代的恐怖暴力和反对这种恐怖的力量。要做一个人文主义的学者,你就得辨析出这一庞大传统中具有正面价值的内容。
《征服美洲》出版于1984年,十多年后他又出版《我们与他人》和《不完美的花园》两书,我的读感是,就仿佛一个人在沙漠里苦苦寻找过绿洲后,重新回到自家的水库。水库里装的是他最熟悉的法国文人,上到蒙田,下迄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中间经过了他最喜欢的孟德斯鸠、卢梭、邦亚曼·贡斯当:他们个个都写道德文章,为未来的人类社会画策。尤其对其中最“邪恶”的法国人卢梭(硬扯的话,保加利亚的凄风苦雨都可以追溯到卢梭造的孽——人们认为他的著作开启了现代独裁之门),托多洛夫以专著《脆弱的幸福》来谈他的理解。他说,卢梭思考的正是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我们要过一种什么类型的生活?我们与自己、与周围人、与国家体制、与政治的关系是怎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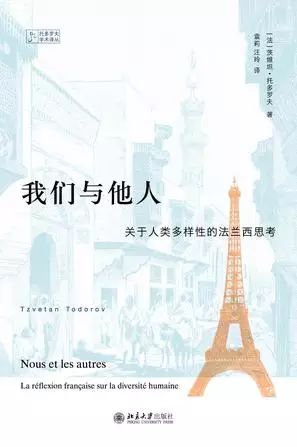
▲ 《我们与他人》/[法]茨维坦·托多洛夫 著/袁莉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这种思考,必须有人去做,哪怕冒着欲速不达的风险;一个民族的思想者,不能只替自己民族的利益和前途考虑,而要超越个别,走向普遍。托多洛夫的著作主题很丰富,但是贯穿其中的一个教诲是,欧洲几个世纪以来积累的思想文化遗产,已经留下了许多道德的甘泉,掬而饮之,眼界便豁然开朗。例如,他在《日常生活颂歌》一书中论述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的绘画,他说,这些话不是发明,而是“发现”了日常生活中的美学,无论是斯梯恩、弗朗斯·哈尔斯还是维美尔,我们从其画作中看到的都不是夸饰后的现实,而是客观事物、人物、场景真实的样子——它们本身的美。
法国人真是迷恋普遍主义的价值观,无怪乎海峡那边的岛国人,总嫌弃他们眼高手低,陷入虚妄的书生气。托多洛夫的书富于法国哲学家的自信,认为孕育于书斋的思想可以指导现实行动,他乐于描述人应该成为的样子,不太乐意胪列一个个细节来勾画人现实中的样子,因为后者是暂时的,即将被告别甚至被克服。在1997年出版的《不自在的人》一书中,托多洛夫断言,我们生而为人的真谛,“不在于仅仅拥有特殊的利益,相反,同样是这些利益,我们要有能力超越它们。”
托多洛夫2月7日去世,去世前刚刚写成一本书《艺术家的凯旋》,跟《个体的颂歌》《不完美的花园》《脆弱的幸福》等等放在一起,看得出其人的乐观。可是新问题出现了:欧洲人现在的心情,同托多洛夫入籍法国时大不一样,如今,“恐外症”不再是一个对极少数保守分子的贬义描写,而是广泛散布的心情。2008年,托多洛夫在一次访谈中说出了他的设想:单纯站在人的层面上,我们和他们只要对话即可;但如果是“诸神”之间相遇——两种信仰教义彼此抵牾,谁都不服谁——可就麻烦了。
(本文原标题:《人活着的真谛,是超越自己的利益》)
·END·
大家 ∣ 思想流经之地
微信ID:ipress
洞见 · 价值 · 美感

※本微信号内容均为腾讯《大家》独家稿件,未经授权转载将追究法律责任,版权合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