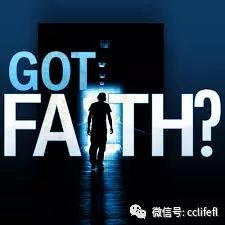
请击点图片上方蓝色的“生命季刊”,选择“关注”,您就会每天收到生命季刊播发的文章)
清华心缘——追忆五位清华的思想前辈
(2)
文/赵征
生命季刊微信专稿
本文为“清华校友信仰见证集”一书的“代跋”。请参考阅读本文作者及清华校友们的文章与见证(本刊将继续播发清华校友的见证,敬请继续关注):
1.
你所不了解的——清华大学的信仰渊源!
2.
清华校友信仰见证集之一:当我走到尽头……
3.
清华校友信仰见证集之二:一个“清华土著”的信仰之旅
4.
清华校友信仰见证集之三:我的信仰历程
5.
清华校友信仰见证集之四
:
从迷失到献身
6.
清华校友信仰见证集之五
:
见证:清华才女蒙恩记
7.
清华校友信仰见证集之六:基督之光改变了我的心
8.
清华校友信仰见证集之七:学长带我去教会
9.
清华校友信仰见证集之八:回家
10.
清华校友信仰见证集之九:寻找与被寻见
11.
回家, 不再一样 清华校友信仰见证集之十
12.
回家了——清华校友信仰见证集之十一
13.
我的见证 ——清华校友信仰见证集之十二
14.
在高山之巅, 遇见上帝!——清华校友信仰见证集之十三
15.
全是神的恩典——清华校友信仰见证集之十四
16.
祂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清华校友信仰见证集之十五
17.
清华心缘——追忆五位清华的思想前辈
吴 宓

陈寅恪的挚友,清华的另一位思想者吴宓先生于1894年生于陕西泾阳。他是清华学堂1911年创立时招收的第一批学生,5年后毕业,赴美国留学,获得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的硕士。他的毕业论文题为:《中国之旧与新》,对当时中国的文化走向深有洞见。殷海光曾说:五四前后,中国海禁大开,大量留学生出国,接触到西方不同的学说、世界观、价值观。他们恍然认识到,世界不只是中国的古圣先贤所描绘的那一点点。而且世界的丰富的文化思想比起自己祖宗代代相传下来的那一套要更新鲜,更有活力。中国原有的学术思想的标准是崇古的,后顾的。到了五四,就来了个彻底逆转,变成‘凡新的就是好的’。然而,吴宓以他思想的定力,努力寻找“新”与“旧”的融合契机,阻止偏颇于任何一个极端的倾向。他留美四年后回国任教办刊,极力顶住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保护文言文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1925年清华学校改办为清华大学,吴宓被聘回母校主持筹建国学研究院。
吴宓和陈寅恪曾是哈佛同窗,又成清华同事。他们之间有伯牙子期之情。如果陈寅恪像是深思忧郁的哈姆雷特,吴宓则像坦率真诚的堂.吉柯德。他二人虽然性情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就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落后状况。吴宓曾说:“苦吾中华古国,竟不能比于希腊罗马之以学术文艺影响全世后来,且不能经于意大利爱尔兰之得其道以复兴,此其摧心丧志真无穷也。”
吴宓与陈寅恪都认识到,要使中国强盛,张之洞主张的从西方引进器用技巧是不够的;康梁提倡的改良政治经济体制也不全面。关键是要以西方的精神精髓复兴中国的精神文化。他虽然在五四时期坚决捍卫文言,并且在文革末期甘愿冒死拒绝批孔,但是他不承认自己是守旧的“孔子之徒”,却认为自己“所资感发和奋斗之力量,实来自西方。”他奉劝中国的留学生:“我们留美学生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大胆地进入美国模范家庭,研究他们的状况诸如孩子们的纯真和坦诚;并从家居生活着手改造我们的国民。清华学生留美时应多多留意其所居留的家庭,因为归国留学生品行的形成与其所寄居之家庭密切有关。”
吴宓对于西方的精神精髓比陈寅恪把握得更透。他对基督信仰不仅不排斥,甚至十分心仪。他爱读柏拉图语录和《圣经》,认为希腊哲学和基督信仰为西方文化的两大源泉,并且是西方一切理想事业的原动力。他在哈佛的导师白璧德(IrvingBabbitt)崇尚古典浪漫主义又兼蓄基督信仰的传统。吴宓认为自己得到老师的真传,可以“直接继承西洋之道统,而吸收其中心精神。”他相信世间有“绝对之善恶,是非,美丑”,也看到世人的迷失混乱:“学术之淆乱,精神中迷离痛苦,群情之危疑惶骇,激切鼓荡,信仰之全失,正当之人生观之不易取得,此非吾国今日之征象,盖亦全世之所同也。”因而他亟欲为自己也为国人“取得一贯之精神及信仰”,“以救其失。”他在清华开设了“文学与人生”的课程,旨在通过文学来研究人生,帮助学生“在自己的灵魂中重建哲学的真理。”他认为:“在人生中…重要的不是行为,也不是结果,而是如此行为的男女的精神和态度。”
吴宓隐约地感到上帝的存在,甚至自称“笃信上帝”。他发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因受儒家“不与焉鬼神”的影响,缺乏对上帝的寻求,认识,敬畏,和爱,而这些恰恰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核心。吴宓沿袭了黑格尔的思想,把人生分为天、人、物三界:“以天为本,宗教是也”,“以人为本,道德是也”,“以物为本,所谓物本主义”。吴宓解释说:“人皆有饮食男女之欲,仅少数人有知识学问之欲,更少数人有品德完美之欲,极少数人有诚爱敬笃上帝之欲……宗教、道德,皆教人向上也。宗教之功用,欲超度第二第三两级之人,均至第一级。道德之功用,则援引第三级之人至第二级而已。……若于宗教道德,悉加蔑弃排斥,惟假自然之说,以第三级为立足点,是引人堕落,而下伍禽兽草木也。”
但是,吴宓所信的上帝局限于没有位格、缺乏对个人的直接关怀的抽象的“绝对观念”。虽然吴宓爱读《圣经》,却没有把其中对上帝在《圣经》中对人的直接启示当作真理。他没有从心里认识和接受那位自有永有,创造人类,深爱人类的上帝。他宁愿与上帝拉开一定的距离。让上帝按照自己的理解,存在于一个没有生命的抽象的概念里。然而,这种抽象的“绝对理念”毕竟是出自人有限头脑的一个哲学概念。虽然感觉上比一个有位格的上帝更容易被人的理性接受,但是单薄空洞,无法把握,没有生命,缺乏《圣经》里对上帝的神性的宏大而具体的彰显。吴宓敏锐地看到这个问题:“吾虽信绝对观念之存在,而吾未能见之也。吾虽日求至理,而今朝所奉为至理者,固尤是浮象,其去至理之远近如何,不可知也。”吴宓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困境:依靠自己的理性去寻找超越自己理性的上帝,追求到一定程度,理性就不够用了。人若非要靠自己有限的理性去理解无限永恒的上帝,最终只能把自己当成“上帝的设计者”去幻想上帝是个什么样子。但是谁会真正地相信和依靠一个自己幻想设计出来的“上帝”呢?
面对这个困境,吴宓甚至产生了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究极论之,道德理想功业,无非幻象。人欲有所成就,有所树立,亦无非利用此幻象,所谓弄假成真,逢场作戏而已。”吴宓虽然比陈寅恪更加认同基督信仰,但是他理性的骄傲阻碍他谦卑地接受《圣经》里面神对人的启示。他虽自称笃信上帝,但是其实仍是个不可知论者。所以,他把自己定位在人生三界中的“以人为本”的认识第二境界。
吴宓对天地大道的追求实际上包含了一个悖论:作为理想主义者,他不仅承认上帝的存在,而且认为这个至高的存在提供了维系、指导人类生命的根基。但是,作为人文主义者,他又不愿意接受《圣经》里启示的有真实位格的上帝,他宁愿相信上帝是高不可攀的“浮象”。这样一来,上帝被他降格成了“逢场作戏”的心理安慰而已
,而这样的浮象又怎能维系、引导自己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