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乘风破浪》宣传曲的“直男癌”倾向,人们已经说得够多了,相信小伙伴们也都已有了自己的判断,不如今晚就让我们回到影片本身,不,甚至不是影片本身,而是谈谈电影带来的某些启发,关于我们与父母之间的“代沟”和爱。
花边君
我要跟你握手言和
作者 / 小日耳耳
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看过《乘风破浪》后,会羡慕徐太浪,我是深深地羡慕。
羡慕他可以回到泛黄的纯真年代,了却自己的夙愿:见到素未蒙面的母亲;羡慕他与父亲像兄弟一样共患难,历经
“
友情岁月
”
后最终理解了父亲的甘于平庸;
更羡慕他拥有一次这样的超能力,跨越时间的同时也跨越了两代人的代沟,重新认识世界也认识自己,开始学会了与父亲握手言和。
其实,羡慕的背后是深深的焦虑。

从电影一开头儿子举起手中的冠军奖杯恨恨地向父亲
“
致谢
”
时,就直接戳中了两代人的
“
痛处
”——
代沟。
父母希望儿女成人后能有一份稳定又正当的工作,而儿女则认为唯有做自己想做的事、圆自己想圆的梦才算实现
“
人生价值
”
;
所以电影里儿子不愿听从父亲的安排开救护车,只想通过开赛车证明自己;那个细节让我想起了李安的父亲,
在他眼里,拍戏始终算不上正经事,
甚至是李安以《喜宴》拿下金熊奖后,还希望李安改行去大学教书或从政。
我们和父母之间:不同的成长经历形成不同的
“
三观
”
,不同的生活阅历造就不同的理想追求,甚至不同的环境、背景渗透到个人的思想、喜好、言行等各个细枝末节里,逐渐产生的心理隔阂和差距,就是
“
代沟
”
。

戏里戏外,代沟无处不在。
无论是父母对我们婚姻的干涉还是我们对父母生活习惯的不解,无论是父母强权的教育方式还是我们的叛逆与反抗,每一种形式的代沟都在拉远着我们与父母之间的距离,分裂和加深着亲情的罅隙,让我们深困其中、不得其解。
其实我们都是爱自己的父母的,就像徐太浪一样,拿到奖杯后都要载着父亲去飙车,用炫耀来解气,用示威来表达
“
我爱你
”
。
然而,我们总是只能笨拙地在一次次与父母对抗之后责怪自己,在一次次
“
隔空喊话
”
失败之后悔之莫及反醒自己。
我们都清楚知道:电影毕竟只是电影,靠臆想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但电影给予我们的思考是真实的,在消除代沟这件事上,我们能努力的地方还有很多:

可以真诚地主动沟通。
就像龙应台的儿子安德烈那样,直接对母亲坦白:
“
妈,你要清楚接受一个事实,你有一个极其平庸的儿子,我觉得我将来的事业一定比不上你,也比不上爸爸
——
你们俩都有博士学位
……”
而这份坦诚也收获了母亲发自肺腑的回应:
对我最重要的,安德烈,不是你是否有成就,而是你是否快乐
……
假定说,横在你眼前的选择是到华尔街做银行经理或者到动物园做照顾狮子河马的管理员,而你是一个喜欢动物研究的人,我就完全不认为银行经理比较有成就,或者狮子、河马管理员平庸。

可以接纳与包容。
就像我们喜欢电子产品或沉迷于微信网络一样,父母也会有他们特殊癖好和我们不能理解的传统。
而这种互不买帐往往会成为代沟产生的源头。
李安说:直到现在他们家还保留着过年要磕头的习惯;而电影《大鱼》里的儿子一直把父亲的传奇故事当作笑谈。
如果我们给予彼此接纳与包容,效果常常会在我们意料之外。
李安在拍电影的过程中逐步与父亲和解,父亲从开始的不满到后来的支持,甚至在他拍《喜宴》、《推手》资金窘迫时,还提供墨宝给他充当书画道具。
而《大鱼》中的儿子在了解父亲的故事并不是虚构之后也与父亲冰释前嫌。

可以用爱填
“
沟
”
。
一位朋友爱好写作,在父母的再三反对下还是辞去了工作专职写作,因此父母气得半年都没有跟朋友通过电话。
但朋友始终没有放弃,每次自己写的稿子都寄给父母、每次刊登的文章都会拍照发给父母。
终于有一天,在他寄给父母一篇写给父亲的文章后,母亲打来了电话,要他春节回家过年。
其实,消除代沟的过程亦是亲情升华的过程。
纵使代沟千差万别、解决方式也各不相同。
爱
——
始终是父母与儿女之间的通天大道。
因为,
这世间都没有爱不能抵达的地方,没有爱不能消除的隔膜,没有爱不能化解的怨怼。
电影里,天台上,六一和正太对着天空大喊:
我就像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
太浪随即补上一句:这个世界是会变的。
其实,他们和我们,都清楚明白:世界会变,你我会变,但爱始终会在那里,一成不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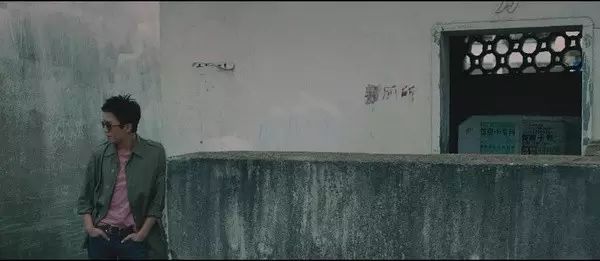
►
图片来自网络(《乘风破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