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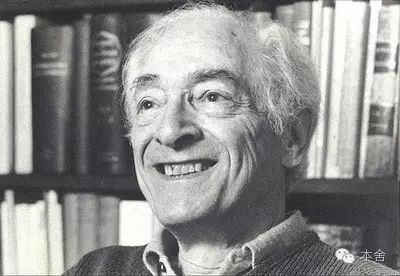
迈耶·夏皮罗(Meyer Schapiro)

海德格尔

德里达
《作为个人物品的静物画:一则关于海德格尔与凡·高的笔记》(1968)在《艺术的理论与哲学》这个集子里的地位特别重要,因此需要分别对待。它声名显赫,是各类选本争相选取的篇什。不过,在介绍这个名篇之前,让我先引用一则最近流行于微信圈的段子。
这则微信应景地采用了截屏的形式,“截取了”某朋友圈的一段对话。我的风趣不及这类微信段子写手的万分之一,只能尽量简明地陈述一下要点。事情仿佛是这样的:
有个叫海德格尔的好友在微信圈里说:凡·高画的某双农民鞋,揭示了“艺术之为真理敞开”的本质。借助于这幅画,一个农民与大地的关系,他或她的世界确立了。

梵高《一双鞋子》1886
正当海德格尔得意洋洋地宣布其艺术理论,长篇大论地抒发其关于艺术与真理的那个亢奋激昂、高潮迭起的段落时,有个名叫夏皮罗的好友插话了:海德格尔教授,谁说凡·高画的那双鞋子是一个农妇的鞋子?那明明是凡·高本人的一双旧靴子嘛!而直到那时,凡·高基本上是一个城市居民,与农民、大地、世界(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嘛!
海德格尔大窘(表情)。不过,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群里突然冒出来一个名叫德里达的人,他叫板夏皮罗道:夏皮罗教授,那明明是凡·高的一双旧靴吗?我怎么看都不像一双鞋子,我感觉那更像两只左鞋,而不是一双。谁说那是一双啦?你有证据么?
现在,轮到夏皮罗在风中凌乱了(表情,表情,表情)。
在我不多的几个微信群里,这一段子就出现了好几回。这大概可以说明它的流行程度。而在我读到国内学者关于海德格尔-夏皮罗-德里达之争的介绍和评论中,这一段子所概括的图景,甚至成为一种标准范式。
然而,我对德里达那篇宏文的印象,与微信段子或国内学者的已有介绍大为不同。我不仅没有先后出场的时间序列的印象——即夏皮罗针对的是海德格尔,而德里达针对的则是夏皮罗;而且,我也没有德里达主要针对和批判夏皮罗的印象。恰恰相反,在我看来,德里达发表此文的主旨仍是解构西方强大的形而上学传统,特别是以声音(言语)居先于文字(语言)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而在这个悠久的传统里,海德格尔显然是最后一位大师。我的这一印象当然可以用文本本身来加以证实。德里达对两位“西方著名教授”的分析和评论的篇幅就证实了我的印象:大体上,海德格尔在这个文本中占据了约三分之二的篇幅,夏皮罗占据约三分之一。此外,海德格尔的名字在这一文本出现了240次,夏皮罗出现了172次。
德里达的那个文本用的是对话体,可是他却没有标明其中哪一位是德里达本人,哪一位(或多位)是德里达的对话者。在欧洲的对话体哲学书写中,柏拉图的对话录堪称典范。在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的对话者大多头脑简单,学问不好(比如格劳孔),对苏格拉底的问题只能答以最简单的“是”或“不”。但是辩证的——柏拉图的那类对话是辩证法的出处——双方的观点是清晰的,角色的分工是明确的,整个对话的推理过程是事先设计好了的,也是读者能够追踪和复原的。但是,面对德里达的那个对话,我费了好大的劲想把他们之间的对话理出个头绪来,至少想要弄明白,哪些话是德里达本人说的,哪些则出自他的对话者之口。而且,我也试着尽可能把德里达的话归在一起,以便理出其中的推理线索,或至少是前后相承的逻辑关系来。但是,我发现这一点根本没有可能。不仅没有可能确定德里达说了哪些话,他的对话者说了哪些话,也没有可能将德里达的话前后关联起来,或将其对话者的话前后关联起来。甚至,没有可能确定在这场对话里,究竟有几个对话者。

梵高《一双鞋子》1887
有个念头突然闪过,我不禁哑然失笑:这样做本身就是可笑的,是可笑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陋习。那种想把哪些话归入哪家之口的做法,难道不是与德氏文本嘲笑海德格尔和夏皮罗楞要将鞋子系于谁的名下(是一个农民,还是一个城市居民;再具体一点,是一个农妇,还是画家凡·高本人?)一样可笑吗?想从德氏文本中读出前后一贯的逻辑,不是正好犯了德氏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基本立场吗?
焕然冰释。
当我不再忙于猜测究竟哪些话是德氏本人的,哪些话又是他的对话者(哪怕是他虚构的对话者)时,我顿时感到了轻松。于是我兴致勃勃地阅读这一德氏本人称其为polylogue(多角谈话)的文本,不再关心是谁说的话,也不再关心他和/或他们是否前后矛盾。反正它是众语喧哗,一些话语的碎片,本身就不以逻辑力量来说服读者,而是以其碎片的直觉力量来击中人。
德氏文本一上来就指出,海德格尔在其《艺术作品的本源》讲演稿里,差不多开篇即说,让他举“一双鞋子为例”:“田间的农妇穿着鞋……农妇站着或走动时都穿着这双鞋”(“Die Bäuerin auf dem Acker träge die Schuhe…Die Bäuerin dagegen trägt einfach die Schuhe”)。
夏皮罗则说:“它们显然是艺术家本人的鞋子,而不是一个农民的鞋子的图画”(“They are clearly pictures of the artist’s own shoes, not the shoes of apeasant”)。
德氏文本反问道:“他俩——我是指夏皮罗和海德格尔——从哪里获得他们的确信,即这里是一双鞋子的问题?”(Jacque Derrida, “Restitutions of the Truthin Pointing”, in The Truth in Painting.Trans. Geoff Bennington & Ian Mcleod,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255-382;这里的引文见第261页)它接着问:“在这种情况下,一双鞋是什么,他俩是打哪儿得到的想法,凡·高画了一双鞋?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这一点。”(Ibid., p.264)
相反,德氏文本立刻断言:那两只鞋子很有可能不是一双鞋,不管是农民鞋还是艺术家本人的鞋,它们只是两只不成双的鞋。“当鞋子被搁置一旁,空空如也,暂时或永久弃之不用,显然从脚上脱下,被带在身边,有鞋带却没系上,一只与另一只总是不打结……那么,某种事件就发生了。”
是的,让我们假定两只(有鞋带的)右鞋或两只左鞋。它们不再构成一双,那么,整件事就开始,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开始以怪异、令人忧虑,或许还是唬人的,略带恶毒的风味,斜睨或跛行。凡·高的某些鞋子有时候就给我这样的印象,我怀疑夏皮罗和海德格尔是否为了让自己安心,就过于急切地让它们变成一双。根本未及反思,就把它们当作一双鞋,以此来安慰自己。(Ibid., p.265)
接着,德氏文本提出了一系列十分尖锐的问题:“因此当人们确定鞋子的归属时,当他将鞋子归还或复原时,他是在干嘛?当他在确定一幅画是谁画的,或者在确定一位签名人时候,他是在干嘛?特别是,当人们费了老大劲将所画的鞋子(在绘画中)确定为那幅画的假定的签名人的时候?或者,相反地,当人们抗议它们的归属的时候,他是在干嘛?”(Ibid., p.266)

梵高《一双皮革木底鞋》1888
尽管,从德里达的角度看,这些问题似乎根本无从回答(事实上也不需要回答,它们只是修辞格中的反问法,答案早已隐含在问题之中),但是,有意思的是,从夏皮罗的角度看,人们却可能回答这些问题,尽管夏皮罗本人可能觉得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夏皮罗的意旨,当然不是单纯驳斥海德格尔弄错了鞋子的主人(不妨这么说),而是,从他这个艺术史家的视野,确定艺术作品,特别是静物画,与画家的个人关系;进而,将这一层关系推进到艺术史与艺术家个人的关系(而不再是黑格尔——海德格尔亦然——所说的艺术史与时代精神或民族精神的关系)。
德氏文本在这个时候提到了一个插曲——但是,那只是一个插曲吗?——即这篇文章是夏皮罗为纪念其同事兼友人戈尔斯坦(Kurt Goldstein)教授而写的。戈尔斯坦,正如德氏文本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犹太人,1933年纳粹兴起后被驱逐出国,其后经阿姆斯特丹,前往纽约,就职于哥伦比亚大学。
此中存在着许多东西需要释放、归还、复原,即使还不是赎罪的话。很有可能夏皮罗没有满足于仅仅向一个逝者表示感谢,因为是他给了他所读的东西(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他还出于对他的同事、伙伴和友人,一个流放者、移民、城市居民的回忆,提供了,
——一个分离的部分,一只割下来的耳朵,但是是从谁身上割下来的耳朵。
——被取回、快速移走,或者从一个共同的敌人身上,或者,在任何程度上都是从共同敌人的共同话语中,扯下来的一双。
对夏皮罗来说,而且也以真理的名义,这是一桩再次发现其双脚的事情,一桩取回鞋子,以便让正确的双脚穿上它们的事情。首先通过断言那些鞋子是一个移民和城市居民的,“是艺术家的,而直到那时他一直生活在小镇和城市里”,事情后来变得异常复杂,因为事实是,这些移民从来没有停止过发出乡村的、手艺人的和农民意识形态的话语。(Ibid., pp.272-273)
这段话被打断了两次(如果这是三个人在对话),或者被打断了一次(如果这是两个人在对话,第三段重新回到第一段那里),总之,这就是我大段引用,尽量想保持原样的原因。

梵高《一双鞋子》1888
接下来,德氏文本重构了夏皮罗与海德格尔通信的情景:夏皮罗询问海德格尔他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里所提到的那幅凡·高的画究竟是哪一幅,而海德格尔非常善意地答复说是他1930年在阿姆斯特丹的一次展览上看到的。夏皮罗根据那年展览的图录,确定他所说的是哪一幅。不管这个重构是否有意思,其字里行间的意思不难看出,即夏皮罗有意“构陷”海德格尔。
在我看来,这是德氏文本批判夏皮罗的两个主要观点之一,一个德性缺陷(另一个是说夏皮罗持有学院派艺术史家的那种教条性,一种智性错误。详下)。因为,这是德氏文本的诛心之论,即穷究夏皮罗的不良动机。整个事件,仿佛都是夏皮罗给海德格尔下的一个圈套。
然而,
我将回到我的问题:它们是分离的……其中一只与另一只是分开的,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它们形成一双。如果我的理解是对的,没有一个标题称这幅画是“一双鞋”。而在别的地方,在一封夏皮罗引用过的书信里,凡·高谈到了另一幅画,称它为“一双旧鞋”。难道不正是这种“不是一双鞋”的可能性……不正是这种虚假的配对的逻辑,而不是虚假的同一性的逻辑,构成了这个陷井?我越看这幅画,它看上去就越不可能行走……(Ibid., pp.277-278)
这里的意思似乎是在说,夏皮罗想要“构陷”海德格尔,但这需要一个前提,即那幅画本身就是一个陷井。因此,想要“构陷”海德格尔的夏皮罗本人,也落入了这幅画本身的陷井之中。不过,这一点却遭到了德氏文本里的某个对话者模棱两可的否定。
——是的,但是事情真要这样的话,那“不是一双鞋”就必须有可能,而这种可能性,我得说,是一种非常有限的可能性,几乎不可能。更有甚者,即使凡·高曾经给这幅画取名为“一双鞋”……那也不会改变它的任何效果,不管这种效果是有意还是无意追求的。(Ibid., p.278)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位对话者先是怀疑那“不是一双鞋”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确实非常小。接着又否定作者的取名不会改变画面的效果。后面这一点当然是现代或后现代谜们耳熟能详的:意图的谬误,作者之死,文本之外一无所有。但是这位对话者又将作品的效果提到了重要位置,好像在确定作品的主题上,甚至连作者的命名也无济于事,重要的只是作品的效果。而效果,问题在于,在不同的读者或观众那里,几乎不可能是一样的。因此这就回到了原点:你说凡·高的鞋子看上去是两只左鞋,而我却说那明明是一双嘛!
让我们提一个天真的问题——这种提法必定已经超越德氏文本所规定的“从效果上判断”,或单纯从文本里作出推断,因为这已经诉诸文本之外的世界——
凡·高究竟有没有可能画两只左鞋?
从理论上说,这种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例如,凡·高无意中拿错了鞋子——假定他房间里有不止一双鞋子,而他碰巧将两只左鞋做了拉郎配;或者,他有意制造一个恶作剧,故意画了两只左鞋,设下了一个陷井——正如德氏文本所说的那样——仿佛只是为了制造哲学家们和艺术史家的一场论战)。但是,这种可能性是极其微小的——正如德氏文本中的其中一个对话者已经指出的那样。
然而,即使是极其微小的,只要在理论上存在着“那不是一双鞋”的可能性,那么,德氏文本在批判海德格尔认为那是一双鞋,并将主观想象投射进那双鞋(农民鞋)方面,同时又在批判夏皮罗认为那是一双鞋,但犯了同样的错误(武断地断言那是艺术家本人的鞋子)方面,至少是有理由的。而且,凭了理论上的这一点可能性,德氏文本就足以质疑海德格尔和夏皮罗在认定“那是一双鞋”这一点上的笃定和确信。但是,仅凭理论上这一点可能性的论说力,到了现实中,究竟还剩下多少?一旦我们走出单纯的文本——这一点必定是德里达所否定的,在他看来,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它的说服力和有效性还剩多少的问题,对德里达来说无疑将是致命的。因为,从根本上说,它就如同那个古代怀疑论者的命题,其效力只在质疑确定论者和迷信者上面,才有一定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它的效力只在否定性(negative)方面。至于它本身能够提供多少关于现实的正面(positive)论说,这本身就是可怀疑的。而且,从逻辑上看,一个绝对的怀疑论者也将面临那个克里岛的说谎者的悖论。一个绝对的解构论者同样如此。
被阿姆斯特丹凡·高博物馆馆长里奥·杨森(Leo Jenson)誉为“未来数十年里都将是权威的凡·高传记”的《凡·高传》(Steven Naifeh & Gregory White Smith, Van Gogh: The Lif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1;中译本《梵高传》,沈语冰、宋倩、何卫华、匡骁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10月版),有多处涉及凡·高所画的鞋子。
例如:
离开科尔蒙工作室以后,文森特不得不画他弟弟收集的小型裸体石膏像。像在纽南的时候一样,他孤独地坐在画室的器物之间,画一些充分折射出他的挫折和遗憾的静物画主题。在一双磨损的靴子里,他发现了完美的隐喻;他以在教堂街画鸟巢的那种忧郁和深思的笔触,画了这双靴子,就好像它正渴望着在荒野里行走的那份自由。(Steven Naifeh & Gregory White Smith, Van Gogh: The Lif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1, p.518)
凡·高的向日葵同样如此。他选择了一种特别在晚夏季节开放的花卉,画了一张三联画。将它们放在一起,它们表现了——在文森特那喜欢隐喻的头脑里,它显然是有意想要表现的——对那个灾难性的夏天的叙事。它们第一次成为他的主题:向日葵。他曾以一种沉思而反省的目光,观看空空如也的鸟巢被遗弃,破破烂烂的靴子跋涉过的徒劳无功的旅途,如今他以同样的眼光打量这些盛开的花朵。(参Ibid.,p.549)
与左拉或都德不同,文森特不可能报道或想象别人的生活,也不可能感受到别人的痛苦或欢乐。无论是画他的靴子还是画他的安乐窝,趟在海滩上的船只,路边的蓟类植物,或是围着桌子吃饭的一家人,所有这些作品都是他观看自己内心的窗户。“我总是感到自己是个旅行者,”他8月份写信给提奥说,当时他第一次打算画咖啡馆。“要去某个地方,某个目的地。”(Ibid., p.636)
这些传记“事实”表明,鞋子或靴子在凡·高那里拥有独特的隐喻意义,它们的信息是清楚无误的。而所有这些细节又与这部新传记所刻画的凡·高形象循环论证:在凡·高那颗充满了隐喻的头脑里,他所选择的几乎每一个绘画主题,都具有独特的意义。
请别误会我会天真到认为一部传记所写到的这些“事实”,足以否定凡·高所画的不是一双鞋,而是两只左鞋这样的哲学高论。而是想要说明:哲学家或怀疑论者所断言的东西之少,并不比艺术史家或传记作者所断言的东西更多。
本质上讲,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工作:正如哲学家们和怀疑论者们忙于解构或怀疑一样,艺术史家和传记作家们则忙于建构某种东西。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建构,解构就没有任何着落。没有解构,任何建构也就有可能忘掉其“建构”的事实。
当然,我一点也不想论证,德氏文本在指责海德格尔和夏皮罗的笃定和确信这一点上有什么过错。我的观点只是:它是并且只是以一个怀疑论者的口吻,来指出那些教条论者和谜信论者的缺陷。因此,在这么说时,德氏文本仍然是有理由的:
如果说夏皮罗指责海德格尔不顾这幅画的内在和外在语境,以及八张画有鞋子的画充满差异的连续性,那么,夏皮罗本人也应该避免一个完全相应的、对称的、类似的鲁莽之处:那就是不顾海德格尔那篇长文的语境,在没有防范措施的情况下,从他的文本中孤立出20来行文字,将它们从夏皮罗根本不想知道的框架中粗鲁地扯下,迅速攫住它们,然后以一种海德格尔在声称那双“农民鞋”时一样的神定气闲来诠释它们。(Jacque Derrida, The Truth in Painting, p.285)
我也不断言德氏文本在批评海德格尔这一点上有什么过错:
然而,假如思之路上这一“后退一步”(backward step)被设想为退回到“主体”(subjectum)背后,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将一幅画中的鞋子归属于这样一个确定的“主体”,那个农民,甚至,那个农妇的那种天真、冲动、前批判的做法呢——正是这一密不透风的确定归属的行为及其决定性,指引着论绘画与“真理”的整个演讲?正如我刚才所做的,我们大家都同意称这种姿态是天真的、冲动的和前批判性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