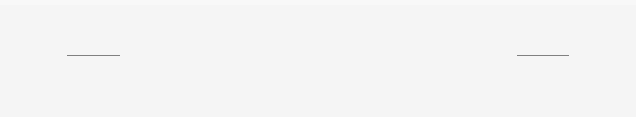

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作者 | 普通老师
本号原创
昨天一个保研的大四学生来我办公室聊天。她的来意是想预定我明年的招生名额,不好意思地说自己本科期间没读过什么教材之外的书,想研究生三年认真读一读书。
我跟她聊了一个多小时,希望把我对书和本学科的热爱传递给她。
临走时她说,高中之后就再也没有老师跟她说这么理想主义的话,跟她说读书是有用的,她很受鼓舞。那么我们如今的大学老师都在跟学生们说什么呢?
如果我是异类,希望我不会害到我的学生。
经常有人批评我身为社会学教授“不懂国情”。
我这些年始终坚持亲自写每一封推荐信,无论中文还是英文,每一封信都是量身定制、亲自打印在学校的彩色信纸上、亲自扫描、亲自上传到申请系统里;
每次答辩,无论多少人,无论是开题还是最终答辩,无论是本科还是博士、博士后,我都坚持提前阅读每一篇;
每次有学生找我,我都会安排在两天内见面,无论那两天我原计划去不去学校;
培养学生,我从不让研究生给我做项目,从不把一本书分给学生每人写一章,从没有让学生给我写过课题申请书。
这些在别人眼里都是不懂国情的体现吧?
且不论社会学从业者是不是必须“懂社会”(总不成数学系老师“最不懂社会”),
我觉得社会学教给我的是,大家都觉得正常的,我能看出不正常;大家都觉得不正常的,我能看出正常。
今天早晨忽然意识到,自己成为这个学校的老师已经整整四年了。
前两年滞留美国不算,这两年最开心的时候是学生写出一篇优秀的论文、跟我一起去开学术会议并上台发言、保研或出国到名校、找到满意的工作、在我面前兴高采烈地谈自己对专业的兴趣、下课后堵住我说她对课上的内容意犹未尽、跟我说老师我想考你的研究生。
最不开心的时候是报发票、身不由己地隔三岔五开各种会、答辩时发现学生压根没读过几本书以及遇到了喜欢的学生却发现自己没有招生指标。因为跟学生“走得近”,遇到了一些误解甚至批评,我自觉问心无愧但也有所反省。
但无论如何,
在我眼里,任何一个学生,他的人生、他的前途都是神圣的、需要我们老师小心呵护的。
在这所大学教书,读书的好苗子并不算太多,但每年都能有幸挖掘几个。
令人五味杂陈的是,这些亲自培养过的好苗子几乎无一例外都选择去其他学校深造。
领导跟我说过不止一次:
“你跟学生关系好,学生听你的,能不能让他们留在本院读书?”
但这又岂能是我几句话就能扭转乾坤的?昨天我还跟自己想读博的硕士生说:
“想继续跟我读博,欢迎;想去更好的平台,那更好,不用顾及我的感受,一切以对你最好为标准。”
我让他开个单子,把心仪的学校和导师列出来,我帮他把关并想办法联系导师。
下午全院大会,院里让我和几位老师谈谈指导学生的心得。
很感谢领导的信任,但我其实真的没什么心得,因为我不知道如何指导学生,我很幻灭,很愤怒,我不知道如何让学生明白在学校最重要的事是读书,如何让学生明白要想读好书必须读书,要想读书必须读好书。
学生问我如何能像我一样自如地用英文阅读和写作,上新东方行不行,我说我读书时桌子前几十本英文书要读完,学生听了跟听了八卦一样;
学生说不知道论文怎么写,我说你写了什么先给我看一下,没有;
学生说不知道对什么感兴趣,我说你把几个领域最经典的书看一下或者把我开的书单挑一些感兴趣的书读一读,读完跟我说说感想,没有下文。
大环境有问题,我也没啥本事,下次只能告诫自己在对学生大发澎湃的学术激情之前,先想一下回国这两年培养出了学生了吗,也许这样就可以少要一点学生了。
下午参加了几场博士答辩,都是自己学院的学生,所以很开心他们都能顺利完成这最后的考验。
其中一位学生说他答辩虽然通过,但并不觉得开心,因为觉得论文写得不够好。我当然希望他能开心一点,但也完全明白他的心情。我自己博士论文答辩后也没觉得如释重负,反而只为论文本可以写得比这鬼样子好得多而感到难过,反而只有
“如果当初……就不会如此”
的难以摆脱的自责。
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最好的状态是学得带劲、玩得开心,但我想,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是学得不来劲,玩得也不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