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朝博物馆藏南朝偏幰牛车画像砖。公元445年,史学家范晔因谋反罪被诛,负责《后汉书》十志工作的谢俨惧怕受到牵连,将成稿施蜡覆车,大概就做成类似于画像砖上的这样一张为牛车遮阳的车幰。建康街道上奔驰的一辆牛车,也许就是《后汉志》在世上的最后一次亮相。
文︱于溯
诚如您所看到的,本文题目是对马克·布洛赫的致敬与剽窃。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布洛赫把自己称作“年迈的工匠”和“手艺人”,这当然是一种谦虚,但历史学家本也确乎需要手艺。中古纪传史的作者没有像布洛赫那样为我们留下一本“手艺人的工作手册”或“技工的笔记本”,对他们的作品,我们又不是当成史料来读,就是当成词章来读,好像双方有种默契,都对技艺避而不谈似的——这也使我在写下标题时,竟有种故弄玄虚的感觉。按理说,技艺是最不玄的东西,虚倒可能是有的,因为我们得寻虚逐微,自行到史书中去寻找那古老的技艺。小文草列四条,愿能因虚得实,为中古史学家的技艺库打开一道裂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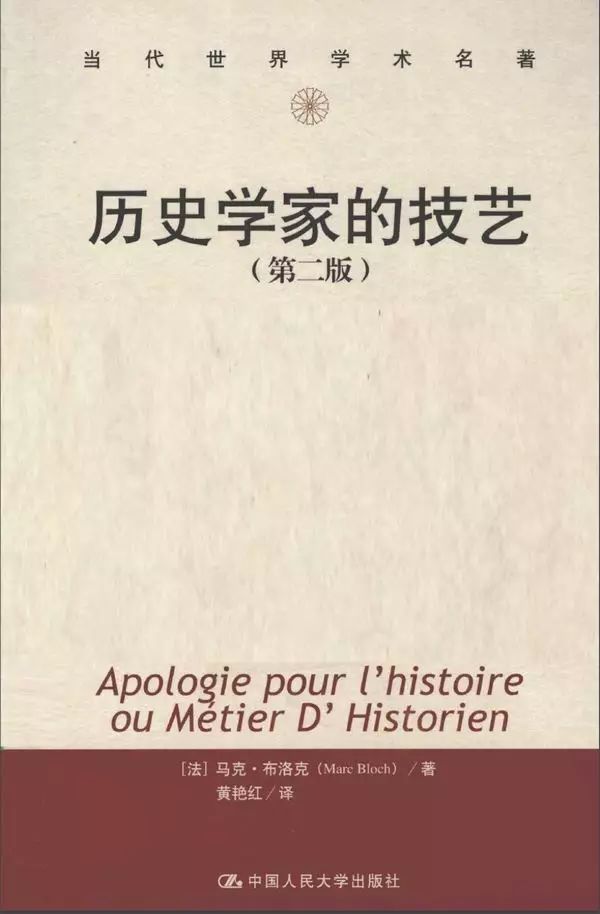
结构的法则
一部著作呈现给读者的最宏观信息就是它的整体结构。魏晋南北朝人编纂的纪传体史书,既遵循着《史记》《汉书》设立的基本框架,又在此前提下各有各的调整,各有各的特色,借用当时一个文学评论的词汇说,就是“体有因革”。尊重传统、贴合时宜、便于操作,这是我们从中看到的三大编纂法则。反过来也可以说,这些纪传体史书的最终呈现结构,就是这三个法则三方合力的结果。
对今天的读者而言,史书结构设计的“贴合时宜”是最易引起关注的地方,因为这个时宜代表了某种历史动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六世纪中叶问世的《魏书》中有一篇《释老志》,这个书志主题是前无古人的新创,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宗教在当时社会生活中角色的日益重要。但一个相反的例子是,五世纪晚期,南齐议修国史,曾有计划要设立一个《朝会志》,最终却因此志“前史不书”而未行。在后一个案例里,发挥作用的力量就是传统。时宜法则的效果常落在明处,它让你“看到什么”;而传统有时施力于暗处,让你“看不到什么”。自司马迁以下,两千年间社会形态、政治结构几经巨变,但最应该反应这些内容的历代正史书志,其设目却始终变动不大,这就是编纂者遵从传统、涵盖旧题的意识,牵制了史书通过创设志目反映社会新变的能力。所以传统作用虽然隐蔽,能量却不容小觑。
时宜和传统是一对互相牵扯的力量。中古纪传史多立八志(如司马彪《续汉书》、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或十志(如蔡邕《十意》、华峤《汉后书》、束皙《十志》、范晔《后汉书》、魏收《魏书》、江淹《齐史》、唐修《五代史志》),这也是遵从《史记》八书、《汉书》十志的传统。所以自我作故的《释老志》似乎是时宜法则的胜利,但它同时也意味着《魏书》必须放弃一个传统的书志主题——总不能有十一个志。类似地,定额八志的《宋书》没有《刑法》《食货》,但沈约也特别交代了相关内容都散在纪传里。总之,在传统和时宜之间,每个史家都有自己的平衡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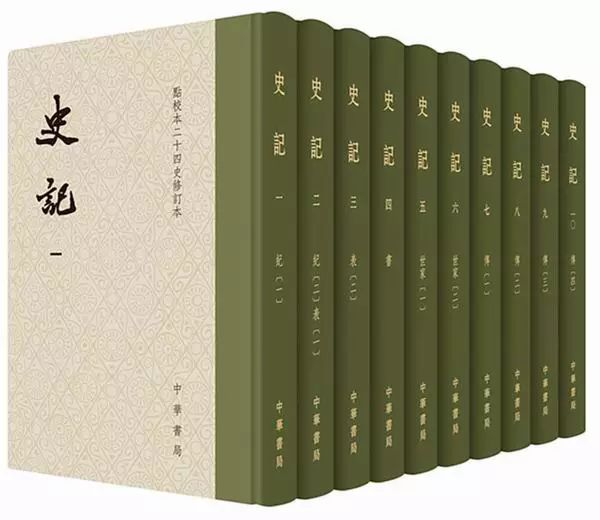
史书的结构设计同时也遵循着便于操作的法则。在对陶渊明的研究中,我们常能见到这样一种看法:诗人在《宋书》《南史》《晋书》中稳居《隐逸传》,可见史撰者不甚以文学家目之。其实从史书结构设计的角度考量,这个解读可能就求之过深了。《宋书》不设《文学/文苑传》,沈约根本不用去考虑“陶渊明首先是个诗人还是首先是个隐士”的问题。在以政治史为核心的正史中,陶渊明既不可能获得单传,那么把他归入其他类传,或者像鲍照那样附于他传,几乎是必然方案。《宋书》布置如此,后史难免因循,《南史·文学传》的照抄度竟然到了,因为《宋书》没有《文学传》,《南史·文学传》里就不见一个刘宋人,遑及陶渊明。陶渊明在其时文坛地位不高,自有其他材料可证,传列《隐逸》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论据,因为我们不能忽视这个结构安排里的便宜因素。我们得承认古人也有图省事的心态,并非他们的每一处设计都有深衷大义,甚至在“完美的设计”和“因循史源原生态”之间,他们有时也会选择后者。
结构设计者不仅会考虑到自己的操作方便,也会照顾到读者的操作方便。在南北朝史学中,以裴松之《三国志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等为代表的、被陈寅恪先生称为“合本子注”的新史注形式,一直备受学界关注;诞育“合本子注”的学术背景,尤其得到了多角度阐发。不过学术背景解释的是人们为什么需要这样一种“内容”的著作,除此之外,我们也应该问:人们为什么需要这样一种“结构”的著作?无非为了阅读方便。在书籍随处可得、装帧便览、页码易检的今天,我们想要对读几种著作中的相关材料,还要摊上一桌子书,何况裴松之们生活的中古时期。其实合本子注和集注、类书一样,都是通过一种结构革命,实现一书在手、众本在握的功能,只不过实现的角度不同而已。总之,便于操作法则关系书能不能编出来、编出来口碑好不好的最实际的问题,因此是任何史书编纂者都不会忽视的。
时间轴的奥秘
历史是依时间展开的,编年史也好,纪传史也好,都不能脱离时间性的本质。其区别惟在于,编年史遵循单一时间轴,而纪传史拥有多条轴线:帝纪提供帝国时间的主轴,列传实系在这根主轴上,大致依次排开;列传中又有自己的小时间轴,它们潜伏于叙事中,伴随叙事逻辑而行。
传记不是年谱,时间轴不存在于叙事之外,所以在阅读时,我们很难像读年谱那样清晰感知时间轴的推进速度,体察到它的快进和慢放——有时几页纸只走了数日,有时一行字带过了数年。另一种难以清晰感知的操作是,随着话题的转换,时间轴还会发生回退,比如这种:
年三十,犹未婚。妹适东莞刘宪之,穆之子也。穆之既与延之通家,又闻其美,将仕之;先欲相见,延之不往也。后将军、吴国内史刘柳以为行参军。(《宋书·颜延之传》)
这段话乍读起来,好像一直在叙述传主三十岁以后的事——实际上在后人编写的几种颜延之年谱里,颜延之就因此被认定为三十岁起家,尽管以颜的社会阶层来说,这个年龄显得晚了些。可里面其实出现了两个主题,一个是婚,一个是宦,两主题间存在叙事逻辑先后关系,未必存在时间先后关系。如果我们利用刘柳的相关履历材料排算一下时间,完全可以确定颜延之参加工作的年龄在二十岁到二十二岁之间,这也就是说,从“妹适东莞刘宪之”以下,传记的时间轴已经悄悄退回去了。
时间轴带来的错乱感不止于此。有时是时间轴明确地正向行进着,我们反而怀疑它违背历史的真实进程。《宋书》写陶渊明“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明确把《五柳先生传》的写作置于陶渊明的青年时代。但是从清代开始,陶渊明的研究者就因这篇名文的系年分裂成了“少作说”“老作说”两个阵地。“老作说”表示,一个还没有走入社会的青年怎么就会有避世的念头呢?《陶渊明传》的编纂者到底清不清楚写作年代?把《五柳先生传》放在全传的开头,莫非只是想为传主的人物性格打个基调?这些针对《陶渊明传》时间轴的质疑都有道理,但也都无从解答。更可怕的是,如果我们将《五柳先生传》拆开,逐句和《汉书·扬雄传》对比:

还能得出“少作”“老作”外的第三说:陶渊明只要读了《汉书·扬雄传》,或者读了在《汉书·扬雄传》基础上改编的某种传记(比如嵇康《高士传》中的《扬雄传》),他就可以仿写出这么一篇《五柳先生传》,无论在少年还是老年的时候。如果《宋书》的时间轴是符合事实的,那就是符合事实的;如果是人为架构的,我们也无法复原出事实的那一条。我们永远只能看到史书而不是历史中的时间轴,也只能忍受它被叙事逻辑和叙事策略操纵扭曲后的样子。
叙事模块
中国古典文献是一个模块化的世界。所谓模块,就是一个系统中具有功能独立性的、可拆卸、可更换的植入单元。举个例子说,宋代一些作家提倡创作要“无一字无来处”,这就有点像借助植入名家开发的模块来确保自己的产品质量——“灵丹一粒,点铁成金”,如果写一首诗,全部用杜甫或陶渊明开发的模块拼装,那产品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史传的叙事也是这样,三史开发或者使用过的模块广受欢迎,就因为它们是学习史传写作的经典读物。两《唐书》记载了一个特别能展现仁君形象的事件:贞观六年岁末,唐太宗释放了二百九十名死刑犯,让他们回家过年,并与其约定秋末要自来就刑。结果到了行刑日,二百九十人全数返回,皇帝就把他们都赦免了。这个故事不仅两《唐书》有载,还有白居易的《七德舞》歌颂之,欧阳修的《纵囚论》批判之,可见相当引人注目。但唐太宗的事迹绝非个案,“纵囚”是一个在史书中出现频率极高的模块,宋代以来的学者对此屡有统计,综合他们的数据得到的结果是:《后汉书》中出现五次,《晋书》两次,《宋书》一次,《梁书》三次,《周书》一次,《隋书》一次,《南史》增两次,《北史》增一次,两《唐书》去复合四次,《宋史》两次,《元史》两次,《明史》一次。一个叙事模块能受欢迎到什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一种书写策略,模块化的大受欢迎是有道理的。模块化的核心精神是分解,即将文本系统预分割为不同的功能区域,再选取合适的文本模块进行接口修改、调试,完成系统的拼装组合。因为不同模块可以由具备不同技术专长的多方并行开发,所以系统搭建的效率将大为提高。小朋友写一篇《有意义的周末》,也知道使用“给灾区寄钱”“扶老奶奶过马路”“带病义务劳动”等等模块,就是因为这样做能减少他们耗费在构思“如何叙述好一个情节”上的时间。模块是雷锋叔叔开发好的,功能和质量有保障,眼下还要做的是修改模块接口,使其能插入自己的系统。所以模块化写作的最重要环节就是修改接口,比如:
卓茂为丞相史,尝出,道中有人认茂马者。茂问失马几日,对曰:“月余矣。”茂曰:“然此马畜已数年。”遂解马与之,曰:“即非所失,幸至丞相府还我。”乃步挽车去。后马主自得马,惭媿诣茂。(《艺文类聚》卷九三引《东观汉记》,《后汉书·卓茂传》略同。)
刘宽尝行,有人失牛者,乃于路就宽车中认之。宽无所言,下驾步归。有顷,认者得牛而送还,叩头谢曰:“惭负长者。”宽曰:“物有相类,事容脱误,幸劳见归,何为谢也。”(《艺文类聚》卷九四引谢承《后汉书》,《后汉书·刘宽传》略同。)
尝有失牛者,骨体毛色,与(刘)虞牛相似,因以为是,虞便推与之;后主自得本牛,乃还谢罪。(《三国志·公孙瓒传》裴注引《吴书》)
(王延)家牛生一犊,他人认之,延牵而授与,初无吝色。其人后自知妄认,送犊还延,叩头谢罪,延仍以与之,不复取也。(《晋书·孝友传》)
很显然,这四个传记植入了同一个模块,其间一个微妙的变化是,卓茂的事迹发生在西汉末,那时官员乘马车出行;刘宽、刘虞、王延的事迹都在东汉中期以下,那时出行已经以牛车为常,牛也跟着变得重要起来,而三人的传记中,出现的恰巧都是牛。“牛”就是这个模块的新改接口,模块通过改好的接口分别插入三个新文本系统,兼容无碍,运转正常。这样看来,模块上没印着出产商的LOGO,若史撰者又植入得完美,如盐入水,了无痕迹,抓“侵权”殆非易事。不过后世学者也颇有挑战兴趣,宋代以来不少学术笔记中都有这个抓模块的主题,像王世贞在《宛委馀编》里著录了六十四个史料模块,并用很欣喜的笔调记录下来,比如“梦赠笔,人知有江淹,而不知有王彪之、王珣、纪少瑜、陆倕、李白、和凝、马裔孙”。
诚如王世贞所暗示的,在模块的反复使用中,总有一些使用案例比较成功(“人知有”),一些不那么成功(“而不知有”)。提起县政府里有谁因为受不了接待督邮而辞职,大家想到的肯定是陶渊明而不是冯良(冯良事见《太平御览》卷六六六引《抱朴子》:“冯良者,南阳人,少作县吏。年三十为尉佐史,迎督邮,自耻无志,乃毁车杀牛裂败衣……州郡礼辟不就。”)汉末蜀人张松有过目不忘之能,其事经《三国演义》的渲染和传播,几乎家喻户晓,其实在汉唐史料中,这个“过目不忘”模块也是多如牛毛。可见“人知有……而不知有……”的危险,倒不在于不知有,而在于读者一旦不知有,就可能拿着一般当特殊。
就像“过目不忘”一样,很多模块是有时代性的。史传模块的时代变化轨迹和真实历史的变化轨迹可能呼应但不完全重合。从生物学的角度说,我们不可能认定人的记忆力会在某个时期会更好一些;从文献史的角度说,我们也很难认定记忆行为的高潮既不落在书写条件更不发达、口耳授受更被依赖的上古,也不落在书籍流通更广泛、士人文明更发达的近世。现象“存在”和现象“被意识到存在”应该分别看待,一个史传模块从出现、激增到消亡的曲线,更多地暗示着一种社会关注点的更迭,或者理解角度、思维模式的转型。
在中国古典文献中,模块化书写广及四部、纵贯千秋。作者运用愈妙,读者求索愈深,你藏我捉,兴味盎然。有意思的是,对史传中的模块化现象,古人并不特别关心它与历史真实性之间的关系。充其量,出现在同期史料中的模块,人们解释为“传闻异辞”;出现在异时的,就是“事有偶同”。也就是说,在古人看来,模块化这种书写方式本身并不为真实与否负责,因此他们识别到模块后,感到的不是对虚构的焦虑,而是“人知有……而不知有”的喜悦。这是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尤其鉴于模块的阅读者往往也是模块的使用者,我们不能说对真实性的漠视只是一种习焉不察。事实上,阅读会规训人们的思维,使人们以阅读给与的角度去理解和捕捉经验世界中原本千差万别的现象;阅读也会引导人们的行为,使人们将阅读经验转变为现实经验。换言之,现象一旦“被意识到存在”,就会引发更多的“存在”。纸上的模块化必会引发实际行为上的模块化,这二者确乎是难以切割的。
让舆论热起来
在传统社会,很少有史书的写作能完全摆脱外部制约力而纯然呈现作者的自由意志,近代史、当代史的编纂尤其如此。不巧的是,由于汉唐间政权更迭频仍,不少史学家就是在处理去己未远的史料。正统问题,限断问题,时讳问题,定性问题,都在牵制着史学家的笔,影响着史书的最终面貌。
干涉的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向:官方,以及传记的直接利益关系人。如果史传被认为损害了朝廷形象,甚至动摇了本朝的合法地位,必会招致残酷打击,前秦史官就曾因记载某些宫闱秽事,引发苻坚对史官队伍的清理,涉案文献也被悉数焚毁。越是时局动荡、政治严酷的时代,越需要善为时讳的史书,像魏晋之交王沈等人修撰的《魏书》,就属于这种性质。前鉴既多,有高度政治敏感的史学家比如沈约,便会事先将可能引发争议的问题上报,主动要求审核,得到皇帝明确指示后再动笔。至于传记的直接利益关系人,主要是指传主本人或其后人。谢朓临死托人向沈约带话说,“君方为三代史,亦不得见没”,俾其为作嘉传。尔朱荣的儿子,据说竟能买通身丁河阴之酷的魏收,使得后者为其父文过饰非。干涉不仅可以通过友情和金钱施与,也可以通过权力。桓温就能以灭门相要挟,务使孙盛修改《晋阳秋》中对其不利的记载。而裴子野因沈约在《宋书》中写了轻蔑其家门的话,竟宣布要在《宋略》中揭沈家老底,可见史笔之间也有博弈和交易。
对史传实施干涉的形式,除了对作者人身打压外,还有封闭档案、禁燬作品等,总之多方阻止其成形或传播。萧梁时吴均撰《齐春秋》,梁武帝就是先拒绝开放档案之请,又焚毁他利用公开资料完成的著作。以上这些干涉,从性质上说都属于消极干涉,而当官方或其他投资方向史学家提供档案、物资、人力支持时,一种积极干涉又形成了。无论接受来自纵向还是横向的物质支持,客观上都等于将外力引入修史过程,其实像尔朱氏对魏收的干预,也未尝不可以视为一种文化资助行为。消极干涉因其见载于书,易为后世读者了然,而积极干涉颇难捕捉,我们只能通过一些史学家寻求支持的个案(比如北魏的李彪、南齐的王智深、上文提到的吴均),体察他们常常面临的物质困境,从而理解外力渗入的无可避免。
史学家受到的干涉既多,舆论的猜度、攻讦甚至造谣也就随之而至。舆论的纷繁程度最能以陈寿《三国志》见其一斑:有人说陈寿向人索取过立传费,有人说他因私人恩怨而书法不公;有人说《三国志》为中书监荀勖深爱,又有人说荀勖不满其书而打压陈寿。这些说法,一如沈约之好诬前代,魏收之好为秽史,虚虚实实,真假难辨。其实值得注意的不是真假虚实,而是这些舆论同样出自中古史书,换言之,中古史学家自己就是自己所处的纷纭舆论环境的制造者。在多维外力的作用下,史学工作者处境极其复杂,威胁与诱惑并存,危险与权力共生。对同行的刻薄议论,其实折射出史学界对外部环境的普遍焦虑感;而制造纷繁舆论,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对外部环境的反抗技艺。
这样看来,干涉虽无可避免,魏晋南北朝史学家对外力总归保有清醒认识,甚至有以特殊技艺反抗、嘲讽外力的自觉。但是,一旦外力演化为一套精密的制度,个体干涉升级为制度驯化,情境将大为不同。自唐代建立史馆,集体修撰、宰臣把关的正史生产制度确立起来,而这个制度的效果之一,就是极大消弭了史臣和外部环境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解决了双方自董狐南史以来的矛盾。在这样的情境下,反抗的技艺既毫无意义,也几乎无可施展了。
雠温社是我们南京的几位青年学者在2015年组织的读书会,两年来每周活动一次,共读中古史料。夫对读互正曰雠,因故知新曰温,又《魏书》云李奇冗散数年而与高允雠温古籍,读书会既未始有意于形式,因以“雠温”名之,兼志冗散也。本文是雠温社系列作品之三。
于溯
南京大学文学院
·END·
《南齐书》修订专题
景蜀慧谈《南齐书》的编纂、点校与修订
徐俊谈《南齐书》及“南朝五史”的点校与修订
胡宝国:南朝学风与社会
姚乐:南北朝时代的战争与和平
张金龙:南北朝时代的和平与战争
聂溦萌:“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中古的禅让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访问《上海书评》主页(shrb.thepaper.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