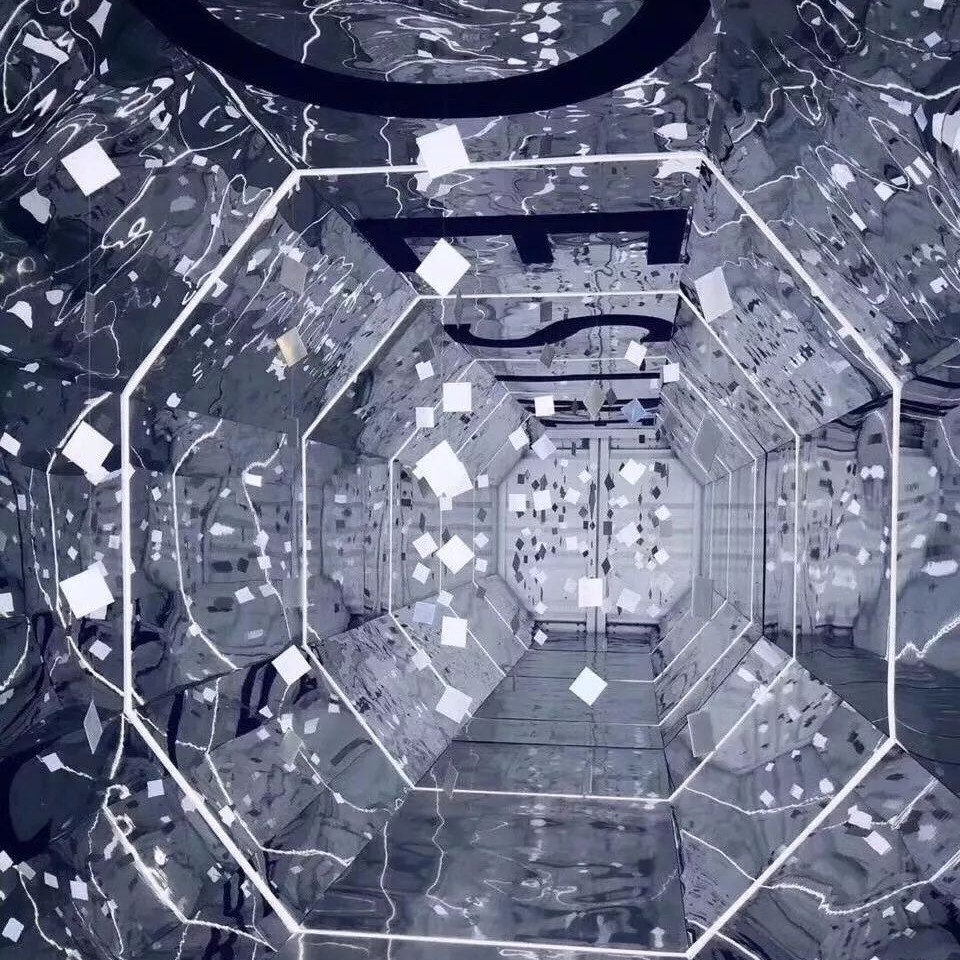戳上面的蓝字关注我们哦!
戳上面的蓝字关注我们哦!
杰伦·斯坦普尔:模式与描绘:
论贡布里希著作中“图式”的概念
按:1974年,汉堡大学为庆祝卡西尔诞辰一百周年举行纪念活动。贡布里希提交了题为“时间、数字与符号”的发言稿,该题目是为回应会议上的另一位发言人纳尔逊·古德曼的《语词、世界与作品》。二人虽是多年朋友,但彼此之间看法相差甚远。贡布里希认为,古德曼陷入了极端的唯名论和程式主义,夸大了惯习的作用。由于前者在《艺术与错觉》里强调图式的必要性,所以他越来越觉得有必要说明自己并非致力于以图画的程式或惯例基础来否定图画与自然的密切联系。《时间、数字与符号》的主题虽然不是图画,但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贡布里希在七十年代对图像、程式与自然三者间关系的再解释。因为此文着重论述了,人类在计算年数时所用的规约,“根植于自然事实之中”,正是自然中存在的年度循环现象,导致了人类产生时间轮回的观念,进而影响人们采用什么约定俗成的数字符号系统来计量周年……
万木春
译
当自然把无尽的长线
漫不经心的绕上纺锤,
当不和谐的森罗万象
发出嘈杂的声音:
是谁生动的划分出单调的流线
使它具有鲜明的韵律?
是谁把个别纳入整体的圣列,
使它发出美妙的谐音?
……
都是靠诗人启示人的能力。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
“舞台序幕”[1]
本文最初以德语写成,题为“Zeit, Zahl und Zeichen”(“时间、数字与符号”),[2] 之所以要取这个押头韵的题是因为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他也是会议发言者之一)的论文题为“Words,
Worlds and Works”[“语词、世界与作品”],而我不惴浅陋,想把我的标题和他的凑成一对。倘若一开始就用英语来写,那我可能会名其为“Nature, Norms and Numbers”[“自然、规范与数字”]。
这样的押韵游戏当然还算不上写诗,可是它和写诗却有共通之处,两者都是借助语言材料[donnès]——换句话说,借助一套预设的符号系统——来进行创造的。在这样的创造中,符号本身会影响符号所指以及创造者的初衷。在此,语言将一如既往,不仅反映创造者最初的思想,它还刺激创造者产生新的思想。我不否认,我搅尽脑汁要用德语妥帖押韵的标题对全篇的写作方案和意图都产生了影响。正是这个标题启发了我,使我决定不去泛谈卡西尔[Ernst Cassirer]和艺术之间的关系,而是以他的百年诞辰庆典作为主题。这个主题同样可以架起通往艺术的桥梁,因为据雅各布·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的见解,正是节日庆典将生活变成了艺术。
本次庆典是为恩斯特·卡西尔诞辰百年而设,我们计算了已逝的年数,给这一特定的数字指派了符号“100”。显然,经计算的每一个年份都是自然事实,它们的总和描述
的
也是一个客观事实,可是符号,连同帮助我们理解事物的符号系统,却源于我们的语言和文化。古希腊思想家把前者归于“physis”,即“自然”,而把后者归于“thesis”,即“惯例”。要是自然没有周期性,或者人类不具备从自然中发现重复性的能力,我们就无法抓住时间之流。我们采用的时间单位——不论是心跳、天数、月相圆缺还是季节——都出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其约定俗成的性质,并不亚于我们给数字指派意义。然而,不管自然事件和人为创造之间存在多么根本的差别,我们都不应将其夸大,因为惯例毕竟根植于自然事实之中,根植于人性之中——人的计数系统也不能例外。人类天生具有10个手指,为计数提供了自然的便利,而“100”等于10个10这一事实,最终也说明人类思维所受到的限制。具有无限创想力和记忆力的生物或许可以摆脱对系统的依赖,这生物能针对任意长度的数字序列中的每一个数给以特定的名称和符号,它还能给不在此列的数字增补一个目类。但是对人类来说,如此不对称、非结构性的数字序列,正像每个对象都有不同发音的极端唯名式语言[nominalistic language]一样,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人类一定得借助概念给事物分类,一定得建立事物和数字的级差秩序。只有将万物捕获进层级系统,人类才能理解世界。一切数字和计数系统都是如此这般建构起来的。数字“100”之所以从序列中凸显出来,是因为它是10的10倍,而在以“12”为基准的12进制系统中,具有同等心理和文化意义的数字当然是“
144”
。
宾根的希尔德加德《认识主的道》中“年”的拟人像
于是,人们的意识中常将自然的时间单位与人为设立的时间单位混淆也就不足为怪了。我们口说“里程碑式的诞辰”,心理却意识不到诞辰(已逝去的年数)本身并非“里程碑”,所谓“里程碑式的诞辰”实际不过是数字系统中为惯例所认可的一个整数符号。即将来临的“千禧年”所引起的不安情绪是说明同一谬误的另一个好例子。人类学会给数字指派意义,进而感到它们与年度的自然循环一样真实,不论从本次庆典看还是从庆典的普遍情况考虑,将“自然”与“惯例”混为一谈的趋势无处不见。
人对自然和自身机体的经验,使他对事件重复有所期待,甚至将时间看作轮回(史前文明和现存原始文化尤其如此)。[3] 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其《约瑟夫与他的兄弟们》[
Joseph and His Brothers
] 三步曲中极为透辟地描写了梦境般的轮回时间观。在题为〈地狱之旅〉的一节中他写道:
我们关心的不是用数字表示的时间,而是数字时间的废除以及取而代之的神秘传统和预言。这意味着“从前”这个词不仅适用于过去,也适用于将来,于是我们获得了对现在的把握。这就是转生这一观念的根源。
尼采[Nietzsche]的“同一物的永恒复返”可算是这一观念最极端的版本,而古代斯多葛派[Stoics]哲学家也表达过同样的观念。据说克里希普[Chrysippus]曾经说过,“将来会再出现一个苏格拉底,再出现一个柏拉图,他们将交上和原来一样的朋友,同邦的公民也和原来一样。他们的再次降临将不只发生一次……而是不断复返,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在这一上下文中的含义为“无数次”。我们不禁想知道,人类的计数能力(无穷数字序列的概念)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适当符号的发明?而主流时间观念是不是符号和数字塑造的结果?对此我们显然不可过于教条,但是以持续的方式来标记某个事件,也就是说将它标记为“符号”,的确可能开发我们的能力,使我们能够比较自然界的各种循环,由此确定它们的持续时间。我马上想到的例子是人类对天体的观察。天体观察是人类文明最早的成就之一,各个文化传下了不同历法,迄今仍伴随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正是通过观察天体,人类才能计算冬至日和夏至日之间的天数,或是这期间月相变化的次数。这些自然界的循环一度难于被人和谐地理解为一体,但是从能够理解之日起,时间之流便就范于人类,“将来”也被驯服。没有这一创举就不会有日历,当然更不会有各民族日历上的周年纪念。[4]
不过,周年纪念的概念不同于节日庆典。许多社会和宗教中都有专为个人设定的纪念日,比如丧考周年纪念日(日本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纪念日)。有时周年纪念甚至为了罪案而设,奥地利刑法就规定在罪案发生周年那一天额外给予罪犯“睡硬床、食劣质面包和水”的特殊惩罚。但是一般来说,周年纪念日的设立都会吸引社团成员广泛参预,与个人同庆,由此周年纪念便天衣无缝地与庆典融为一体。
从心理学上讲,这类及相似的宗教节日都与轮回时间观紧密相联。预设的仪式及其经过艺术修饰的变种意在刺激信众,使他们如临其境地重新体验被纪念的事件,而完全忽略当初事件和当前庆典之间的时间间隔。然而,认为年年向前的线性时间观在此也有它的角色。据《路加福音》记载,耶稣于最后的晚餐席间告戒门徒:“为纪念我,你们要这么做”——这一要求通过弥撒献祭仪式由一次纪念变为不断重复的纪念。在莎士比亚笔下,事件同时就是节日纪念的预言:
——《亨利五世》第二幕第三场[实际出于第四幕第三场,译文用蒋坚松译本——译者]
在这个例子中,周年纪念分明是植根于日历中的。而莎士比亚还写过更加意味深长,也更为不祥的一段,那是《尤里乌斯·恺撒》第三幕紧接恺撒被刺的一场戏,布鲁图斯预言了将来纪念节日上的仪式,可这预言竟未实现:
众所周知,现在人们并没有为尤里乌斯·恺撒设立纪念日,但是人们用整整一个月作为他的纪念,“七月”[July]就是以他命名的。这也足以使他永垂不朽了。
同样一种对不朽的渴望激发贺拉斯[Horace]写下颂歌,坚称“无论是迁延无尽的岁月还是飞逝的时间”,都不能有损于他业已创造的成就:
Exegi monumentum aere perennius
Regalique
situ pyramidum altius
Quod
non imber edax, non aquilo inpotens
Posit
diruere aut innumerabilis
Annorum
series et fuga temporum.
Non
omnis moriar, multaque pars mei
Vitabit
Libitinam: usque ego postera
Crescam
laude recens, dum Capitolium
Scandet
cum tacita virgine pontifex.
中国诗人李太白也具有同样的信心,[5] 尽管表现不同,但他的诗意与轮回时间观并无抵触。从纯粹逻辑的角度来看,线性时间观和轮回时间观不能相融,可在人类的意识中,它们并非那么不能相融。
年度循环是人类最基本的思考依据,这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这样一种时间观,即大的时间轮回是由一系列时代的循环、复返和再生构成的。这种时间观固着于许多高级文明的神话中。古印度对构成时间轮回各时代长度的说法是最大胆的,而且与他们的十进制计数系统关系密切。大时[mahayuga]由4个不相等的时代构成,总共12,000年,而这只相当于圣年的1年。360圣年构成1个宇宙循环,因此1个宇宙循环共有4,320,000年。1,000大时构成1劫[kalpa],而1劫只相当于梵天[Brahmā]生命中的1日。以1劫为1日,梵天的生命将持续100年,到那时旧时间将终结而新时间将开始。[6]
柏拉图在《蒂迈欧篇》[
Timaeus
]中谈到“大年”[“Great Year”]。大年是一个宇宙时代,当大年结束时,所有的行星将重归原位。在《治国篇》(旧译《理想国》,现从王太庆,作《治国篇》——译者)的一段里,柏拉图似乎表明1个大年循环等于360年。后来在维吉尔[Virgil]的第四牧歌中又出现了类似概念,到中世纪被解作对救世主的预言:
ultima Cumaei venit iam carminis aetas;
Magnus
ab integro saeclorum nascitur ordo.
Iam
redit et virgo, redeunt Saturnia regna.
上述这些例子也许充满玄奥的知识和期待,未能触及普通人的生活。相比之下,墨西哥古文明的时代循环要短得多,短得足以影响社团的日常生活。在古墨西哥人的观念中,52年为一“集束”,当52年循环结束时所有明火都得熄灭。这一文化举行残酷的人牲仪式,坚信新的火焰将从一名人牲的胸膛中点燃,进而传遍各地。
迄今对西方文化产生最大影响的轮回时间观要数古代犹太人的拱形时间观。它的要点见于《利未记》第25章,这一章的内容是对农时的规定。正如人在每周的第7天要休息,耶和华规定田地在耕作的第7年也必须得到休息,届时田地休耕,等到7个7年(共计49年)循环完毕之后,《旧约》规定下一年用来欢庆,因此每隔50年就有一次禧年。詹姆斯王钦定本《圣经》是这样表达的:
当七个安息年已过,就是七个七年,也就是四十九年已过。你们要在
七月十日
这天吹响欢庆的号角[trumpet of the jubile]。这天是赎罪日,你们要遍地吹响号角。你们要遵守第五十年为圣年,遍地向所有居民宣告自由。这是你们的禧年[jubile],每个人都要恢复他们的产业,回到他们的家庭。
大家肯定要问这些规定到底有没有可能严格遵守。[7] 且不考虑实行情况,这些规定背后的观念在基督教时代产生了持久影响。草木枯荣的自然循环向人们昭示了希望,使人们相信生命经过漫长间隔后仍然能够重新焕发。而自然所不曾昭示的,当然是表示年份和天数的数字,在本例中,这些数字是从周循环中取来的。
就其本身而言,用数字来计算时间与轮回时间观是有冲突的。但是要确定计年的时间观自何时开始、又如何成为文化惯例则纯属徒劳。计年惯例的形成可能不是源自对年寿的计算,因为即便到现在,在一些原始部落中仍有许多成员不知道自己多大岁数。当然,有些文明情况不同,他们能够牢记代代先祖,一直追溯到神秘的过去,并心存子孙蕃衍,直到遥远未来的希望——《圣经》为证,我们的文化也被赐予这种希望,它暗示着线性时间观。
在一些发达文明中,统治者和王朝的在位时间为社会提供了更大的时间尺度。这也加强了现在与往昔之间的距离感。古埃及王表一般都在王的名字旁注明该王的在位年数,而希腊化时期的埃及历史学家马内托[Manetho]除了注明在位年数还注明该王所属的朝代数,这一惯例至今依然为埃及学家所遵循。还有一种起源更晚的时间观,它以某个独立事件为元点,从该元点开始计算年数以定义“时代”。佛教徒通过计算他们与佛祖诞生或入灭之间的年数来记年,不同地方和传统的佛教徒得出的结果还互有出入。而对于罗马建城以来到底过了多少年,在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看法。
只要人类之间的时间观不同,划分历史时代的长短不同,庆典就不得不用
“纪念日”来标定,而这些纪念日可在特定社团的公共日历上查到。贺拉斯曾为之创作《世纪颂歌》[
Carmen Saeculare
]的罗马建城百年庆典,以及其他落成庆典[8] 的情况可能就是这样。只有当人们普遍认同以时代作为时间数字的集约框架后,我们称之为周年纪念的可预期的庆典才有可能得到确定。我们已知最早的周年纪念与圣经有关禧年的律令相关,而这竟是由于对希伯来原文的一个翻译错误造成的。上文所引《旧约》中的“欢庆的号角”宣布了这一庆典的诞生。希伯来文把公羊角制成的号角称为“yobel”,这个词被拉丁文译者错误地译为“iubilatio”,于是英语跟着错为“jubilee”[欢庆,禧年,周年纪念]。
1300年,教皇保尼法斯八世[Boniface VIII]宣布了天主教会第一个“欢庆之年”,部分是因为他听说一个世纪前曾经举行过这样的庆典。朝圣者的云集和以后多次举办的“欢庆之年”说明这是一个有利可图、教会认为应当经常举行的庆典。开始这一庆典每隔50年举行一次,后来变成每隔33年举行一次,到了庇护二世[Pius II]时代更发展为每隔25年就举行一次圣年庆典。不过,真正的百年庆典最早似乎是由新教徒举行的,这就是1617年在德国为纪念1517年宗教改革而举行的百年庆典。这场庆典有专为它铸造的钱币为证,其动机可能出于对天主教会的模仿。天主教很快接受了这一形式,1640年,耶稣会出版了一部印着徽章的豪华书籍《耶稣会百年像集》[
Imago Primi saeculi Societatis Jesu
]以庆祝该教团成立一百周年。所有这些例子都证明,最初的周年庆典都与特定的社团生活相联系。人们要纪念的是其自身的历史,因此我们见到15世纪佛罗伦萨为但丁诞辰(大约)200周年举行了庆典。对于曾将但丁放逐的佛罗伦萨人来说,公开赋予他们这位伟大诗人以荣耀是极为重要的。佛罗伦萨人于1465年决定委托多米尼科·米开里诺[Domenico Michelino]绘制一幅但丁肖像,以取代大教堂原先的一幅画,这幅但丁像直到今天还挂在那里。[9]
以世纪为单位计算时间的办法越来越流行,这似乎要归因于学校采用的历史教学法。到1700年,用世纪来记年的办法已被普遍采用了,[10] 从此百年庆典大量出现于史料之中。1706年,奥德的法兰克富大学[University of Frankfurt an
der Oder]庆祝了学校的百年华诞,普鲁士国王亲临祝贺。[11] 而据我所知最早为哲学家举行的百年庆典,是莱比锡大学[Leipzig University]为纪念莱布尼茨[Leibnitz]百年诞辰于1746年举行的。庆典上约翰·克里斯蒂安·歌特谢德[Johann Christian
Gottsched]用拉丁文发表了纪念演说。1728年,人们为了纪念艺术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在戈斯拉[Goslar]出版了一部纪念集,出版时间“恰在他于200年前辞世之时”。这庆典后来发展成节日游行,迄今不衰。
令人惊奇的是,首次特地以“jubilee”[禧年纪念]为名的大规模庆祝活动并没有在整数年举行。我指的是1769年规模盛大的“莎士比亚禧年纪念”,它是由演员大卫·加里克[David Garrick]在斯特拉福德[Stratford-upon-Avon]发起组织的。这类禧年庆典当时就染上了许多不那么健康的特点,吵吵嚷嚷,趣味低俗,商业气息浓厚。正像我刚才说的,这场庆典的举办时间是随机的,禧年大庆的主意最早是在为莎士比亚树碑立像时产生的,为报偿加里克,斯特拉福德授予他自由行事的权利。韩德尔[Handel]可能是第一位人们为其百年诞辰举办庆典的作曲家,这场庆典于1785年在英国举行,为他举办庆典十分自然,因为他创作的乐曲在他身后仍在到处演奏。[12]
按照《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在现代意义上使用“百年纪念”[centenary]这个词最早是在1788年,当时用这个词来纪念“1688年光荣革命”。英国人的纪念活动得到了民族意识日益觉醒的意大利和德国的回应,后两者也通过举办庆典来增强民族精神。1820年,柏林美术学院[Academy of Arts in Berlin]为纪念拉斐尔举行了一场公开的世俗庆典,于时德国人首次决定要按照不低于拉斐尔的规格来举办纪念丢勒逝世的庆典,到1828年,纪念丢勒逝世的周年庆典已发展成为纪念德国浪漫主义的民族欢庆。不过,即使这样盛大的庆典在场面上也敌不过1859年为纪念伟大的席勒而举行的百年庆典,这场庆典激发了举国上下的爱国主义热情。
不用说,统治者家族也利用他们的世袭权利,通过举办家族庆典和纪念活动来加强附庸对他们的依附关系。[13] 我母亲生于1873年,她到老都记得1879年在维也纳为庆祝皇帝和皇后银婚而举行的盛大游行,游行是由画家马卡特[Makart]导演的。同样,1887年举行的维多利亚女王禧年庆典也仍然保留在英国人的记忆中。小说家罗伯特·穆斯尔[Robert Musil] 在其《没有品质的男人》[
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
]中展现了优秀的讽刺天赋,小说围绕着一场王朝庆典的徒劳组织而展开,假想了1918年“和平皇帝”弗朗兹·约瑟夫[Franz Joseph]遇刺70周年庆典,其举办用意是要掩盖于同年举行的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遇刺30周年庆典。
从那以后,庆典的发展情况我看就勿需赘述了。如今,新年年历保证我们不会错过来年的周年纪念活动。[14] 出版商,展览商,影视制片商——还不用说旅游产业——无不得益于这些年历,借助它们来组织活动。我最近收到一份来自伦敦波兰文化研究所[Polish Cultural Institute]的邀请,邀请我参观纪念波兰首张电影海报问世百年展。在周年纪念活动快速膨胀的背后显然有社会经济因素,但是肯定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导致它的不断增长。在我们这个步履迅速的技术进步时代,往昔太容易被遗忘了,过去我们用纪念碑来防止这种危险的趋势,但是它现在的效果并不是很好。当我们步行或是驾车路过名人雕像时,甚至不会注意到纪念碑上镌刻有文字,遑论阅读它们了。纪念宗教奇迹和事件的圣地处境稍好,还能吸引成批的朝圣者,但从世俗的角度看,所有这些都是旅游“景点”。游客喜欢听人告诉他们,某所房子、某个地方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名人离去时的样子——这毋宁是说,时间从那以后一直静止不动。对于具有同样诉求的人们来说,惟有周年纪念能够给予他们那种确定感,确信业绩和事件就像贺拉斯曾经热切希望的那样能够不朽。周年纪念属于那些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根在过去的文明和“普遍文化”,因此,周年纪念与庆典仪式不同,它并不否认时间的线性流动,相反,它使我们意识到当前庆典与那被纪念的、不能丢失的往昔之间的距离,尽管卡西尔已经逝世一百年,他的哲学却依然与我们同在。所以我想以一句英文格言作为发言的结束——这句格言机警地混合了轮回与线性两种时间观,简直无法翻译——“Many happy returns of the day”[今日快乐多重回]。
[1]
歌德[Goethe]《浮士德》[
Faust
](悲剧第一部,舞台序幕),P. 韦恩[P. Wayne]英译,伦敦[London],1949年,第34页。
[2]
本文最初是向1974年庆祝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提交的发言稿。后来又应狄特尔·
亨里希
[Dieter Henrich]之约收入文集中出版,以感谢他在纪念卡西尔百年诞辰庆典上替我宣读德语原稿,也感谢他在我于斯图加特[Stuttgart]领取黑格尔奖[Hegel prize]时为我作介绍。参阅〈时间、数字与符号:纪念日的历史〉[Zeit, Zahl und Zeichen: Zur Geschichte des Gedenktage],载M. 斯塔姆[M. Stamm]编《综合意图中的哲学》[
Philosophie in
synthetischer Absicht
],斯图加特,1998年,第583—597页。
[3]
例如,可以参阅弗兰克·E. 马努埃尔[Frank E. Manuel]《哲学史的形状》[
Shapes of Philosophical History
],斯坦弗[Stanford],1965年。
[4]
参阅阿兰·布朗[Alan Brown]编《世界宗教节日》[
Festivals in World
Religions
]中收录的文献,本特米尔[Burnt Mill]、哈劳[Harlow]、埃塞克斯[Essex],1985年。
[5]
该诗的德语释义见H·贝特格[H. Bethge]《中国的笛子》[
Die chinesische Flöte
],莱比锡[Leipzig],1920年,第39页。
[6]
见解采自墨尔西亚·埃利亚德[Mircea
Eliade]《永恒回归的神话》[
Le
Mythe de l’éternel retour
],巴黎[Paris],1949年。
[7]
这些规定的实行情况可参阅B. Z. 瓦考尔德[B. Z. Wacholder]〈第二庙期与早期长老时期之间的安息年循环历〉[The Calendar of Sabbatical Cycles During the Second Temple and the
Early Rabbinic Period],载《希伯来联合学院年报》[
Hebrew Union College Annual
](辛辛那提[Cincinnati]),XLIV,1973年,第153—196页。
[8]
参阅M. 伯恩哈特[M. Bernhardt]《罗马钱币学手册》[
Handbuch zur römischen Münzkunde
],哈勒[Halle],1926年,第75—76页以下。
[9]
图片和进一步信息可参阅C. 马尔齐西奥[C. Marchisio]《鲜花圣母玛利亚教堂中的但丁纪念像》[
Monumento pittorico a Dante in Santa Maria del Fiore
],罗马[Rome],1956年。
[10]
J. 布克哈特[J. Burckhardt]《现代百年庆典的发生史:源起与进程:从弗拉西乌斯到兰克的历史编纂学》[
Die Entstehung der modernen
Jahrhundertrechnung. Ursprung und Ausbildung einer historiographischen Technik
von Flaccius bis Ranke
],戈平根[Göppingen],1971年。还可参阅A. 威茨西-本茨[A. Witschi-Benz]给R. 兰德法斯特[R. Landfester]《历史乃人生之导师》[
Historia magistra vitae
]一书及J. 布克哈特《现代百年庆典的发生史……》一书所转写的书评,载《历史与理论》[
History and Theory
],XIII,no.2,1974年,第181—189页。
[11]
H. H. 芒克[H. H. Monk]《理查德·本特利博士生平》[
The Life of Richard Benteley, D. D.
],伦敦[London],1833年,第191页。
[12]
伯尔内博士[Dr Burney]《论音乐演奏……纪念韩德尔》[
An Account of the Musical
Performances…in Commemoration of Handel
],1785年。
[13]
参阅E. 布里克斯[E. Brix]和H. 斯代克尔[H.
Steckl]《围绕纪念的战斗:欧洲中世纪的公共纪念活动》[
Der Kampf um das Gedächtnis. Öffentliche Gedenktage in Mitteleuropa
],维也纳[Vienna],1997年。
[14]
例如,克鲁兹林根[Kreuzlingen]的戴克[Deike]出版公司承诺,公司出品的下一年年鉴将包含总数超过1600个诞辰、逝世及其他纪念日。
(
插
图
为
维
特
鲁
威
美
术
史
小
组
下
载
自
网
络
,
并非原文插图
)
 为
了
方
便
读
者
查
阅
所
有
文
章
,
本
公
众
号
已
将
所
有
文
章
归
类
放
在
菜
单
栏
往
期
推
荐
里
面
了
哦
,
欢
迎
关
注
查
阅
。
为
了
方
便
读
者
查
阅
所
有
文
章
,
本
公
众
号
已
将
所
有
文
章
归
类
放
在
菜
单
栏
往
期
推
荐
里
面
了
哦
,
欢
迎
关
注
查
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