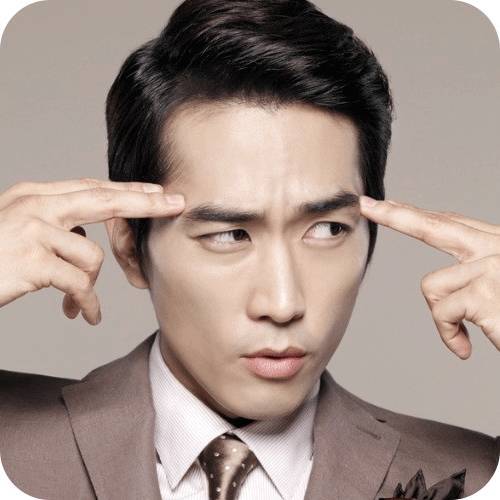睡前聊一会儿,梦中有世界。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进入蛇年的第一个爆款,毫无疑问属于人工智能。这股可以“深度思考”的“东方神秘力量”,席卷的可不仅是科技界。相信有不少人已经上手,经过短暂的错愕、震撼与兴奋之后,更多人开始冷静思考。比如,一个相对浅显的问题,当文本生成如此轻而易举,那么我们还需要学习语文吗?进而言之,一个更加深邃的命题,人类引以为傲的文明演进,是否会就此发生偏离?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对一名文字工作者来说,人工智能的出现可谓喜忧参半。
喜上眉梢的是,那些不知道躲在互联网什么角落的素材案例,终于有“人”能把它们一网打尽了;那些明明就在嘴边但始终说不出来的“漂亮话”,难得有了打工人的“嘴替”,“会说你就多说点”。甚至,还能享受一把“这版不行,打回重写”的“甲方爽感”。反之忧心忡忡的是,“吾与临安狄公,孰能?”
在精致到几乎“完美”的文本面前,曾经熬过的夜、秃然的发,所有的煞费苦心仿佛刹那间失去了意义。乃至更现实的考虑,我,会不会被取代?

AI作诗引起网友讨论。
图源:上观
复杂而矛盾的情绪,正在蔓延更多行业里的更多人。相信你也一定惊诧于社交平台上流传甚广的“AI名篇”。给它一个诗眼,还你“整个大唐”;输入一个名字,传记信手拈来……恍惚间,“文章千古事”不再需要殚精竭虑,“七步成诗”“一字之师”的隐喻被技术革命渐渐瓦解。
人们有理由相信,26个字母、3000多常用汉字,文学不过是文字的排列组合,“无穷匮也”只是人类的极限而非机器的天花板。
难道说,我们已经抵达了文字的尽头?
显然,由此断言“人文理想的黄昏”,有些为时尚早。
单就文本而言,也有人给出评价:工整有余,意境不足,难免“平庸”。只不过,这究竟是人类的自我挽尊,还是机器的力所不逮,恐怕见仁见智。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那些文坛巨擘、艺术大咖穷其一生所追求的精神世界,能不能被“拟态”?文学艺术的情感载荷与价值标准,是谁来赋予,又是谁在接收?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再精致的“生成”,也少了点多巴胺的激昂、荷尔蒙的丰盈,自不必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韵”。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本质,是数据的消纳、转化与重塑。
所谓“展示人类所有认知能力的系统”,仍然依赖投喂与养成。可以说,这是其命门所在。比如,“吃”不到关键数据,自然也就束手无策;再比如,“吃”下不完整的、有偏颇的数据,就会产出“言之凿凿”的谬误。有人就在其生成的自传中,被伪造了籍贯,虚构了经历,笑谈“这哪里是我”。同样,对数据的调用也是一门学问。一样的疑惑,得到的却是五花八门的答案。
难怪有人说,DeepSeek的出现不仅没有削弱语言的作用,反而加剧了语文的“参差”,因为“人与人的差距不在于能回答什么问题,而是能提出什么问题”。
或许,更重要的讨论在于,身处技术革命的前夜,我们应该葆有一种怎样的心态。
技术是一种力量,每一次突破都会带来一个新的“可能世界”。此前,我们在基因编辑婴儿事件里,反思过“科学万能”的伦理挑战,发展进程中尤要提防“愚者的傲慢”;如今,面对类似蒸汽机代替人力、铁路取代马路、计算机超越算盘的“时代奇点”,也理应拒绝另一种意义上“弱者的胆怯”,去直面,去接纳,去超越。
科学技术的魅力正在于此,翅膀轻轻扇动,影响悄然发生,改变人类行为方式,重塑社会文明形态。对此,无须惊慌,也不必示弱。放眼整个人类文明长河,潮起潮落,一浪接一浪。
最后,我问了它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