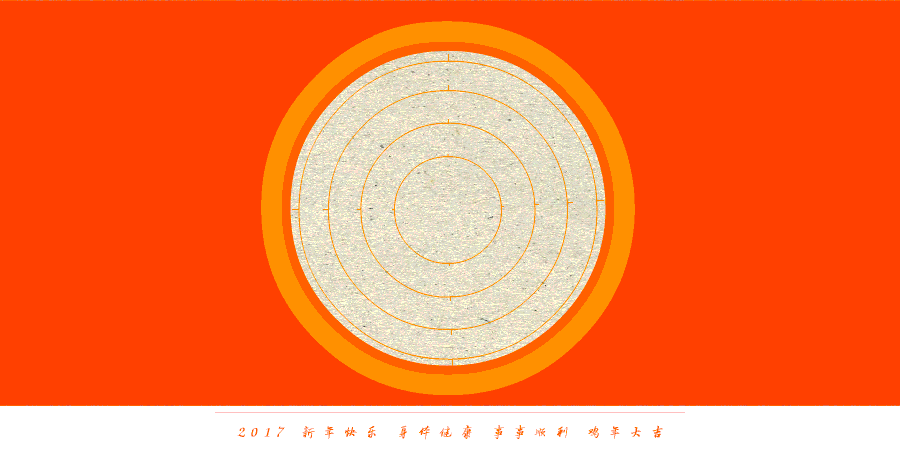
>>>> ⼀
我的故乡叫河口镇,位于北江、西江和绥江的汇聚处三水,这是一个有着四百多年历史的⼩镇。我的祖父母在这里度过了一生,我的父亲在这⾥出⽣后来到了省城求学谋生落脚,我出生后被送回这里由祖父⺟隔代抚养到⼋岁然后回到广州。

祖屋位于一条铺着⻘石板的⼩街中间,楼⾼两层,⻘砖⽩瓦,红梁高悬,和两旁低矮的房屋相⽐犹如鹤⽴鸡群。这⾥还住着三叔公和一些叔伯婶⺟,毗邻⽽居,鸡⽝之声相闻,⽅便便照应。这真的是⼀条充满着温情的⼩街,一条总是萦绕在我脑海久久不去的小街!
祖⽗是家乡⼀个普通的水务公司技⼯,祖⺟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她自从嫁给我祖父后就一直在家⾥操持家务。两⼈一起⽣养了六个儿子,还盖起了全街最漂亮的楼房。每每想到这⾥,我既佩服祖⽗母赚钱持家的能⼒,也对那个年月的物价⼼生景仰!

祖⽗母膝下的六个儿⼦除了大⼉子在家乡⼯作⽣活、五儿⼦因病早夭外,其余的⼉子星散各地
祖⽗母膝下的六个儿⼦除了大⼉子在家乡⼯作⽣活、五儿⼦因病早夭外,其余的⼉子星散各地,平时就是两个⽼人家日夜厮守,平淡度⽇。记忆中祖屋最热闹的就是每年的春节,各房⼈马都如约回乡,即使远在外省的四叔也携雏挈眷长途跋涉⽽回,并笑称⼀年的积蓄都是留着进贡给铁道部了。

二房大合照:记忆中祖屋最热闹的时候就是每年的春节,各房人马都如约回乡,即使远在外省的四叔也携雏挈眷长途跋涉而回,并笑称一年的积蓄都是留着进贡给铁道部了。
这时候叔伯婶⺟有些忙着宰鸡杀鸭煎炆炒炖,准备烹调出⼀顿美味丰盛的年夜饭来;有些忙着铺床叠被,安排着各房晚上的睡觉事宜。我们十多个小孩就忙着翻找祖⺟早就炸好的拿手年货——油角煎堆,⼀边吃⼀边追逐,欢声笑语满屋充盈。其时两个⽼人家眼⾥洋溢着⼉孙满堂承欢膝前的自豪和幸福!
⼤约年初三的时候,各房⼈马带着浓浓的亲情陆续散去,⼀切⼜静寂下来了,只留下门前鲜红的⼀地炮竹⾐,祖⽗母那平淡的⽣活⼜波澜不惊地继续下去了。
>>>> 二
我是⼤约在⼀周岁的时候被⽗母送回家乡由祖⽗母抚养,⼀直生活到八岁才回⼴州。
我的童年就是在故乡度过的,那段岁⽉距今已经差不多有五⼗年了,许多事情都慢慢模糊记不起来了,但慈爱的祖⽗母总会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想到他们⽢苦与共相伴⼀生,心底⾥就会不由自主地泛起⼀股温暖和钦慕!
祖⽗个⼦不⾼,身材精瘦,头发花⽩,目光炯炯,给⼈一种十分精神利索的感觉。他身体很好,每天早上都骑着⾃行⻋去河⼝饮茶买菜;再后来年纪⼤了就改为⾛路了,但那肩托⼀袋⼤米健步如⻜回家的身影,于今仍然令我震撼不已!
祖⽗每天晚上都要坐在⼆楼的⼩木桌前,在昏⻩的灯光下记帐,收⼊来⾃哪⾥,⽀出⽤在何处,结余数是多少,⼀笔⼀笔记得清清爽爽。那时我年纪还⼩,不知道记录家常⽤度的作用。祖⽗就告诉我:家庭开⽀要有计划;还有就是勤笔免思,写下来才容易记住,不然光靠脑⼦是记不住多少的。
祖⽗特别喜欢吃鱼,⼏乎天天他都会买⻥回来,多数是清蒸来吃,他说这样才鲜美。他还喜欢每顿饭都喝一小杯白酒,可能是广东⽶酒之类,也就是⼀两左右的样⼦,极其规律。他说这样⾏气活血,对身体有好处。他后来活到九十三岁,很好地印证了酒如适量可养⽣!
祖⺟长着⼀副圆盘⼤脸,⼀看就是慈眉善⽬和蔼可亲的样⼦。她⻓得很胖,⼀个大肚腩再加上⼀双⼩脚,⾛起路来缓慢⽽淡定。她还怕热,夏天的时候⼿里总是拿着⼀把大葵扇,轻轻地摇着,⼀如她的性格淡如和风。她⾔语不多,看着⼈的时候总是笑眯眯的,这时额上就会露出⼏条浅的皱纹来。

祖⺟十分爱⼲净,每天头上都梳着⼀丝不苟的发髻,屋⾥的⼀切都收拾得井井有条;祖⺟做饭的时候总是叫上我,耐⼼地教我怎样⽣火、烧⽕和收火,熊熊的柴⽕煮好了饭菜也映红了她的脸庞;祖⺟很喜欢拉一张竹椅坐在⻔口纳凉,⼿摇大葵扇看着我和⼩伙伴在街上跑来跑去,有时街坊行过,也会停下来和她聊上⼏句。
>>>> 三
我是在家乡读了两年书才回⼴州的,我仍然记得那⼩学叫红城⼩学,离祖屋很近的,不用⼗分钟就能⾛到。实在是年月久远了,那时候的班主任是谁,我的成绩怎样以及有没有⼥同学喜欢这些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学时才六岁多⼀些,学校本来是不打算收我的,后来是身在教育战线的⼤伯娘去了学校⼀趟,这书才读成了。
我还记得学校里有⼀个小的⾜球场,天天放学我都很喜欢在那踢球,足球的萌芽不知是不是在那时就开始种下,以致这项运动让我热爱了⼀生。有⼀次我踢了⼀个很⾼很⾼的球,砸碎了课室的一块玻璃,幸好没有伤到⼈,最终⼜是⼤伯娘去学校赔钱了事。
上学的路上会经过⼀口水井,那是当时这条街的居⺠的⻝用⽔源。井是⼀口⽅形⽔井,井台四周都是⽤条⽯砌成的台阶,时间⻓了⾛的⼈多了,井台都已经被磨得特别光滑。挑⽔是所有家庭每天不可或缺的节目,祖⽗年纪⼤了,挑⽔都是⼤伯⼤伯娘的事,后来到堂姐⼤了,就接过了那担水桶。
堂姐稚嫩的双肩挑着⼀担⽔晃晃悠悠的身影,现在我仍然能够记起。因为那时我很喜欢跟着去看她挑水,在井边看着她往井⾥放下⽔桶然后轻轻⼀晃荡,水就满了,十分熟练。后来我也试着挑⽔,总觉得那担⽔很重,压得肩膀酸痛,我就用脖⼦来担,⾛起来姿势很怪,⽔桶也摇晃得厉害,回到家时往往只剩下⼀半多。
上⼭打柴也是我童年时经常参与的⼀个节目,也是堂姐带上我去的。⼤人们⼀般都要求我们成群结队地去,并叮嘱我们千万不要⾛散,以防麻风佬祸害⼥孩子。麻⻛佬其实是当时的⼀个隐晦的说法,就是指躲在⼭上专等着奸淫猥亵落了单的⼥孩的那些坏⼈。那时我听到这些,都不由自主地握紧拳头挺起胸膛,⼼里充满着保护堂姐们的欲望。
我们打柴主要就是拗枯枝扫树叶,剥竹壳拢竹叶,⼀切能烧⽕做饭的柴草都是我们的目标。堂姐⼀般都带着我们⾛很远的路才来到⼭上,⼭上有⼀些⾼低的坟堆⼗分吓人,但柴草真的很多,可能是路远,来的⼈少的缘故。很快我就打满了一箩,我玩⼀下又帮堂姐拢⼀下,然后黄昏时我们就乘着夕阳满载而归了。
>>>> 四
八岁的时候我极其不情愿地离开了故乡回到⼴州⽣活,可能是父亲觉得祖⽗母年纪⼤了,⾃己的⼩孩⾃己抚育了。我已经记不起当时有没有哭闹着不肯走,⽗亲有没有答应我寒暑⼆假都让我回来故乡住,但有⼀点我可以肯定,我一定是舍不得与慈祥的祖⽗母分开的。
回到⼴州我花了很⻓的时间才适应大城市特有的⾃来⽔的漂⽩剂⽓味和汽⻋飞驰⽽过的噪⾳,当然还有我的⽗母和妹妹这个新的家庭环境,但我仍然牵挂着故乡的祖⽗母,牵挂着故乡的⽣活,那时候哪⾥懂得⼈生就是不断的分别和不断的重逢啊!
每个学期⼀考完试放假,我迫不及待问⽗亲拿上路费⽣活费就直奔⽕车站,想着很快就可以⻅到慈爱的祖⽗母、管得没有⽗母那样严的叔伯婶⺟还有堂兄弟姐妹和⼀大街的⼩伙伴,想着那熟悉的⼤街、地堂、⽥基、山岗、⻥塘和⽔井等又可以留下了我们顽⽪的身影和欢乐的笑声了,我奔向⽕车站的脚步就显得那么急促⽽有⼒!
那时候回乡我们最喜欢坐⽕车,就在⽯围塘⽕车站坐广三线,⼏毛钱就到河口。要是赶上春节,绿⽪客⻋都被抽去⽀援春运,我们就只能搭一种叫“牛卡”的⽕车回乡。“牛卡”是平时用来运载耕⽜的⻋厢,既没有座位,又充斥着浓郁的⽜粪味,十分难受。好在行车时间并不算长,铺张报纸一屁股坐下去,忍一忍也就到了。
放完假了,又要回⼴州上课了。那时每次从故乡回来,我都⼗分难受。我在挂历上找到下一个假期的起始⽇做上标记,然后每过一天就交叉一天,就这样⼀天⼀天地等待着下⼀次回乡的⽇子。记得有一个假期,⽗亲不知是⼿紧还是不想我回去,总是不给回乡的生活费,我一急拿上⼏毛钱就去坐⽕车了,父亲没办法,过了几天就顺路将生活费送到祖⽗手⾥了。
就这样一直到参加工作了,我才结束了寒暑⼆假回乡度假的生活,但每年的春节、清明祭祖都是我法定的回乡日。这个习惯⼀直延续到祖⽗母相继去世、亲戚朋友陆续迁去⻄南居住才慢慢改变,而今⼀般就是清明才回河⼝祖屋缅怀⼀番,这时候总不免有一种物是⼈非沧海桑田的感觉溢上⼼头。
>>>> 五
⼀生中我第⼀次直⾯死亡就是祖⺟的去世,那时我⼤约⼗三四岁,祖母突然病发。病来如山倒!当我们闻讯后赶回家乡时,祖母由于急病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我看到她静静地躺在祖屋前厅,旁边跪了一屋⼦的人,嚎啕⼤哭声、啜泣声和哽咽声此起彼伏,满眼都是白⾐白帽⽩腰带白晃晃的⼀片。我想起将我一⼿带⼤的慈祥的祖⺟就要下葬了,不禁悲从中来,扶棺痛哭,久不愿意撒⼿。
一眨眼祖母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了,祖⺟留在我脑海的点点滴滴依然十分清晰。我每次⾏清时回到祖屋,我都要走进她的房间,在她的梳妆台前站⼀下,想象着祖⺟每天在这里整理出⼀丝不苟的发髻;我又会在厨房的灶头前蹲一下,回忆着祖母教我们烧柴⽕时的情景;我还会拿⼀把⽵椅在⻔前坐⼀下,望着寂静的街道思考着为何没有了疯跑的小孩,百感交集难以言说!
祖⽗在祖母去世后,仍然顽强地独自⽣活了⼗五年。随着岁月的流逝他慢慢地变得衰老起来,也比以前更加沉默寡⾔了,很多时候看见他读完大伯捎回来的《参考消息》后,经常会陷⼊沉思,我想他可能在回味报纸的内容,但更多的,是在想念相濡以沫的祖母。但有一条祖⽗始终没有改变,就是每天晚上临睡前都不会忘记拿着⼿电筒去检查⼀下所有的门窗。
有⼀年的春节,大伯和他的⼏个兄弟商量,让我和⼀个堂弟带祖⽗到中山的⼆伯家小住,希望换⼀下环境以减哀思,那是我第⼀次和祖⽗出远门。我们搭乘堂姐夫⽗亲的运货便船顺利来到了中山,⼆伯带着我们游览了翠亨村、中山公园和逸仙湖等。在烟墩⼭上,二伯指着⼀条蜿蜒的⼭路教会了我“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涯苦作舟”,晚风中到处飘扬着我们祖孙众⼈快乐的笑声。
祖父过了八十五岁后,⼤伯和他的兄弟们决定不能让祖父⼀个⼈独居了,他们商量后决定让祖父在五家人轮流居住,这也不失为⼀个公平的权宜之计。祖父来到我父亲家里住的时候,其时我已搬离家多年了。我⼀下班就回去陪祖父,带他去喝茶、在小区花园晒太阳和聊天,希望能尽量让他有家的感觉。
又过了几年,祖父不知道是意识到了什么,他⽼是要求结束这东漂西流的生活,强烈要求回河口祖屋居住,我⽗亲告诉我,祖父是感到了死亡的临近,他是想土葬,葬在祖⺟旁边。就这样,祖⽗在九十岁的时候⼜回到了祖屋,这次就不是独居了,大伯他们在街道里雇了⼀个五六⼗岁的⽼头来照顾祖父的起居饮食。
到最后那年,家乡不时传来祖⽗病重的消息,令⼈十分牵挂。有一天⻩昏,我挈妇将雏赶回河口看望他。看他形容枯槁垂暮衰老的样⼦,我完全理解了风烛残年的含义。不过他仍然能认出我们,他拉着重孙⼥的手微笑着,我轻地擦去了他浑浊眼角的眼眵。如今每看到那次拍下的照片,我仍然是痛心的不能自持。
在祖⽗弥留的时候,我很想陪伴在他的身边,让他在离去的时候能感到丝丝温暖。我约了两个堂弟回去住了几晚,其时祖父已经坐不起来了,就躺在祖屋前厅的⼀张竹床上;也吃不进东西,只是喝一些粥水,嘴唇⼗分⼲裂。深宵夜静,他没有睡着总是叫痛,声声悲嚎于今言犹在耳。祖⽗终于在我回⼴州⼏天后离世,其顽强的生命⼒令我最终没能送他上路,于我实为⼈生⼀大憾事!
>>>> 六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故乡现在⼀般是每年清明回去一次,墓园祭扫后又回到祖屋给先人遗像上香,然后我⼜会到街上逛⼀逛,不过已经很难碰到熟⼈了,⻘石板的街道和静谧的院落处透露出⽼街的落寞。水井填了,家家都⽤上⾃来⽔了;红城⼩学拆了,重新盖起了崭新的楼房。
路过三叔公的故居时,我想起了我们在这里帮勤快的三叔婆粘贴火柴盒,还曾经拿了她的⽕柴盒写上筒索万学会了打麻将;街口的地堂被四周的房屋⽇渐包围,只剩下了一块细⼩的空地,我想起我带着⼀街的⼩孩在这⾥踢⾜球的欢乐;近公路的那个⻥塘还在,只是那塘水浑浊得难以形容,我差点不敢想起曾经在这⾥抱着⼀棵砍来的蕉树和小伙伴戏水。
极目远望,我看⻅了魁岗⽂塔有如⼀支如椽巨笔倒插于北江之畔,擎天⽟立。⽂塔始建于四百多年前,其间屡经劫难,多次修葺。这座开三⽔文运的古塔⾼九层,琉璃配瓦,檐角挂铃,晚⻛吹过声闻数⾥之外。少时我们经常⾏田基攀⼭岗跋涉⽽来,其时但⻅塔⻔紧闭,塔上百⻦翻飞,我们绕塔有顷,也许就是这样沾了些许文气。
⽇已⻩昏,暮色四合,乡关渐远,何处是岸。站在北江⼤堤上,我想起了多年前和妻子婚前第一次出外就是回家乡看望祖父,饭后我们漫步在落日镕⾦的坝上,温馨情景仿如昨日;我眺望着滚滚江水百舸争流,想到⼈生匆匆数⼗年转瞬即逝,荣华富贵终也是⻩土⼀抔,重要的是活在当下,惜取眼前一切,让⾃己和身边的⼈快乐,⽤心过好每一天,这就是⽣活的意义,看似平凡实是真谛!
这些年每次当我回乡后就要离去的一刹那,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平添⼏分惆怅;⼜或者我每次搭乘夜行列车经过这个⼩城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这⾥曾经的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这时心底就会泛起一股温暖,尤其是我牵肠挂肚的祖⽗母,你们在另⼀个世界⼀切可好?

我隔空告诉祖父母,我真的很想念你们,我从你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我万分的感谢你们!
我隔空告诉祖⽗母,我真的很想念你们,我从你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我万分的感谢你们!诚然,祖⽗母的那个年代⾥物质是相对贫乏一些,⽣活是相对简单一些,但⼈的心地是那么的纯朴善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那么和谐融洽,夫妻之间是那么容易的平淡⻅真情相守过⼀生!⼈生一世,草⽊一秋;⽣不带来,死不带⾛,还会有什么比真情更为难能可贵的呢?
相关阅读:
吾心安处是故乡【归乡记系列 · 2017】
没有故乡的孩子 【归乡记系列 · 2017】
关乎青春、成长与责任的那点事【归乡记系列 · 2017】
我们是归人,但最终是过客【归乡记系列 · 2017】
一座集市的变迁,一部家乡经济史及背后【归乡记系列 · 2017】
三千里路 两位父子 一缕思绪【归乡记系列 · 2017】
你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归乡记系列 · 2017】
何处是吾乡?新生代农民工的迷思
有爷爷奶奶的地方就是家【归乡记系列 · 2017】
一年中最后的匆忙【归乡记系列 · 2017】

格隆汇声明:格隆汇作为免费、开放、共享的海外投资研究交流平台,并未持有任何关联公司股票。转载本文,请务必注明来源“港股那点事”及作者。
● 扫描下方二维码,下载“格隆汇”APP
● 遨游格隆汇官网(gelonghui.com)
● 添加微服妹妹微信号:guruclub_011
● 关注格隆本人微信公众号:guru-lama
● 商务合作(0755-86332133-823)
● 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