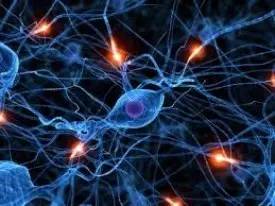1
车拐进州精神病院大门时,莫平夫人说,“你不会觉得你父亲有很大改变的。”
“他穿着病服吗?”安吉拉问道。
“不,亲爱的,当然不会。他是受到特殊照顾的。”
这是安吉拉的第一次探望,而且是她自己提出的。
自从莫平勋爵在一个暮夏的阵雨天被送走后已经有十年了。这是给她带来混乱而辛酸回忆的一天。这是莫平夫人举行每年一次花园舞会的一天,一直使人感到辛酸和混乱。这一天的天气反覆无常,但总象有转晴的希望。可是在第一批客人到达后,突然乌云满天,狂风四起。大家都忙着躲雨。帐篷吹翻了,椅子和椅垫乱晃,桌布刮到了智利松的树枝上,在雨中飘荡。天晴了一会,客人们又小心翼翼地出现在潮湿的草坪上。接着又来了一阵狂风;又是二十分钟的阳光照耀。这是一个天气极坏的下午,直到六点来钟她父亲企图自杀时才告结束。
莫平勋爵经常威吓说要在举行花园舞会时自杀。那一年他果真用他的裤带在桔子园里自尽,被发现时脸已变青。一些在那里躲雨的邻居把他放了下来,晚饭前为他叫来一辆马车。从那时起,莫平夫人就每季度到精神病院来探望一次,并按时回家吃茶点,从不谈及她的感受。
她的很多邻居都想评论莫平勋爵的供应。他当然不是一个普通的住院病人。他住在精神病院单独一侧的病房里,这是专为较富有的精神病人隔开的。这些病房根据他们的病情,有各种不同的设施。他们可以挑选他们自己的服装,因为很多病人沉迷于最强烈的幻想中。他们可以抽最高级的雪茄烟;而且在他们入院的周年纪念日,还可以开私人晚餐会来款待他们所爱慕的其他一些住院病人。
然而,事实上,这的确还不是花费最高的病院。横刻在便条纸上的不协调的地址“州精神病院”也印在看护人员的制服上,甚至还漆在主要入口处最显眼的墙板上,暗示着这是花钱最少的病院。莫平夫人的朋友们常常尽量机智地想让她注意海滨疗养院的特点:那里有“好的大夫和大片私人场地适合于治疗精神病或疑难症”,但是她都没有采纳。等她儿子长大后,他一定会根据他认为合适的再作改变。她倒不是为了要减轻她的经济开支,而是因为她的丈夫在那一年的那一天,当她期望得到忠实支持时卑劣地背叛了她,这已经远远超过了他应得的报偿。
有几个穿着大外套的孤单的人影在花园里懒散地闲逛。
“那些是较低级的精神病人,”莫平夫人看见后说,“这儿还有一个非常雅致的小花园,专供你父亲那样的人享用。去年我还送了他们一些花木插枝。”
他们驱车过了一垛黄色的空心砖墙,来到医生的私人入口处。医生把他们引进了为了探望时用的设在旁边的“会客室”。这儿的窗户在里面用木条和铁丝网防护着;没有火炉。安吉拉胆怯地想把她的椅子从散热器处移远一点,但发觉它是用螺丝拧紧在地板上的。
“莫平勋爵马上就会来看你们的。”医生说。
“他好吗?”
“喔,很好,我可以高兴地说他的确很好。前不久他得了一点讨厌的感冒,但除此而外,他的身体很好。他花了他的很多时间在写作。”
他们听见一阵慢吞吞的跳蹦声沿着铺者石板的过道而来。门外边,传来一阵恼怒的高喊声,安吉拉听出是她父亲在说:“我告诉你,我没有时间。让他们就回去。”
一个较温和的稍微带点乡下口音的声调回答说,“现在来吧,这是一次纯礼节性的接见,你愿意呆多久就呆多久。”
门没有锁和闩,一推就推开了,莫平勋爵走进了房间。陪伴他的是一个身材矮小的老人,满头白发,态度和蔼可亲。
“那是勒弗戴先生,莫平勋爵的看护人员。”
“秘书。”莫平勋爵说。他步伐迟缓,和他妻子握了握手。
“她是安吉拉,您还记得安吉拉吗?”
“不,我不能说我记得。她想干什么?”
“我们是来看您的。”
“唷,你们来得极不是时候。我非常忙。勒弗戴,你已经打好给蒲柏的那封信了吗?”
“还没有,勋爵。您记得吗,您不是要我先查查纽芬兰渔业公司的数字吗?”
“是的。唷,这倒好,我正想把这封信重新起草。午餐后已经出现了很多新的消息。很多很多……,你看,亲爱的,我忙极了。”他把他的一双疲惫而滑稽的眼睛注视着安吉拉。“我想你大概从多瑙河来。唷,你以后一定要来。告诉他们这里很好,一切都好,但是我没有时间把我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这上面。告诉他们这一点。”
“好的,爸爸。”
“无论如何,”莫平勋爵颇性急地说,“这是次要的事。首先要处理的是易北河、亚马孙河和底格里斯河,对吗,勒弗戴?……多瑙河其实是一条又脏又小的河,我自己只能称它为一条小溪。唷,说得没完了,你来得可好。如果我有空,我一定会给你谈得更多,但是你看我多忙呀。把它写出来给我,把他用墨水写在纸上吧。”
说完这些他就离开了房间。
“你们瞧,”医生说,“他身体很好。他增加了体重,饮食和睡眠都很好。他全身都没有什么毛病。”
房门又开了,勒弗戴回来了。
“先生,请原谅我又回来了,我只怕这位年轻的小姐会因为勋爵不认识她而感到烦恼。您不要介意他,小姐。下一次他一定会非常乐意来见您的。今天他只是因为耽误了他的工作而感到烦恼。先生,您是知道的,这个星期我都在图书馆帮他查资料,没能把勋爵所有的报告都打出来。他又把他的卡片索引弄乱了。就是为了这些原因。他没有一点恶意。”
勒弗戴回去照顾病人后,安吉拉说:“一个多好的人呀!”
“是的,我不知道如果没有老勒弗戴我们会怎么办。每个人都喜欢他,工作人员和病人都一样。”
“我一直记着他。我为您能得到这样好的监护人员而感到极大的愉快,”莫平夫人说,“不知道的人就专爱谈论精神病院这样一些无聊的事情。”
“喔,勒弗戴可不是一个监护人员。”医生回答说。
“你是不是说他也是一个疯子?”安吉拉问道。
医生纠正了她。
“他是一个住院病人。这是一个颇有趣的病症。他已经在这里呆了三十五年了。”
“但是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比他神志更清醒的人。”安吉拉说。
“他确实是那样,”医生说,“在后来的二十年里我们就这样对待他的。他是这儿的中心人物。当然他不是一个有钱的病人,而我们准许他自由地和他们来往。他台球打得极好,能在游艺会上玩魔术,能修理他们的留声机,侍侯他们,帮他们解纵横字谜,并满足他们的各种不同的嗜好。我们准许他们给他少许消费作为报酬,他现在肯定已经积聚了不少钱财。即使是最麻烦的病人他也能对付。他是这里的一个无价之宝。”
“哦,但是他为什么会到这里来的?”
“唷,很遗憾。在他还是一个年轻人时,他杀了一个人,一个他素不相识的年轻女人。他砸了她的自行车,并且掐死了她。事后他自己立刻投了案,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呆在这里。”
“那么肯定他现在完全可靠的了,为什么不让他出去?”
“唷,我想这是每个人都感兴趣的,他可以出去。他除了一个住在普利茅斯的异父母姊姊外,没有别的亲属。她有一个时期经常来看他,但现在已经有几年没来了。他在这里过得非常愉快。我可以肯定告诉你,我们不会首先提出来让他出去的,他对我们实在太有用了。”
“可这好象不是太好。”安吉拉说。
“就说你父亲吧,”医生说,“如果没有勒弗戴来当他的秘书,他就完全受不了。”
“这总好象不是太好。”
2
安吉拉离开了精神病院,心中压抑着一股愤愤不平的感觉。她的母亲却冷漠无情。
“打算把一个人一辈子都关在精神病院里。”
“他想在桔子园里上吊,”莫平夫人回答说。“而且是在切斯特—马丁家门前。”
“我说的不是爸爸,我是说勒弗戴先生。”
“我想不起来我认识他。”
“哦,他们要他照顾爸爸的那个病人。”
“你父亲的秘书。我想,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而且很适合于他的工作。”
安吉拉暂时丢下了这个问题,但是第二天午餐时又提起了它。
“妈妈,要让人离开精神病院应该做些什么事?”
“精神病院?天哪!孩子,我希望你不要指望你父亲再回到这里来。”
“不,不是,是勒弗戴先生。”
“安吉拉,你简直把我完全弄糊涂了。我想昨天我带你去的那次短暂的探视是错误的。”
午饭后,安吉拉躲进图书馆,立刻埋头查看百科全书里写的精神病法。
她不再跟她母亲谈论这个话题。但两星期后,当提到要为她父亲入院十一年聚餐会送去一些野鸡时,她异乎寻常地表示乐意把它们送去。她母亲忙着别的一些感兴趣的事,没顾得怀疑什么。
安吉拉开了她的小汽车来到精神病院,交完野味后,就去找勒弗戴先生。这时他正忙着在为他的一位时刻想当巴西神权皇帝的伙伴做了一顶王冠,但他丢下了他的工作,高兴地和她谈了几分钟话。他们谈到她父亲的健康和精神状况。过了一会,安吉拉提醒说,“你从来没有想到要出去吗?”
勒弗戴先生用他温和的蓝灰色眼睛看着她。“我已经非常习惯这里的生活,小姐。我喜欢这儿的可怜的人,我想他们之中好些人也是非常喜欢我的。如果我要走,我想他们就会感到失去了我。”
“那么你从来也没有想再获得自由?”
“喔,是的,小姐,我想过,几乎一直我都在想。”
“如果你出去了你预备干什么?有些事情是你还在这里时就应该决定的。”
老人有点踌躇不安。“唷,小姐,听起来很不愉快,但是我不能否认,我希望有一个短短的外出机会,好在我太老以前来享受它。我想我们都有我们秘密的欲望,有一件事情是我经常希望我能做到的。你不要问我那是什么事……那不要很长时间。我以为如果我来做它,只要一天,甚至一个下午,那么我就死也安心了。我就能更安心地安定居下来,用一颗更好的心把我自己奉献给这里可怜的精神错乱的人。是的,我以为是这样的。”
那天下午安吉拉开车离开时她的眼里含满了泪。“他一定会有一次短暂外出机会的,祝福他!”她说。
3
从那一天起,有好几个星期安吉拉有了一个新的生活目的。她来来回回地干着她的家务事,但是心不在焉,既生疏又谨慎殷勤,使得莫平夫人大大为难。
“我相信这孩子是在恋爱了。我但求不是那个粗野的爱格伯特森男孩。”
她在图书馆里读了很多东西,并反复盘问每个有法律专长或有医院知识的客人,她对他们的议员老罗德里克·莱恩—福斯考特爵士表示特殊的好感。现在,“精神病医生”或“律师”或“政府官员”的名字对她这个以前围着电影演员和职业摔跤家转的人着了魔。她是一个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女人,在狩猎季节结束以前她终于胜利了。勒弗戴先生获得了她的自由。
精神病院的医生有点不大愿意,但没有坚决反对。罗德里克爵士给精神病院院部写了信,必要的文件都签了字,勒弗戴先生离开精神病院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在这里他度过了多么长久和可贵的岁月呀!
为他的离开还举行了一个仪式。安吉拉和罗德里克·莱恩—福斯考特爵士跟医生们一起坐在体育馆的看台上。在他们下面,病院里凡是认为能很安定地忍受这次刺激的人都参加了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