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一直想成为那种酷的姑娘,可小时候的行为总是跟这个词不搭界。
那时候成绩一直在年级前几名,从一年级开始做班长做到高三,就像传说中「别人家的孩子」,小马尾一甩一甩,腰板挺得巨直,也从不热衷打扮,写完作业就把书包一扔,钻进书房看书,通读了西方名著。
绝对适合出演社会主义接班人宣传片的女主角。
但那时候藏着逆反心理,觉得根正苗红的小姑娘一点都不酷
,考试考第一越是被表扬越是羞愧,有天午间休息带着全班唱歌大闹,被罚站写检讨,觉得自己酷得要命,有古时候带领一方百姓起义的霸气,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思想慢慢就跑偏了,每天想着怎么让自己酷起来。
酷的人应该都会打游戏。于是初一开始接触了一款网游,叫
QQ
自由幻想,开始没日没夜地玩,把好几个号打到当时六十级满级。每天做完功课,跟我妈谎称看书,钻进书房锁上门开始厮杀,打到凌晨,眯着眼睛扑到床上去。
后来账号竟然被盗,也没有了重新开疆拓土的勇气,突然元气尽失。
随后小镇风靡了「非主流」和「杀马特」,初三时大家也开始分化,有人过得越来越符合主流价值观,有人越来越肆无忌惮。学校里慢慢也有了一群痞人大哥,我放学后脱了校服偶尔也跟他们玩,喝啤酒,谈恋爱,他们叫我「玮哥」。

老师拿我没办法,毕竟我学习成绩依然好,每个月还在各种杂志上发表小作文儿。
那时候天真,觉得这样的生活才叫酷,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一部分凛冽如风,一部分暖煦如光。
后面不知怎么玩大了,那天我在外地,一个姐们儿打电话告诉我,我一个大哥为了替我出气,放学后把我前男友围堵痛骂了一通,没想到前男友马上找了一群人,真刀真枪地把我大哥堵在小酒馆,准备直接干起来。
还好没人受伤,不过周一升旗大家都耷拉着脑袋挨了大处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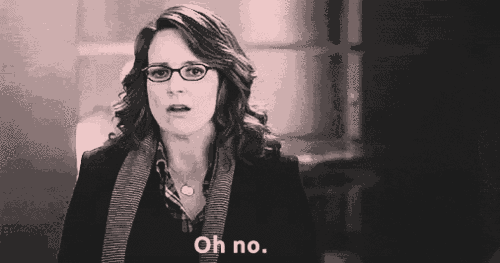
我依然疯狂迷恋这种反差感。
不想做惨淡的白开水,让人瞬间读懂,要做就做那种藏在大铁壶里的烈酒,神秘,炽烈。
大一有段时间很喜欢化浓妆。坐上出租车,司机懒洋洋问我在哪工作,我一本正经地说在复旦上学,司机惊掉了下巴,说「就你这样还是学霸」,我非但不生气,反而一阵暗爽。
跟一堆朋友混,在小酒吧吸着她们的二手烟,听她们一边喝酒一边吐脏话,觉得晚上跟她们厮混在一起,白天去学校学《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跟教授讨论马克斯韦伯,这种割裂的生活才是酷。

我在两种世界里颠倒,自以为乐此不疲,但最后生活应了那句歌词所说,我特么不是真正的快乐啊。
经历越来越多事,我发现我做不成藏在铁壶的烈酒,我就是个寡淡的白开水姑娘。
而且我发现,我喜欢真心交往的姑娘,都是些白开水女孩。我享受的交往方式,就是普普通通,找个敞亮的餐厅或者书店,跟她们聊聊走心的话,没有那些耍宝和搞怪。
我也不喜欢那么妖艳的口红色,不喜欢身上戴太多首饰,我青睐的就只有基本款。
我有时候甚至连有趣都谈不上。跟人聊天时从不会冷不丁天马行空冒出几句话,只是规规矩矩,该抒情抒情,该一本正经聊生意就聊生意,该尴尬还是要尴尬。我骨子里就是个向往节制生活的普通青年,不爱热闹,不怎么经常社交,每天十几个小时用来读书写作。

有几个读者吐槽说,我公众号下面那张头像太「网红脸」了,说没想到一个这么锥子脸的姑娘,是写这样文字的,太反差了。
在此之前,我听到这些话还挺得意的,有种人不可貌相的快感。但慢慢发现,我明明生活中不是那种「网红」形象,干嘛为了制造反差感来给自己那样的定位呢。
前几天有个老朋友来上海,在小酒馆门口,他递给我一支烟,并娴熟地想给我点上,我摆摆手承认说,我真的不会抽。他惊诧极了。他说,我一直觉得你很酷啊,没想到你不会抽烟。
我心里笑,不会抽烟就不酷了嘛。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那些有两副面孔的人很酷。
我有个朋友白天在学校做历史学老师,晚上在小酒馆驻唱。
还有人白天在工地做工头,晚上写小说。从前我迫切想成为那样的人,但慢慢地,我终于可以云淡风轻地摇摇头,对全世界说,我就是个单调的姑娘。
承认这一点也没什么大不了。
我突然开始迷恋那些纯粹又简单的姑娘。她们虽然没有神秘的纹身,没有割裂的身份,不是那种穿得稀奇古怪或者思想不断挑战常规价值观的人。
但或许,一个认认真真做自己的人,也一样可以很酷。
你觉得呢。
GoodNight
长 按 二 维 码 关 注
▼
据说,全宇宙最酷的人,都点了
阅读原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