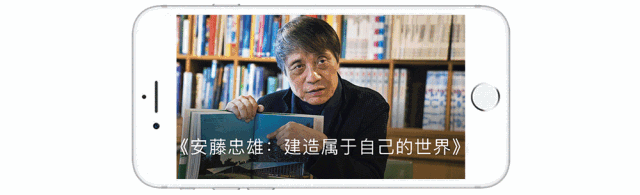过年在家,每天陪父母走亲访友,
还没来得及好好处理这一年所经受的压力和委屈,假期就结束了。
新的一年新的开始,可整个人并没有轻松起来。
带着来不及疏解的情绪回到工作的城市,
人们都拥在里面,动弹不得。情绪被吞没掉了,大多数时间你隐隐地感觉不高兴,没意思,可是要做些什么呢,不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也许
哭出来就好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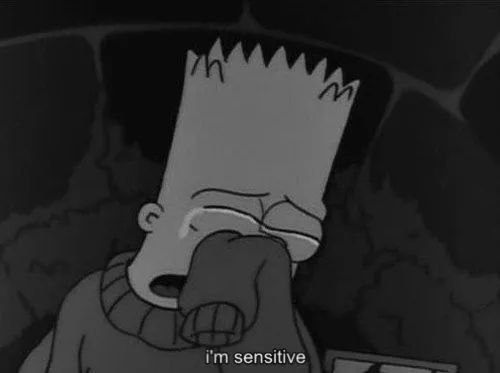
九年前,自传体小说《东京塔》揭开了“哭泣小说”风行的序幕。随着它被改编成电视剧、电影、漫画,各类“哭泣作品”在日本大行其道。
继而,“哭泣有利排毒”“眼泪消解压力”的各种论述,也纷纷出炉。于是每到周末,或买或租一些催泪的小说、DVD,在家里边看边流泪,成为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女性中的一种时髦,“周末号哭” “哭泣文学”形成了日本社会独特的文化现象。
“用痛哭清除内心毒素”
日本一家周刊对800名20岁至50岁读者进行调查,结果有70%以上的人在最近一年中有过痛哭的经历,其中,约四成人哭泣的直接原因,是那些催人泪下的文艺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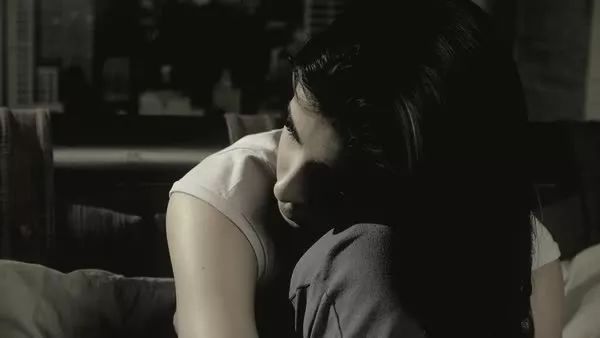
日本社会以生活节奏快、生存竞争激烈著称,各种心理辅导手册、压力舒缓指南盛行不衰。心理学专业出身的安原宏美指出:
只有人类才有发自内心的哭泣
。科学证明,无论出于什么感情而哭,都能减
轻精神上的压力,尤其在痛苦难过之时,大哭一场有助消除体内郁结的负面情绪。之后,随着《号泣力——卸下心灵的包袱》《脑部压力消除法》等类似图书相继出版,“周末号泣”的减压方式风行一时,其拥趸们深信,痛哭流泪能清除内心的“毒素”。

要强调“周末”,是因为流泪减压要求全身心投入。对于含蓄内敛的日本人来说,周末有着更多的独处空间,可以放松平时在大庭广众下紧绷的神经,任泪水恣意流淌。

随着周末号泣的流行,大量“号泣”类作品应运而生,不但书店专门辟出“哭泣小说”专架,各类有关哭泣文学、电影的推荐榜单也屡见不鲜,还诞生了不少专事推荐此类作品的网站,就连美容界也瞅准“哭泣文化”蕴含的商机,相继推出“可哭的眼影”“可哭的眼线笔”,确保女性在哭泣时也能保持端庄美丽。
“
悲伤是人活着的真理
”
诗人谷川俊太郎曾说:“
日本人往往把悲伤作为一种美⋯⋯悲伤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人活着的真理。
”从“物语”文学到“身边小说”“私小说”,都能轻易发现感伤催泪的作品,以致如今出现
“哭泣小说”
这一独特品类。
亲情是催泪的王道,
《东京塔》
是此类代表。

电影《东京塔》剧照
小说中的“我”从懵懂少年长大成人,日子过得糊里糊涂,远在家乡的母亲却始终鼓励、包容。当“我”终于浪子回头,成家立业,母亲却已病危垂死。

“老妈就像橡皮擦,越擦越小/
小时候,是你牵着我的手,走过大街小巷/ 现在,就让我牵着你的手,走完最后一段路⋯⋯”

山田太一的《遇见异人的夏天》中,主人公是一位刚刚与妻子离婚的失意编剧,在倍感落寞的盛夏时节回到家乡浅草,意外遇见一对异常亲切的中年夫妇,像极了自己30年前因车祸不幸离世的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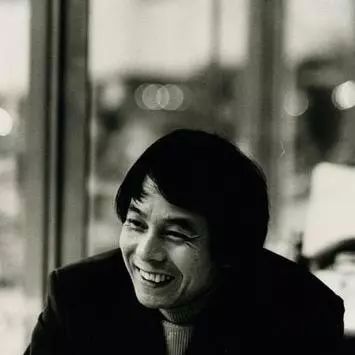
作者:山田太一
和这对夫妇相处的时光里,他重新感受到久违的家庭温馨。然而最终发现,那对夫妇正是在他思念召唤下重返人间与他相聚的亡父亡母。在必然的分别来临之时,他只能眼看着悲伤的双亲逐渐变得透明,消失在空气中。

与此类似的是东野圭吾的
《秘密》
:一场车祸夺走了妻子的身体与女儿的灵魂,妻子的灵魂附在了女儿身上。

电影《秘密》剧照,改编自东野圭吾同名小说
看似不幸中的大幸,却令这个家庭陷入更深的痛苦。
丈夫从此不得不面对一位以女儿形貌存在的“妻子”。他深深爱着妻子,眼前却是一天天成长的女儿,既无法和“女儿”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又无法弃“妻子”不顾,另娶他人。而作为“妻子”,今后都将以女儿的身份生活,却无法无视丈夫的感受,坦然与别人恋爱、结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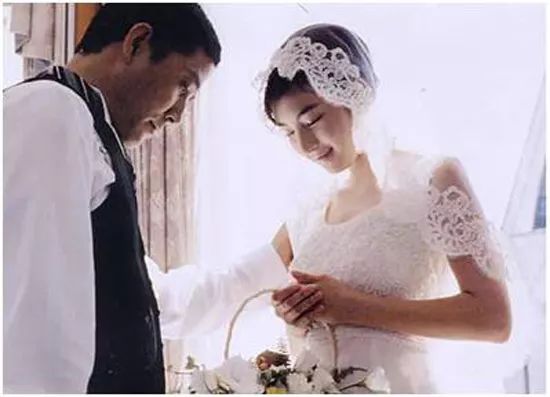
看似不可思议的题材,稍一走偏就会踏入伦理的禁区。东野圭吾细腻、微妙的叙事能力为整个故事赋予了更深刻的人性内涵。

在《秘密》里,“爱”从花前月下的甜柔升华成为对平淡生活的渴求,表面的荒诞并未指向单纯的猎奇,而是回归了真挚的夫妇之情与亲子之爱。难怪有人说,这是部男人看了也会流泪的小说。
“对逝的迷恋是对生的珍重”
偏好樱花之美的日本人,对“逝”有着一种特殊的迷恋。


师从寺山修司的汤本香树实,在小说
《夏日的庭院》
中借“死亡”描述了对生命的感悟。
故事从三个男孩的视角说来,小学最后一年的暑假,升学压力、家庭矛盾、身心改变等诸多问题在潮湿闷热的季节中发酵,每个人都困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找不到出口。一次葬礼后,三人决定偷窥一位独居的怪老头,观察死亡是什么样子。

电影《夏日的庭院》
男孩与那个孤僻的老人由相互试探的陌生人变成朋友,又逐渐对彼此生出依恋之情。男孩从老人身上学会了很多生活技巧,老人也慢慢走出孤单的阴影,变得开朗起来。夏天过去,老人离世,三个曾经迷茫的少年,面对各自未知的未来。

日本文艺对死亡的关注,恰恰总能转化为对生命的珍重——“
这个世界或许有许多隐藏着的、肉眼无法看见的东西。其中有的像彩虹那样,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看到;而有的却要在漫长而艰辛的旅途的尽头才能找到它。现在也许有什么东西隐藏在什么地方,静静地等待着去被发现。
”村上春树写道。

“那些恍如静止般的美好时光”
“纯爱”
也是哭泣小说的习见题材。
《野菊之墓》中,作者伊藤左千夫道出了此类作品的精髓:“
青涩岁月的纯爱,就像山谷中遍地的野菊,也许是一生仅见过一次的美景——稍纵即逝,却能令人回味绵长。
”

电影《野菊之墓》
所以,纯爱类的哭泣小说,很大部分是描写少男少女的青涩恋爱,比如畅销一时的《在世界中心呼唤爱》《恋空》以及被赞誉为“日本爱情小说圣经”的《天使之卵》。诗意的青春,纯纯的爱,伴随着生离死别的煽情,总能成功赚人热泪。
但在哭泣文学中,“死亡”并非“纯爱”的归宿,死亡的存在是为了证明“爱”的纯洁与恒久。并且,为了保持爱情的纯粹与洁净感,通常侧重于表现精神性的爱恋。

电视剧《恋人啊》
野泽尚在《恋人啊》中描写的海枯石烂的精神之恋,已然成为“纯爱”迷心目中的经典。书中男女主角最亲密的接触,是他吻过她的小指尖。即使有无数次越轨的机会,两人每每止步于欲望的陷阱前,“欲望”让位于“只想爱着对方”的柔情,所以“心中燃烧的火焰,到最后仍然是炽热的”。
对于多情善感的读者而言,这种
遗世独立、永无止息的爱就是心底最温柔的叹息
。
日本的哭泣小说文字多是素淡轻柔,没有曲折激烈的情节,靠素雅感伤之美感染读者。
虽然时常有“患绝症离世”之类令人厌烦的桥段,但若恰逢你身心疲惫、心变得粗糙坚硬之时,它们能促你“感极而泣”,在心中升起对爱、生命、时间、死亡的省思,则不失为让心灵恢复柔软与敏锐的途径之一。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所有权原作者所有
文/小茕
你有多久没好好地哭一次了?
都是为什么而哭呢?
留言分享你的故事吧。
▼
点击观看“重逢岛”原创视频
▼
点击“阅读原文”
直达微店预购
《安藤忠雄:建造属于自己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