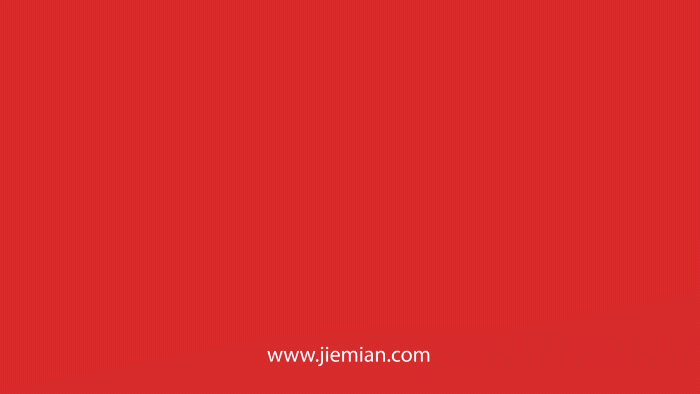![]()
今年夏天,我们认识了一个年轻的作者孙中伦。他生于1994年,目前就读于美国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攻读PPE (政治、经济、哲学)及德语双专业。他选择休学一年,回到中国,在各地漫游。有时停留在一个工厂,有时去一座寺庙,以作家和记者的方式观察中国。今天发表的,是他春节期间去苏州一座寺庙的经历。
1
春节以后,我去了紫泉寺,做一个居士。
紫泉寺很小。找到它,我颇费力气。去的路上,我在一百米外的小超市门口迷了路。超市老板把花生壳丢在地上,用苏州土话回应我,“什么?这里还有一个寺庙?”后来,一个度假酒店边上,我发现一个小木头牌子,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紫泉古寺”。而再向前走五十米,一座两层的寺庙出现在一堆砾石上。它废弃的外墙上,还印着平安银行的广告。“半夜三点找我贷!7x24小时可放款。”聪明的漆工把背景涂成橙红,胜过寺庙的土黄。
我在平安银行的大字下碰见性悟法师。性悟师父是紫泉寺里唯一常驻的师父。一位居士先前告诉我,性悟师父是佛学院毕业的,科班出身,佛法的问题都精通。因此我想象他步履蹒跚,讲经时也许需要眼镜。然而现实中他矮小又瘦削,嗓音尖刻,远看像饥饿的一休,使我误以为他是某个师兄。“我就是这里的性悟师父。”他告诉我,随后双手合十行了礼。他招呼我把东西放下,随他去楼上诵经。
来寺庙,我早就想好的,即使我对佛学一窍不通——我对它的全部理解,来自于黑塞几本主题重复的小说,和外婆时不时去山上排队求得的红丝带。或许是后殖民主义的影响,我对佛教少许多对基督教的敬畏,这样,也就更有勇气去探索它世俗化的结果。“我要去一个小庙。”我开头便想好了这个故事。“若文学要求我,我甚至愿意扮演魔鬼。”春节以后,我终于踏上旅程。我既不虔诚,也很无知。我不指望能解脱。
在二楼的诵经房里,一群黑衣妇女已等候多时。她们通通上了年纪,其中一个,甚至完全伛偻了,她在房间里张罗,像一把行走的手枪。“那老人八十多岁,”后来,一个女人告诉我,“现在就住在庙里了,烧饭。”在性悟法师坐定之前,女人们互相之间碎言碎语,而其中唯一的一个黑衣男人则站在她们中央,大声地说着什么让每个人都开心的事情。随着师父敲响木鱼,所有人都坐上自己的位置——
今天诵的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和《佛说阿弥陀经》。师父的诵经声一开始还依稀可辨,后面就整个沉没在妇人们的声音中。妇人们虽然大都来自四周的村庄,诵经却一点不粗糙,口音里苏州女子的娇气,甚至盖过了经文里的禅味。她们越唱越起劲,后来,倒像是女人在河边洗衣服时唱的山歌了,泡沫漂浮在小溪中央。我跟不上,滥竽充数。读到“断疑生信”的时候,我第一次心虚。
这是我第一次读《金刚经》。在充满困惑的同时,罕见地受到触动。这触动无关宗教,是文学上的。奇妙之处在于,诵经节奏由缓入急,情绪却是逐渐冷却,而到最后诵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的时候,情绪忽的高涨,随之彻底崩溃——多美的人世,多残忍,多短暂!我久久沉溺在这个句子里,以致读到《佛说阿弥陀经》中对极乐世界的描写,竟心生嫌弃。“尽是些金碧辉煌,”我心里抱怨,“俗不可耐的审美,我倒宁愿活在尘世的玻璃渣子里。”
诵经的最后,是读功德簿的环节,给寺庙捐钱的都有功德。女人们从位子上站起来,聚到师父对面。师父读到哪人的名字,有关的女人就跪下磕头。有的女人关心的人多,要跪拜好几次。我站得腿麻,心里寻思着,要是哪位路德精简掉诵经的环节,而只留阅读功德簿和磕头,一定颇受欢迎。然而我看到妇人们幸福的双眼,想起刚刚念到的“断疑生信”,又不禁愧怍。我真的愿意扮演魔鬼吗?这可由得我选择?
念完经以后,家里还有差事的女人们都回家了,庙里一下冷清许多。屋檐下站着一位新和尚,看上去年纪比性悟师父还要大不少。我诵经时没看到他。那时他正来回踱步,似乎有些不安,过路人也不理他。“您也是这里的吗?”我上前问他,用了敬辞,仿佛自己心也诚了。“嗯,我新来的。”他告诉我,仍低着头,“我法名叫释常国。”
我们在寺庙外面的砾石地上散步,天色渐晚。释常国告诉我,他五十岁,已经出家十多年了,刚来这里十几天。对于他的话,我有所保留,因为并没有看到他上楼念经,我怀疑他是来寺庙里蹭吃蹭喝的。他倒不遮遮掩掩,反而字正腔圆地告诉我,他是安徽池州人,父母都已经去世。“父亲活到73,母亲活到84,两个坎。”他认真地看着我,眼睛瞪得很大,“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言下之意是,孔子活到七十三,孟子活到八十四,这是圣人都无法克服的命运。“那你为什么踏入佛门?”我问他。他告诉我,他是最小的儿子,一直随母亲生活。到了三十多岁,也没了成家的意愿。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城里的房子被拆迁。他没有要拆迁房,而是拿了钱,去乡下买了一套房子。“不应该不要房子。”他感叹,“不过,就像这小寺庙一样,都是因缘……因缘让我在乡下的房里修行。”母亲第二年在乡下的房里病逝了,从此他一个人生活。“很辛苦。每个月就领四百元。到了年末,亲戚会给一点。”他拉下脸,摇摇头。之后的日子他并未多说,直接跳到了来紫泉寺的部分。“来苏州是慕名而来,我那边的师父介绍。呆多久说不准,要看缘分了。”他说,“人,世上所有事物都在不断变化,所以有六道轮回啊!只有佛心是不变的。”他又瞪大眼睛,认真地看着我,给我讲起道理来。“饮苦食毒。我们吃的喝的都是有毒的。”我不明白他为何突然转变话题,“这是大自然的业报。”我似是而非地点头。“你学什么专业?”他忽然问我。“政治。”我随便一说。“那以后回来要做公务员的咯。”他寻求我的肯定答复。我回避他的较真目光,点点头。我们一起踢着脚边的石子。
远处,性悟师父正和村妇们聊天。脱掉黑衣的男人在一旁劈柴,他的嗓门大又沙哑。“这批木头,很难劈!”他把斧头举过头顶,“唉!”的一下劈下去。村妇们正坐着,往篮子里剥青豆。一个女人说,“我老公家的弟弟没有家庭。”性悟师父说,“那我帮他申请困难户。”女人说,“他不是要钱,而是想要一个孩子。”
晚饭是三道素材,驼背的老妇人把菜端上桌面。“小伙子,多吃点。”她一遍一遍嘱咐我。饭桌上性悟师父告诉我,他是湖北黄梅人。“我听说你懂很多!”我的奉承让自己觉得恶心。“惭愧。”师父说。“我听居士说,你来是要写东西。”我心一颤。“我给你出个题目,孝道。论孝道。”
饭后我一个人去了旁边的度假酒店散步,路上我寻思着师父的题目,心中冷笑,“孝道和佛教有什么关系呢?”我妄想自己接过他的考卷,就写上“梦幻泡影”四字。我想象他气愤的样子,他枯瘦的脸拧成一团。而我则脱下外衣,变成魔鬼的模样。我拉长的脖子绑住他的身体。“亚伯拉罕在山顶决意祭祀他的儿子,”我在他的耳后低语,“你又会怎样做呢,我可爱的阿辽沙?”
我被这孝道问题搅得心神不宁。“哼,这破庙里的和尚,能懂什么……”我正欲脱口而出,却发觉自己迷失在路上。眼前的度假酒店,黑灯瞎火,许多楼都废弃了,游泳池里空无一物。我意识到,自己站在一片无人的废墟上。我继续向前走,发现一片竹林。道路幽幽,我凭着莫名的信念往山上走去,却步入一个死角。一股黄昏气息扑面而来。我感到害怕。
2
四点醒来,天仍黑着,有鸡鸣。
今天是拜山的日子。每个周日,性悟师父都会去灵岩山脚下,三步一拜,拜上山顶。传说灵岩山是印光法师圆寂的地方,净宗道场。所以周围寺庙里,大大小小的和尚都会来拜山,以示虔诚。“有的时候,我们身后会跟一长串的人,”性悟师父说,“有的时候,刮风下雪,只有我和护持。”在紫泉寺的六年里,性悟师父已经拜了三百次山,从未间断。今天,是第三百零一次。“再过一些日子,我们就要向九华山朝拜。九华山是地藏菩萨的道场。”师父说,“要带上帐篷,走两个月。”
床边,我点了盏灯看书。一会儿,听见大厅里师父开始念经了。过了不知多少时间,他在门外喊我的名字,吃早饭。
“每天早晨都念经吗?”饭桌前,我问师父。“不一定。”师父说,“小寺庙,规矩没那么多。去年的时候,还总是吵架呢。”“吵架?”“捐钱呗……”他不愿再说下去。“我听说,你上过佛学院。”我找来其他话题。“是啊。三十多岁才去的。之前,也就在外面干活。”师父说, “三十多岁上了灵岩山。在班上,我是差学生,总考不及格。”“学佛也有考试?”“有的。”
师父告诉我,那年,本来有一百人报考,录五十人,他是第六十一名,但由于他一直在灵岩山做义工,得了优惠,最终勉强过了线。进入佛学院一个月以后,五十个学生都受了戒,从沙门僧变成了比丘僧,戒律也从十条多到了二百五十条。“就比如吃饭,”师父给我演示,“双手不能靠在桌上,而得矜持地夹紧肩部才行。包括走路,坐姿,都是有要求的,学院里希望我们成为有气质的僧人。”
“可就算进入了五十人的名单,也不见得就保险了。”师父皱紧眉头,他的严肃让我不自在。 “那年的第一名,就是中途被开除的。”“开除?为什么?”“牵手了。”师父小声说。“什么?”“他在寺庙里和人牵手了。”
六年前师父从灵岩山毕业。“我们其实很好找去处,”他说,“大和尚会来找小和尚,只有来我们这里。”而对于为什么来紫泉寺这座小庙,他的解释是,“当时,这里的护持上灵岩山来找我,我也只想去个安静的地方。”紫泉寺离灵岩山不远。从那以后,每个周日,不论风吹雨打,他总是会去灵岩山拜山。有的时候人山人海,有的时候,身边只有护持老钱。
老钱,一个忠实的伙伴,总是奋力地劈柴,在黑衣女人中说些让所有人欢喜的话。每逢开口,他必然扯着大嗓门,情绪是纯粹的,从不说带言外之意的句子。当老妇人把早餐端上桌时,他“哎哟喂”一声拍案而起。“桂圆粥!”他咕噜咕噜一饮而尽。吃完,又去忙着修灯泡和串佛珠了。“他的虔诚是物理性的。”我想,“他成不了有气质的僧人,但每个人都希望有他这样的护持,像堂吉诃德身边的桑丘。”吃完早饭,老钱开着小电驴捎我去灵岩山脚下。他告诉我,他今年四十三岁,女儿在北京读空乘。“皈依佛门多久了?”我问他。“真正的,四五年了!但其实,小时候就有因缘。四五年前开始,只要有空就来庙里帮忙。”去年六月老钱辞了职,成了庙里新的护持,大大小小的事情,全由他操办。“我们每周日都来拜山!”老钱在前座大声告诉我,风打在他脸上,声音像分叉的流水。“拜山对你有什么意义?”我问他。“傲慢消除了!”他不假思索,“拜山的时候,对每个行人都是抬头看的。我觉得学佛,首先要学会做人。”
今天天气不错,山脚下面,拜山的队伍里来了十多人。除了我和另一个男人,其他都是女人。有个年轻的女孩在后面大声说,“我,我上大学就信了的!这是第一次来这里拜山。” “这么年轻就来抱佛门,会有很大的福报的。”另一个女人喜笑颜开,“我第一次拜山的时候都快瘫倒了,很狼狈。但第二次开始就好了。自从来拜了山,我腰和颈椎上的毛病都好啦。这是佛光加持的结果。”性悟师父在最前面,吩咐我也站到前面去。“为什么女人都站在后面?”我问师父。“在佛教里面,男性是要更高一点。”师父认真回答我。我身边的男人笑笑,他看起来面目善良,“中国传统呗,男尊女卑。”“在印度也是这样。”师父又补充说,“就比方说,我们比丘僧有二百五十条戒律,而比丘尼有三百四十八条。”我身边的男人又笑了,他笑起来总是低着头,我应该与他一起庆祝吗?
开始拜山了。老钱在一边,一手拿着女人们给他托管的包和袋子,一手拿着大喇叭。“阿弥陀——”他叫着口令,我们走三步——“佛!”我们拜一下。上山的台阶很脏,我磕头的时候总小心翼翼,免得额头亲上谁吐的痰液、丢的垃圾。抬头的时候,前面的路人都在拍照,他们端着苹果手机,嘴巴微张着。小孩子从侧路奔上台阶,指着师父喊,“妈妈,看!”我们到哪了?拜山真累。老人背着冰糖葫芦上山。戴墨镜的男人哈哈地笑。我想起释常国和老钱。他们总说因缘。哪有什么因缘。过去正不断被吞噬,逝去的人飘散在空气里,而现在正荒唐地发生。那是谁,一个导游?二十五岁光景,她的小腿好细,裹在牛仔裤里。“从这里可以看到太湖。”她的声音清脆又着急,“但今天雾霾。”我感到膝盖酸疼,我想我可能随时放弃。我将坐在路边,我将看着师父和其他人渐行渐远,我将哀叹自己的生活。为什么他们都若无其事?师父原来那么瘦,我好像都能看到他张合的肋骨。那女人在烧香吗?她嘴里在嘀咕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小声,旁人听不见,菩萨就能听见吗?石阶终至尽头。寺庙柳暗花明。我们到了。
山顶上,一个女人跟师父攀谈,说起师父的师父的母亲往生了。“大年初二的事。”师父说。“往生了?”那妇人笑逐颜开,像听到了什么喜事。“往生了,102岁。”师父说。我好奇,是否对他们来说,死亡是件好事,意味着此世修行终于开花结果。这需要多坚固的信仰——恐惧将爬进任何裂缝。我们围着佛像念南无阿弥陀佛,柱子上写着“在此佛像前朝拜可免去下地狱之苦”。我想,佛教不主张救赎,只有解脱。正如它没有基督的神迹,只有观望。在庙宇的大厅里我们又念起“阿弥陀佛”,我已精疲力尽,脱口而出的刹那,竟念成了“阿门”。
下午照例是诵经。这次,释常国也上楼了。念了几句,性悟师父突然停下来。“常国师父,你的礼仪不对。”他说。“哎,哎。”释常国答应着,像是觉得丢了脸,“各地的风俗不一样。”今天我的书被另一个女人拿走了。没有书,我听不懂,连滥竽充数也不成。我有时看看窗外的白玉兰,有时看看房里的佛像。这佛像粗糙得过分,不过佛本无形,相由心生,也无伤大雅。诵经到后面,一个婆婆站到我身边来,不停戳我,意思是这句该跪下了。但她总戳错,别人跪下了,我俩站起来。
傍晚时候,我又出门与释常国聊天。“我可能再呆一两天就走了,也许去别的寺庙。”我告诉他,“听师父说,明天还要去灵岩山做义工。你去吗?”“随缘。”他说。说完,把手上的念珠给我。“不好,这怎么能收下呢!”我推辞。“收着,收着。”他说。
“这些年,学佛对你有没有什么改变?”我问常国师父。“慈悲心。”他说。我忍不住又扮演起那个可怕的精灵,“金刚经里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既然如此,要慈悲心干嘛呢?”常国师父大惊,连忙后退两步,仿佛我犯了什么大忌,“那可是佛的境界啊,我们凡夫子弟怎么能这么说呢?”“若我们不能理解佛,又怎么能知道自己所理解的慈悲心与佛无异呢?”常国师父瞪大眼睛,一时手足无措。“众生平等啊!”过了许久,他用力地说。
常国师父出生于1966年,原来在池州的工厂里上班,2000年下岗潮,他没能幸免。“你怨恨吗?”我问他。“历史发展,总会有的。一部分人富了,一部分人就牺牲了。站在出家人角度,一切就看得很清了。”他目视前方。常国师父让我想起我在定西见到的人们,在不幸中,他们的愤怒也一并消失。“这样也好,”我安慰自己,“若无力改变命运,至少可以改变命运的观念。”常国师父喜欢讲道理,但不常说佛法,倒是对一些旁门左道的知识颇有涉猎。“我们这里后面是公墓,阴气重。”他告诉我。“有什么影响吗?”“鬼多啊!你看这树叶,都是环境变化的结果。”他告诫我,“要多学《地藏王经》,地藏王轮盘一转,六道就轮回了。这部经把这一世都讲清楚了。《金刚经》讲的是佛的事。”末了,他又问我,“你们在家吃什么……算了……吃什么?……算了,都有因缘。”他欲言又止,“吃脏的东西,是黑血。佛家人吃素,都是健康的,消除业障。”
晚上,我在房里读一本书,《现实即弯路》。性悟师父推门进来,给我送水壶。“你就要走了吗?”他问我。“也许很快就要走了。”我告诉他。他看到我床上摆的书,说,“现实怎么是弯路啊?这句话不对。”我趁机问他,“你怎么理解现实?”他没料到我这样唐突,怔了一下。“佛教里讲贪、嗔、痴……”他滔滔不绝地讲着,见我并无耐心听下去,声音越来越小。我们尴尬地告别。他的答案并非我想要的。我期待一个明白无误的回答:弯路还是直路,真实还是假象——然而性悟师父从未给过我一个不暧昧的说法。我想他未必真切理解现实,然而他是那么虔诚修道——在三百零一次的拜山途中,他可有一个瞬间动摇?夜里,我想象有一个人,在生命尽头发现自己穷极一生所侍奉的,无非是一个伪神。我感到不安,因为他孤单而落寞的背影,让我分不清那是我,还是师父。
![]() 江苏灵岩山景区“灵岩寺”。
江苏灵岩山景区“灵岩寺”。 3
下雨了,今天不去灵岩山。
我们坐在庙里的屋檐下,看雨水打在砾石上。一只老母鸡在胡乱奔跑,它常来庙里啄米吃。
“苏州是不是化工厂很多?”释常国突然开口。“没有吧。”老钱说,“都去苏北,四川那里了。”“应该也有工厂在这里。”释常国瞪大眼睛,我知道,他又要开始引出自己观点了。“这大地上的物种,生灵都在变。都是业报……”
性悟师父不说话。下了雨,他好像也忧郁起来。
“师父,我在书上读到说,出家人会对自己在尘世里的一些事渐渐忘掉,是这样吗?”我问他。雨越来越大,庙口的蜡烛熄了,远处的泥土也模糊起来。“是的。”他说。
释常国也叹了口气,“生活就是一场梦,一场戏。”
“师父,”我又问他,“您来这里,也不只是因为这里安静吧?”
他望向我。“不是的。”他说。
“是因为寺庙小,我接管了,可以把母亲接过来。”
在佛学院的最后一年,他听说母亲生病了。那时尘世的事情已经渐渐模糊,可人们告诉他,母亲在家里的床上大呼小叫,只喊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他的,另一个是二哥。二哥已经去世。人们说,母亲的声音很大。到后来,村上的人路过他家,都避而远之。
他三十多岁出的家。出家的时候,已经想的很明白。之前打工的时候,他自己看佛学的书,早已结下因缘。母亲和姐姐听说了,大惊失色——他成了全村第一个和尚!母亲是大嘴巴,最好闹到全镇都知道。他回家的时候,小孩在村口喊,“和尚!和尚!”
一开始,他不愿纠缠俗事的。他和姐妹们说好,每月他寄回两千块钱,姐妹负责母亲的生活。然而他回家的时候,发现母亲的床边只有一个碗,里面尽是污垢。他明白了——姐妹们从来不洗,只是记起来的时候,往里面倒些吃的,像喂动物。
灵岩山上,紫泉寺的护持上来找和尚。然而小和尚都被大和尚领走了,去了大寺庙。末了,护持找到他。“我是做住持吗?”他问。护持当然欣喜答应——之前,庙里可是连和尚也没有。11年,他来到紫泉寺。年末,他把母亲接来庙里。
母亲仍在病痛里,时常大呼小叫。“叫出来,人会好受些。”他说。母亲也说胡话。有一天,一个弟子买了两桶油,一桶电动车捎来给庙里,另一桶留在车上带回家。母亲看见了,扯着嗓子大喊,“偷庙里油啦!偷庙里油啦!”“别给我添乱了。”他对母亲说。
他想也许是母亲孤独了。人们都听得懂她说话,然而她听不懂苏州话。她觉得所有人都仇视她。她甚至无法确定儿子的情绪——他越发陌生了。她叫他的俗名。“在这里,你要叫我师父。”他说。“哦。”她敷衍塞责,“师父、师父。”她开始放弃抵抗,总在厅堂里独自转悠。到后来,她似乎是更信佛了。人们说,她时常去庙里跪拜。她为谁祈福呢?她的女儿不孝,她的儿子要么死去,要么成了陌生人。2014年,她在庙里的房间往生了。那里如今已布满灰尘。没有人再进去,没有人提起她。“她直到往生也没有真正理解我。”师父说,不无遗憾。然而他是否理解母亲?他是否尽了孝?他没有说。你可以看出来,这个本不该存在的问题持续折磨着他,如同锁链般的泡影,滑落不下的露水,消逝不去的闪电。“我给你出个题目,孝道,论孝道。”他对陌生的来者说。两年以后,两天以前。
“三年守孝,我现在是没有机会了。”师父说,“转世只要七七四十九天。下辈子,我们应该无缘做母子。”
“人往生的时候,应该什么时候撒粉?”释常国忽然问。
“尸体凉了以后。”师父说。“那样不会已经灵魂出窍了吗?我觉得,应该在闭眼的那个刹那,就撒粉。”释常国争辩道。师父被搅得烦了,说,“这些都是仪式,主要还是看自己。”
常国回忆起自己母亲往生时的景象。“她不叫,不喊痛苦。”他说。母亲生命里最后几年,只有他陪在身边。他有个姐姐,“也孝顺,但是她丈夫不孝。现在她离婚了。对,她可以找到更好的。她的儿子已经养了小娃娃。”
2000年,他们的房子被拆迁了。他没有要拆迁房,而是拿了钱。“是个错误。”他又感慨。他和母亲去了乡下。她走的那天,他睡在她身边。她要起来上厕所,没有叫醒他。下床的时候,她倒在地上。他惊醒过来。母亲说,“没事。”他扶着她去上厕所,再扶着她回来,帮她盖好被子。母亲又说,“没事。”他再醒来的时候,母亲已经驾鹤西归。
“她进棺材的时候,那个神态,都好得很。我想,她一定是有大福报的。”
常国说,葬礼的前一天晚上,他被托梦了。佛祖告诉他,葬礼上不要哭。到了葬礼上,他的姐姐哭得昏了过去,成了全村有名的孝女。他没有哭,虽然只有他陪着母亲过了最后的十多年。
“人们总说世上没有绝对的善恶。其实在佛教里,善恶分得很清楚。在事情上,要不它就是善的,要不它就是恶。”性悟师父说。如今他终于变得果断了,那么,对于母亲的不诚和他的冷漠,他如何判断善恶?他会去琢磨吗?我想象一扇无边的黑门后,一位老态龙钟的长者把唾沫点在手指上,翻动簿子。“你做了一辈子的善事,”他谨慎地得出结论,随即眼神向上,露出狡黠的笑,“可你没有尽孝。”
其余人都走开了,就留下师父和我坐在屋里,我们仍看着雨水落下,像观看一场不知道何时会戛然而止的戏。“你就要去其它寺庙了。那里,应该没有人和你说这么多。”师父对我说。“可能是吧?”我回应他。“你知道我们刚才为什么要和你说这么多吗?”“闲聊?”“闲聊不会说这么多。我和你说这些,是有目的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一下心虚了。“精神上的,还是世俗上的?”我小心地问,说完便觉得自己愚蠢。“我图你什么吗?你身上,并没有我需要的。”师父说,“你刚刚的回答,或是说明你没有敞开心扉,或是说明你没有主见。这样,别人不会与你交心而谈。”
那天下午,我落荒而逃。在逃跑之前,我最后一次随师父上楼念经。这天是元宵节,有许多新来的妇人,她们只在特别的节日前来为家人祈福,仿佛宗教和人情一样,只要时不时笼络一下,就有关键时刻的效用。读《金刚经》的时候,我心神不宁。身边的那位妇人跟不上,她眯着眼睛,用手指指着书上的小字,一字一字地念,我们都念到“梦幻泡影”了,她还在“此人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就不能配合一下大家?”我心里的烦恼越积越深,妇人的声音像一颗乌黑的种子在我耳朵里扎根蔓延,“愚不可及,愚不可及!”诵经成了折磨,我任由它鞭挞。
落荒而逃的这个下午,师父和我挥手告别,也没说什么下次再来之类的话。再回头的时候,师父已经不见了,倒是释常国远远地抬头看我。路上,我想象大口大口地吃肉。我最终没有去下个寺庙了,而是去了北京。
又过了些日子,我看到紫泉寺的公众号更新了,师父和老钱踏上了去九华山的拜山之行。我看他在公路上三步一拜,到最后,背都伛偻了。九华山下,他显得摇摇欲坠。那时我已离开北京,又去到其它地方。时常有人问我,还要不要回紫泉寺看看。“不去了。”我说,“不会再去了。”
— — E N D — —
![]()
▽点击“阅读原文” 下载界面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