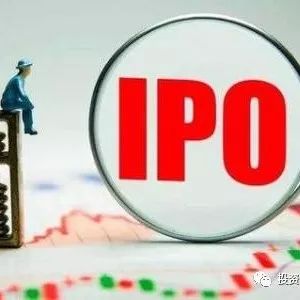“莫负年华” : 恩师傅尚文先生永远的教诲
李金铮
我一直珍藏着一个20世纪80年代的笔记本。本子里的内容有些杂乱,有读书札记,有对学术研究的随想,甚至还有七八页剪报。现在看,这些东西已经没有什么价值,只能当作个人学习历史的一份记录了。我之所以一直珍藏,是因为扉页上有恩师傅尚文先生的一幅题字“春风得意,莫负年华”。落款时间是1986 年6月11日,那是我在河北大学从先生攻读研究生的第二个学期。当时历史系在七教一楼,中国现代史教研室平时空着,我就在那里学习。这天先生来这里与我谈话,说到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问题。我知道,先生这一辈学者大多有厚实的 传统文化根底。我看到过他写的书法作品,于是开玩笑说什么时候能给我写一幅。他看到桌子上我的笔记本,就随手写下了这八个字,说你一定要努力,要超过老师。字为繁体,规矩周正,清丽含蓄,毫无一些所谓书法家的张牙舞爪之状。说实话,我对“春风得意”一点儿感觉也没有,也没有超过老师的奢望,但对“莫负年华”的印象却非常深刻。因为我一入学时,他就给我讲过这个话。我明白, 当时老师的处境不顺,这是老师对弟子的一片苦心和殷殷期望。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奋发努力,不辱师命,光大师门。
我是傅先生招收的第一个研究生,也是河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最早的研究生,为此我常戏称自己是这个专业的大师兄。入学时,正赶上申报硕士学位点, 先生让我整理材料,填写表格。因为历史系高级职称老师不够,为此还联合了经济系的教授。据说在评审时,正是这点成了“问题”。幸运的是,硕士点终获成功。据说是某位著名史学家说了话,说傅先生是中国现代史的开拓者之一,拿个硕士点还不应该吗? 现在看,硕士点已经算不得什么,而在当时却是 “价值连城”。也正因为有了这个硕士点,中国近现代史学科才有后来的发展,才能培养才俊,代有传人,我们真得感谢傅先生! 我知道,有的学科本来实力不错,但因为 硕士点没有申报下来,就由强变弱,乃至瘫痪了。傅先生对我说,你要好好干, 我们以后还要申报博士点。在他的有生之年,没有实现这一愿望的环境和条件, 但他的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也成为我 “莫负年华”的一个动力。
与本科生不同,研究生的学习一切要围绕着如何做好研究去读书、去思考。先生因为只招了我一个学生,也就不在教室,而是在家里上课。实际上,也不是上课,而是聊天。聊天比较放松,使学生容易接近老师,了解老师的治学思维、学术观点。不像现在上课,上完课,各奔东西,师生很少交流。当然,现在一年招生数十人,也没法用这种形式了。当时我“求知”心切,恨不能一下子就得到一个 “灵丹妙药”,能快速读书、搜集材料、撰写文章。先生告诫我说,任何事情 都不能一口吃个胖子,现在趁年轻,要多读书,读好书,打下坚实的基础,一辈子受益无穷。他给我谈了中国近现代史各个领域的名家、名著,要我找来阅读。我感兴趣的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他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学者最权威, 像严中平、吴承明、李文治、章有义、汪敬虞、彭泽益、宓汝成、聂宝璋等人的论著,都绕不过去,必须在这些大家的基础上做研究,才有可能取得像样的成就。按照老师的指点,我将他们的书和论文,凡是能够找到的,都仔细阅读了。真可谓名不虚传,这些论著给我的启发是多方面的,选题、资料、结构、分析乃至文字表达,都是可资学习的榜样。当我由学生变为老师,指导研究生时,我也特别强调对名家名著的精读,不要将宝贵的时间浪费到一般或者次品之中。
仅仅读书,而不实践,经常是感觉人家写得好,而自己还是不知道如何下手进行研究。先生的办法是以课题带动研究。我先后参加了他三个课题,一个是 “中国近代经济史讲义”,另一个是 “中国抗日战争史”,还有一项是 “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家研究”。仅就那本经济史讲义而言,我读完了中国社科院经研所老一辈专家编纂的全套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以及现有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资料汇编,看了无以计数的论著,撰写了其中的一些章节。这些研究成果虽然没有出版,但这一实践,给了我非常严格的学术训练,使我懂得了基本的学术研究方法,尤其是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

图为1983年傅尚文先生(左一)参加《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座谈会
我记得,我经常背着个大书包,借书,读书,还书,宿舍、图书馆、食堂三点一线,难得有空闲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很累,真想休息休息。但为了多学一些东西,我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其实,都是因为有先生 “莫负年华”的警醒和激励,它时时鸣响在我耳边。
我看了那么多著作和资料,自我感觉能写文章了,所以就想投稿。尤其是看 到其他专业有的同学发表了论文,颇为羡慕。傅先生是《历史教学》的创办人, 一直担任编委,我以为经过他修改、推荐,是有希望的。于是,我把这个愿望汇 报先生。他说:按照你现在的水平,写出几篇文章已经问题不大,但还有必要加强学习,提高质量,不要着急发表论文。否则,文章一旦发表出去,如果存在不少问题,就很难收回了。希望你在研究生毕业后,在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发表论文, 那样会更加成熟,少留遗憾。其实,他是想让我 “莫负年华”,继续磨炼基本功, 真正写出有水准的论文。就这样,我谨遵先生嘱咐,研究生三年我没发表一篇文章,按现在一些学校的要求,连毕业答辩的资格都没有。但它培养了我不苟且、不敷衍的严谨作风。
做毕业论文时,为了锻炼我的独立研究能力,先生让我自己选题。我选了一个难度较大的乡村史题目,做得很辛苦。除了河大的资料外,我还到北京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社科院近代史所、北大、清华、中国人大以及重庆、南京查阅资料,多次到乡村做实地调查。现在看,田野考察已成为历史学者的一种研究方法, 而当时还是很少的。先生为了扩大我的视野,还亲自带我走访京津著名学者,让我大开眼界。每次前往京津的路上,他都说韶光易逝,要充分利用现在良好的学术环境,做出成就。我也一再表示,一定要做出一篇既对得起老师,也对得起自己的毕业论文。一篇硕士论文,我做了十多万字。答辩主席和委员是著名史学家 李文治先生、从翰香先生,他们都对我的论文给予了高度评价,说我照此下去, 一定有光明的前途。到这时,我也第一次听到他私下表扬我的话:这样的论文拿 到北大、南开也不逊色。一个后生小子,听到前辈如此的鼓励,感到所有的付出、所有的汗水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