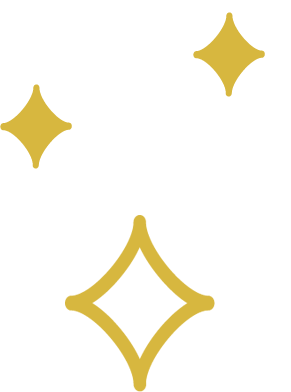我是最近才听过袁文逸的。
我听过的袁文逸,曾是一名东方卫视的战地记者。她在奥妙联手网易公开课的一场名为“勇于改变,活出奥妙人生”的主题演讲中,提到自己的工作。
她说:

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探索周遭世界的方式与他人相比,可能并没什么不同:最初是通过报刊亭和家里的电视来认识世界,后来借助笔记本电脑和互联网络来获取资讯,再后来有了可以跟世界的声音保持同步的手机,和更大屏幕的手机。
说来奇怪,我们获取资讯的方式越来越便捷,得到的信息越来越丰富,但我们表达观点和态度的方式却越来越,怎么说,我是该说单调,还是直接?

曾经的我们,会提笔写快乐写苦痛写读书札记写观影感受,再后来我们凭借电脑鼠标和键盘逛论坛刷网页开博客。
是从什么时候,我们渐渐迷失在140字的短消息框架里?又是在怎样的契机下,我们仅仅用转发表达自己的观点,用表情包记录自己的情绪?又是谁告诉我们:当我们选择按亮竖起的大拇指图标,就是最便捷最包容一切的表达形式?
我们以为自己离这个世界很近,以为自己通过指尖了解的资讯也足够多,但我不知道科技的便利和自我的选择,是否成为亲手为自己设下的藩篱和限制,把自己更远地推离真实。
我知道的袁文逸,是毕业于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女生。
从2011年到2015年,正是这样一个对生命保持敏感的女生,走过了世界上主要的一些战乱地区:利比亚、叙利亚、埃及、乌克兰,有一半以上的时间给了战乱、动荡和新闻现场。

著名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曾说过:“如果你拍得不够好,可能是你离得不够近。”也许每个身处战场的记者,都曾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无常,也见识到死亡的迫近和无情,但依然以为所当为的坚强,将这句话当做箴言来践行。
在距离现场足够近的地方,袁文逸体验着走出文字和影像的真实的战争。
她描述子弹在头上掠过时发出嗖嗖的声音:“它好像还在震动,把空气都划破了。”
在叙利亚大马士革遭遇过汽车连环爆炸后,她第一次明白小学语文课本里“血泊”这个词的含义:蓝天、白云、焦黑的墙面和被炸的车辆,都清晰倒映在地上的血中。

在距离现场足够近的地方,无可避免死亡也会离自己更近。
袁文逸说起自己人生中遭遇的第一次炮袭:当炮弹在身边不到两百米的地方爆炸的时候,裹挟着巨大的气浪,裹挟着撒哈拉沙漠里的沙子,扑到脸上。有那么一刻,时间仿佛是静止的。可能只有一秒两秒,但是好像过了很长很长。脑子里的记忆不是连续的,而是一张张静止的照片。即便卧倒在地,即便边上有同伴摁住自己的头,即便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心里仍然体会到一种真正的无助,因为她不知道下一颗炮弹会落在哪里。

也正是在足够近的地方,她拍下这样一帧相片:在乌克兰顿涅茨克,一个带着眼镜的斯文少年。他在战区边上只学了十几分钟的步枪射击,就被人带着走进交火最为猛烈的机场。她不曾知晓这个男孩的姓名,不知道他是否在此刻会偶尔想起班里心仪的姑娘,她只知道不会再见到他走出机场。
她带着一双中国的眼睛来到战地,代表在中国背景当中有着中国视角的我们,去真实和客观记录,去理解、去诠释战争的含义,也让我们思索如何尊重自由和生命,又该如何更好活着。
看完她的经历,我经常会问自己:何不从此刻开始站起来走出去,去自己拍自己感受?何不挣脱曾经为自己设置的藩篱和限制,去体验人生的精彩?
试着从停止以140个字符定义自己的人生开始;从不再依靠转发或表情包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开始;从不再用标签来定义世界万物开始。
与世界更靠近的时刻,也是与真正的自己更靠近的时刻。
最近我看到了奥妙一组户外系列广告,让我第一次了解到赵奕欢不为人知的一面。照片中的赵奕欢,一改往日的光鲜亮丽的性感形象,而是满身泥水,一脸坚定地冲向前方。
她说自己很幸运拍摄了三部《青春期》,但从此也被贴上“宅男女神”的标签。这个标签让她感到不安,她开始思索:真正的我是这样的吗?与其活在性感的标签里,我为什么不去改变?去尝试和世界更接近,去尝试体验人生的精彩?

于是便有了这样一张不寻常的照片。
赵奕欢说服了经纪人,让她去参加世界级障碍赛"斯巴达勇士赛"。赛程6.7公里,22道障碍关卡:下泥潭,翻越障碍,铁丝网下爬行挑战……照片里,当赵奕欢带着满身的泥水冲过终点的那一刻,她觉得终于把“宅男女神”这个标签甩在身后——这次,她是斯巴达勇士赵奕欢。她的奥妙人生故事,让渴望表达自我、活出精彩的心,重新有了跳动的能量。

当我们跟世界更靠近一些的时刻,也是我们跟自己率真的心更贴近一些的时刻。正如,奥妙品牌所倡导的理念,“洗得掉的污渍,带不走的经历,活出奥妙人生”。
走出去,去离世界更近一点,去纵情表达率真的自我。女性不应该之受制于表面的“家庭妇女”或是“性感女郎”等标签,应当鼓起勇气,去感受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去经历每一次的全新体验,走出朋友圈,去活出真正的奥妙人生。
这里有一个
只有女性
的肖像展,这里有
38
个姑娘的故事,LOFTER不打烊展览馆联合奥妙,举办LOFTER不打烊女性肖像展,邀请四位摄影师,用肖像的方式记录下38位女性“活出去”的故事。
点击
阅读原文
,即可在线上参观此次“她说”女性肖像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