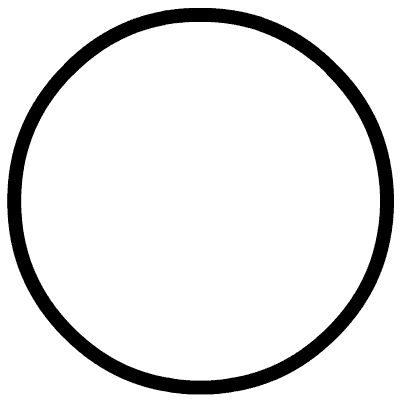
点击上方关注我们

Zach Blas, Facial Weaponization Communiqué: Fag Face, 2012, video still. Courtesy of the artist.
黑客阶级已死,但黑客长存!
The Hacker Class Is Dead, Long Live the Hackers!
文 | Francisco Nunes
译 | 振声
原文出处:e-flux Issue #146 June 2024
我们中的一些人比其他人老得更快。自《黑客宣言》(A Hacker Manifesto)首次发表以来,20年的时间对那些“神经脆弱”的人来说并不友好,在Tiqqun看来,这些人拒绝“满足于任何形式的舒适”。与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托尼·奈格里(Toni Negri)的“诸众”(multitude)等一些当代时髦的替代词相比,《黑客宣言》的理论表述更加一致,同时也摆脱了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即将到来的共同体”(coming community)等词在语言学和文字学上的简化主义。虽然这两个术语都指出了当代形式的生物政治学重新利用主体身份及其表征的方式,但哈特和内格里的“共同行动的独一性”以及阿甘本的“无论何种独一性”都很少关注自我构成的社群摆脱将其束缚于主流秩序的压迫性结构时的实际物质条件。通过在信息矢量的发展中找到实现这一突破的可能性条件,沃克(McKenzie Wark)的黑客们获得了一个出发点。
沃克的宣言具有独创性和煽动性,它试图阐明一个新阶级的存在,这个阶级是在生活和劳动日益信息化的过程中产生的黑客阶级,是新近占统治地位的矢量主义阶级(vectoralist class)
【沃克认为,矢量主义阶级就是在信息政治经济学中拥有、操作、控制信息网络和平台的阶级——译注】
的对立面。在当时(世纪之交),黑客阶级需要盟友,它还必须发展和强化其阶级利益,并获得完全成熟的阶级意识。黑客阶级将实现阶级概念本身的最终归属,即阶级政治的虚拟化。信息将是这一进程的驱动力,事实证明确实如此。然而,我们在过去二十年中看到的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新的主导财产形式,信息的抽象潜力是不够的。被矢量主义者彻底商品化的信息无法“释放阶级性的虚拟性”。
因此,那些抵制资本主义矢量转向的人一次又一次地加强了身份和表征对虚拟性和抽象性的控制。尽管这往往是确保某些形式权利的唯一途径,也是对抗政治抹杀的唯一可用形式,但身份诉求与其国家认可的表征之间无休止的相互作用,确保了沃克的黑客们要带来的“身份危机”不会深刻到足以从根本上动摇自由主义政治的主体。这一危机源于黑客所释放的虚拟性,它并非以纯粹的语言或操演性转向为前提,而是绝对内在的、物质性的。黑客要通过一种表达政治来颠覆自由主义主体的自我封闭——这种表达政治由黑客提出,可以克服困扰资本主义主体化的“稀缺和匮乏的约束”所带来的限制。
从那时起,黑客们遭受了不止一次的打击。用沃克的话说,资本的死亡并不意味着其运作力量的消亡。资本家比比皆是,这一点我们再清楚不过了。黑客的形象可能仍然存在,但它的存在显然在政治上是无力的;它只保留了同犯罪的联系,其伴随的意象越来越局限于一系列鬼魅般的表现形式,就像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或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笔下的赛博朋克的黑暗小巷。信息作为全球经济生产的主导力量所开辟的数字空间已逐渐丧失了其激进的可能性。如果说有死亡,那就是黑客阶级的死亡。
沃克将黑客概念化为触及不可表述之物的事件时,她所设想的潜能得以幸存,这将导致一种超越表述的禁锢、超越信息、超越财产的政治。而这正是《黑客宣言》的起点:抽象性,那个令世界惊恐的双重性,无论人们选择哪种表述方式,它仍然是当前生产方式背后的主要驱动力。
Juliana Huxtable, BAT 3, 2019. Inkjet mounted on Dibond. 29 3/4 x 44 3/4 in.
“抽象是每一个黑客所产生和确认的。”这句话依然正确,但这里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抽象?哪些抽象的产物导致了矢量主义者的横行和黑客阶级的消亡?沃克的论点是,“黑客阶级产生于以知识产权的形式将信息转化为财产的行为之中”,因为矢量阶级“使专利和版权等同于工厂或田地”。然而,今天,矢量主义者现在和未来的利润来源不仅仅是知识产权。当然,信息是这一过程的核心,但矢量阶层从中获利的信息远比传统的知识产权、专利和版权抽象得多。
矢量主义阶级将这种捕捉提升到了一个更加抽象的层次。它不再仅仅是一个拥有矢量和物流系统的问题,尽管这些矢量和系统使生产出来的信息得以转化。它还关系到从元数据的无限重组潜力中获取盈余的扩展可能性。沃克在《黑客宣言》发表十年后写道:“那时,我们可以成为数据朋克;现在,我们必须成为元朋克。”十五年后的今天,情况变得更加严峻了:“现在几乎无法想象,在信息技术中会有一种开放式的、游戏性的方法,让新事物从旧事物中脱颖而出,而且这种方法完全不会被信息矢量的商品化和控制所遏制。”
如果说阶级压迫是建立在最初的剥夺之上,那么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一看与黑客阶级被掠夺相对应的奠基时刻——作为一个最初反复出现的时刻,也就是其劳动产品被俘获和占有的时刻。在沃克看来,正是在发现了黑客阶级的原始物质(信息)的“非物质虚拟性”后,该阶级才开始了与其阶级前身的历史性决裂。这在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摆脱稀缺神话的一线生机:无束缚的信息,虚拟性的无限物质实例。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表面上看是抽象层面量变的结果,实际上却是潜伏在主流商品形式背后的阴影。从数据到元数据,从信息等同于知识产权到信息等同于以数字为媒介的行为的每一个残留痕迹,那么什么才是当今的根本性破坏呢?
正如弗雷德里克·奈拉特(Frédéric Neyrat)正确指出的那样,当今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的主要商品——当下可以称之为矢量主义——是由“购买记录、选举、预防措施,和色情广告等数字化的个体元素,经过机器人和市场算法组装而成的”,而且它们能够按照跨个体的方式进行(再)组合和(再)组装。由人类和非人类的——越来越多的是后者——网络元素生产和收获的信息,已成为信息的原始形式,也是黑客阶级迅速解体的主要原因。
这类信息抽象而丰富,并不完全是劳动产品,但几乎每个人都在生产它们。事实上,它更多的是非劳动的结果,或者说,非劳动越来越多地转化为一种劳动形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所有生产这些数据的人都变成了黑客——从旧事物中创造新事物的人。通过大幅扩大信息的概念和物质范围,更重要的是,通过发现信息的抽象力量并不止步于表征层面(它一直向下延伸),矢量主义阶级抵消了其中的黑客可能性。
矢量主义阶级意识到,信息爆炸所带来的抽象化进程在捕捉和管理全新表征性王国的过程中引入了内在的不稳定性,他们很快就明白了沃克的激进黑客们已经理解的东西:所有表征都具有内在的虚假性。但是,矢量主义阶级并没有允许自由表达的相互作用,从而导致不可还原的差异领域,而是利用其矢量沿着新的次主体路线重构表征。因此,“分而治之”的策略被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抽象水平,它现在被应用于最细微的元素。

凯瑟琳·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将矢量世界的后人类描述为“一种恰好在生物基质中实例化的信息模式”。与主体产生的非实体信息相比,不仅主体边界的物质性无关紧要,其表征也是如此。
当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占主导地位时,它就必须像“经授权的表征警察 ”一样,密切管理表达与表征之间日益不稳定的联系——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动员国家去约束身份的传统。矢量主义阶级最大的黑手就是先发制人地瓦解这种联系,然后战略性地占有取而代之的空间。如果说矢量主义是建立在连接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物质胜利之上,而连接主义是“技术主义完全透明梦想的实现”,那么,只有当表达与其表征之间的距离变为零时,这种透明才能完全生效。
这种联系的消失揭示了表达与表征之间不可能存在的对应关系。这种虚无化非但不会导致对无限和无限制的虚拟性的肯定——即超越重复的差异——反而是控制不断扩张的身份所产生的不稳定影响的唯一可能形式。在数字抽象史最新章节的表面之下,我们发现了国家作为符号指涉物保障者的漫长历史中的另一个步骤的痕迹。
今天的主流抽象是无限重组的痕迹,而这种痕迹本身并不存在,那就是主体严密的、密封的内在性。在元数据的统治下,我们再也谈不上“符号与所指之间的不一致性 ”了。不存在 “不一致”,而是符号弥补了空洞:这是柏拉图式的悲剧。只有符号,没有所指。无独有偶,在所谓的“信息时代”,高度抽象的个体元素不断涌现——这些元素的永久性重组构成了主体表征和身份的基质——与之相伴的是源于隐私(或缺乏隐私)的(所谓批判性的)词汇。与其说主体被剥夺了构成某种主体性的符号,倒不如说主体是由这些符号群组成的。最重要的是,这既可以向上延伸,也可以向下延伸。社群沿着不断变化的巧合数据点,和以信息模式为索引的个体生命功能重新组合。事实上,“信息矢量延伸到了生活本身”。
Installation view TOTAL PROOF: The GALA Committee 1995-1997, Red Bull Studios New York, 2016. Photo: GALA Committee/Red Bull Studios New York
这并不是什么新把戏。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对新自由主义的分析中看到的,是矢量作为一种生产力早期发展的结果,当时它开始取代旧的资本主义统治。在早期的矢量时刻,我们首次看到了一个预先给定的主体,它被解析为可以量化的离散部分,从而被优化并进一步市场化(即加里·贝克[Gary Becker]所说的“人力资本”)。个人与市场的联系不再是通过抽象的、无所不包的劳动范畴。
斯蒂法诺·哈尼和弗雷德·莫腾(Stefano Harney and Fred Moten)在谈到“马克思所谓的自动主体的幻想,即资本可以不依赖劳动而存在的幻想”时指出,自动主体被人力资本所效仿,其形式是“空洞的主体......一个恰恰是通过驱逐劳动的否定性而致力于将自身空洞化的主体”。在他们看来,“人力资本”是主体对其被放逐的内部进行自我强迫的标志;这个主体被转化为“一个多孔的客体,但它仍然像一个主体一样说话”。在矢量主义的统治下,用于抽象人力资本的技术手段增加了这种多孔性。我们不要忘记:“生产不仅生产作为商品的客体,也生产作为其消费者出现的主体”。
顺便提一句,这正是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在批判“监视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时所忽略的。红利元素的重新组合指向了一个比“隐私”更深层次的问题——正如克莱尔·伯查尔(Clare Birchall)所言,“隐私”就像“我们从一颗死星上看到的光芒”。隐私权的主张让人联想起田园诗般的自由主义概念,即公共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完美界线,但在当代矢量主义权力的形式下,隐私权的主张越来越无用。相反,正如奈拉特(Neyrat)所言,“当资本主义变得具有重组性时,当资本主义控制了虚拟化和现实化的过程时,我们被剥夺的是我们的综合能力”。换句话说,矢量对我们主体化模式的殖民化,将主体的经验可能性领域限制在矢量每时每刻提出的数据点的连续过渡安排上。
西方(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批判,作为一种撕开意识形态面纱,将表征从资本主义拜物教中解放出来的实践,并没有取得成功。没有什么可以复原,没有什么可以揭露。在这个数字套娃中,各种外壳下的内核究竟是什么?如果对元数据商品化的过程进行逆向分析,除了以隐私为中心的谬论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复原?在这些噪音变成金钱之前,它们到底是什么?
几十年前,某种肯定性的模式为解放政治带来了希望;我们被告知要摆脱否定性,选择肯定想,正如福柯在为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反俄狄浦斯》所作的序言中提出的著名命题那样。简而言之,当福柯呼吁“差异胜过均一,流动胜过统一,流动的安排胜过系统”时,我们仍然需要做出政治选择。这也许是游牧浪漫主义的最后岁月。
在矢量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问题并不在于否定性因素的局限性与肯定想因素的解放潜力之间的斗争,而在于一个严峻的现实:流动才是主导力量,系统早已被多变的安排所取代,而今天的资本显然才是游牧的最高形式。矢量获胜了。
今天,真正的政治悲剧是互动性。事实上,正如沃克所言,“资本主义是一种以可交流疾病为形式的传染病。它让一切事物与其他一切事物进行交流”。“矢量主义是资本主义绝对可传播性的技术强化形式。从矢量主义的视角来看,元数据之类的东西是进一步抽象表征的精炼形式,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为矢量主义阶级带来了盈余。
这就是为什么黑客阶级无法从矢量主义者手中夺回任何东西,为什么这个阶级无法重建以获得解放:它所生产的抽象,它所产生的信息——无论是自愿的,还是无意的——都是不可赎回的。矢量主义者所利用的大部分东西并不完全等同于对某一阶级劳动成果的剥夺(即使情况的确如此)。或许我们可以更准确地将其描述为越来越抽象的表征的强制流通。
当然,后者是通过索引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的痕迹而产生的;它们几乎无处不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全球“智能”网络。但是,当它们与开发其经济潜力的矢量(或堆栈)脱节时,往往会变得毫无用处。矢量产生的信息不对称会不断被重塑,因为矢量主义者会拆除旧市场,创造新市场,利用任何一点可以进一步抽象的信息。
几年前,一位热心的控制论学者说:“信息与物质或能量不同,它不是一个守恒量:原则上,它可以无限制地复制。”他进一步补充说,互联网“由于其数字特性......可以被视为一种几乎没有摩擦力的媒介,它[使得]在实践中无限复制[信息]成为可能”。这位著名的控制论学者希望,这会导致“元系统......将整个人类及其所有支持技术和大部分周边生态系统整合在一起,并以我们目前根本无法想象的智能、意识和复杂程度运作”。这样,一个由“全球大脑”指挥的“全球超级有机体”就能够对特定系统中的代理人——在作者的矩阵中,这些代理人“可以是人、组织、细胞、机器人或任何生物有机体”——之间的互动进行认证、选择和分级。这种“智能网”将“[借鉴]其用户集体的经验和知识,而这些经验和知识则外化为用户在他们所走过的道路上留下的偏好‘痕迹’”。有没有比这更好的矢量主义理论实例?
我们的黑客是否已经抽象化为全球数字一体化,参与了矢量的基础设施的形成?还有这个“难题”(vexata quaestio):这是不是我们根茎式希望的不幸命运?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再也无法脱离普鲁东所说的“财产即盗窃”的论调;丑闻在别处,在那些永远无法成为财产的非财产本身被迫出现,并因此成为表征和交流的过程中。即使是最抽象的事物也可以采取财产的形式——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但这种财产不是那种存在于禁止占有的平面上的财产。
Jessie Jeffrey Dunn Rovinelli, So Pretty, 2019. Filmstill from movie. Courtesy of the artist.
正如过去二十年所证明的那样,当信息成为财产的主要形式时,它所带来的质的不同并不足以威胁其存在。信息的抽象力量本身无法取代财产形式。如果说黑客阶级未能将其劳动成果社会化,那是因为信息始终只是财产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潜在的财产。正如沃克所深知的那样,“财产一件件地制造出主体性的盔甲”。我们在今天的主体性盔甲上发现的漏洞,就是矢量主义者成功控制连接信息与表象的门户的证明。
既然过去二十年的悲剧已开始在各地上演,那么黑客们又该从何入手呢?今天的黑客不必成为新的历史主体——左翼无休止的标签游戏中的又一次迭代,用一个集体主体取代另一个集体主体。从萨帕塔主义者(Zapatistas)到“占领”(Occupy)及其他群体,每当一个新的集体主体失去政治动力,左翼的革命希望就会转移到下一个集体主体身上。这个“即将到来的群体”永远只在到来的过程中。
在阶级关系的钙化历史之外,“黑客”或许可以作为表达的物质实例——作为非主体性平面的投影——重新焕发活力。实际上,矢量主义者一直在做第一部分的工作。他们越来越抽象的表述方式对主体的掏空程度是黑客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因此,让我们承认我们的损失;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报告失窃,而是为了计划我们在流亡中可以做些什么。
就像二十年前的沃克一样,我们也不会“把潜在性作为语义人质献给敌人”。潜在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已经知道,在矢量中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流通的身份之表征不仅是虚假的,而且其短暂的配置会被周期性地撤销,并被其他在环境上更适合扑灭任何反抗火花的表征所取代,从而赚取一些钱。我们“跳起了错位的舞蹈”,摆脱了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真理的技术性测量”的焦虑。既然矢量主义者已经明确地回归了柏拉图主义,既然正如亚历山大·加洛韦(Alexander Galloway)所指出的,“生成已经优于存在”,所以我们的出发点也许就更加明确了。
我们的潜在化和他们的现实化,我们的使用价值和他们的交换价值,我们的表达和他们的信息之间的斗争还在继续吗?生产工具的发展——在全球数字一体化时代不断强化的抽象化——对于新事物来说,对于任何表达方式来说,都不足以触及无法表现的事物。如果“黑客”作为一种概念工具要继续存在下去,它就必须超越自由主义的普遍性,形成一种共同的形式。
A Syrian refugee scans her iris at an ATM at a branch of Cairo Amman Bank, Amman, Jordan. Photo: UNHCR, 2015.
沃克已经指明了方向,但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那时,或许可以通过暂时“默许代表权”,在阶级冲突中获得一些让步。但这一空间已经被矢量主义者黑掉了。现在,“黑客”只能在难以察觉的情况下进行交易,再次在黑暗中重塑表达。在“追求不存在”的过程中,黑客既是概念,也是策略。由此看来,黑客阶级的失败根本不是失败。换句话说,黑客不是一种身份,不是阶级关系更新计划中的一个位置,而仅仅是一个点,它是沿着通向通用性和共同性的逃逸线上的某处。
德勒兹深知,共产主义的投影之一——共同性——一直与自由政治的主体格格不入。如今,统治性矢量所授权的主体化的永久重组形式已经终结了对理想化主体的任何重启。哈尼和莫腾争辩说:“物流想要完全摒弃主体”。矢量主义作为物流管理的最复杂形式,所做的正是如此。在这一过程中,它让我们中的许多人体会到了“成为别人供应链中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感觉。
塞布·富兰克林(Seb Franklin)在讨论爱德华多·威廉姆斯(Eduardo Williams)的电影《人类浪潮》(El auge del humano, 2016)时谈到了这种特定的困境:主体“被标记为不可靠的组成部分”,某些身体是“有待计算的生命”,而另一些则是“有待凝结的生命”。富兰克林对生活在一种 “对价值信息需求漠不关心的关系 ”中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因此,“黑客”可以被视为一种“漠不关心”的密集化形式,它为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认为的策略性减法提供了物质基础,而策略性减法正是解放的特权姿态。
在沃克看来,黑客阶级是要“黑透并摒弃客体和主体的所有属性”。现在,矢量已经将所有这些属性——除了属性形式之外的所有属性——都抽象化了,黑客们找到了新的帮凶来完成任务。矢量主义者在建立了一个过度充斥着他们在政治上使之失效的身份诉求的超级传播王国之后,对努力维持生命与其投射形象之间稳定对应关系的虚构越来越不感兴趣了。
如果正如安德鲁·卡普(Andrew Culp)所说,“减法是地下的政治学”,那么这个减法平面就是新的、意想不到的黑客可以帮助瓦解矢量统治阶级的地方。地下世界充满了非自然的帮凶,有人类的,也有非人类的。蝴蝶和菌丝体也是“黑客”,但它们的“黑”往往被定格为生命能量和循环流动的完美交流网络的一部分,与资本主义共享着绝对可通约性的伦理。相反,“黑”能否成为一种异种交流(xenocommunication)的工具?
是否有一种方法可以将线条投向一个不分在场与外表的外部世界?除了重演关于哪种概念工具更符合当前困境的令人厌倦的争论之外,只要我们挖掘后情境主义机器及其继承者积累的沉淀物,显然还有很多东西值得借鉴。
有一些强度在起作用,由此导致了新的共谋。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黑客在工作,他们切割物质,形成巨大的不透明区域,拒绝表述。黑客们是否能找到新的方法,将每次相遇时的不确定性空间潜在化?哈尼和莫腾说得对:“我们欠彼此一个不确定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