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延平王
郑成功
当然是无可争议的民族英雄。开拓台海,功在千古,矢志抗清,至死不渝。
无论从中华民族的角度,还是从狭义的汉民族角度。
大明延平王:郑成功

郑成功当时后世屡被非议的“私心自用”,作为南明史权威著作,顾诚先生的《南明史》中对此严厉批评,认为郑成功视本集团的利害高于抗清大业,一心只为
割据自雄
,才多次拖延失约,不肯出兵配合李定国,令反攻两广大事不成,新会战败丧师失地,南明中兴从此无望。
大明晋王:李定国

岂不知郑成功不愿和李定国合兵而屡屡失约,与其是说他自己的私心,不如说更多是有明一代的严苛政治所致。
虽然他当时名义上奉了永历皇帝为君上,但郑氏是隆武皇帝最大拥立者这一事实无法改变,郑成功用以号令三军的“赐姓招讨大将军”,俗称“国姓爷”,皆是隆武皇帝所封。
而隆武帝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庶子传下的远支藩王,连明成祖朱棣子孙都不是。论血统,远远不及万历帝亲孙的永历帝近,在绝大部分永历帝支持者看来形同篡逆。
隆武皇帝殉国后,其弟称绍武皇帝,还曾和永历皇帝兵戎相见,大战一场,被清军乘虚夺了广州,亦殉国。而此时有记载,郑成功还私下拥立了淮王朱常清为东武皇帝,只是当永历皇帝使者来招抚时,迫于当时形势才取消了。所以对永历帝政权,郑成功是有洗脱不了的“
原罪
”的。
从百年前于谦于少保等拥立代宗的臣子遇害起,就彻底证明了大明臣子于国家社稷功劳再大,若在拥立问题上站队错误,也是万劫不复。
是以
从郑成功的角度,是绝不能将自己势力置于永历帝这方麾下的
,就算他本人再忠心大明,郑氏再多部将也绝不答应。
若永历帝真的反清成功,或至少实现稳定的南北对立,则郑氏必遭清算。只需一个御史上书发难,便必然群臣群起而攻之,令郑氏一门万劫不复。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实,永历帝给郑成功许下再多保证,双方都不可能相互取信,绝不以任何人的意志和品德为转移。
大明永历皇帝:朱由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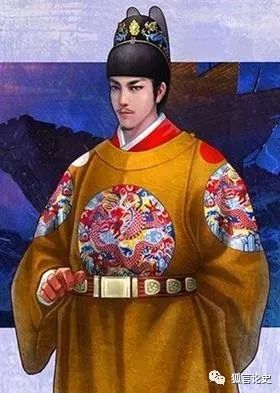
这场病因,早从
靖难之变
和
夺门之变
就种下了。在皇统问题上站错了队,是什么悲惨下场,大明臣子都明白。当靖难之变,竭尽忠心于一个朱姓皇帝,却会落到妻女家眷被野蛮蹂躏、世世代代打入贱民的境地时,大概就已经不会有多少人在兵败国危、大势既去时,还愿意对其中某位朱皇帝誓死竭忠了;
当夺门之变,于谦一个对大明帝国、对朱明皇室皆有再造社稷恩德的大功臣,仅仅因为皇帝对他的怨恨,以“「意欲」迎立外藩”罪就被杀害、家属流放戍边时,扪心自问,又还有多少人,愿意再对这样的皇室去效忠,步于少保后尘呢?
大明少保,兵部尚书:于谦

终于演变到明末,有士子提笔写下「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道出了他们的共同心声,无数个文武臣僚皆视君皇如陌路,坐视其自取灭亡,岂知却让清虏趁虚而入,导致衣冠沦丧、神州陆沉的历史大悲剧。
南明的几十年,为何始终在强敌当前依旧众心不齐,内讧不止,无数品行高尚的忠臣志士皆不可免,根子就在这里。李定国毕竟是农民军出身,对这套冷酷帝国规则也未必能充分理解。所以才会一次次对郑成功的会师合兵,抱有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所以,这只是令人叹息、而无可奈何的大悲剧。
不论古今,什么时候都缺不了污蔑英雄、落井下石的宵小;比如于谦遇害时,某地一个教谕小官上书,就说于谦罪当灭族,于谦荐举诸文武大臣都当一并诛杀。好在当时明英宗朱祁镇并其大臣还有基本的智商,知道众怒难犯,连他自己的母后孙太后都因此叹气哀伤,无声抗议,此事遂部议不行。
将心比心,哪怕逆挽天澜重光华夏,哪怕像于谦于少保那样流芳千古,但自己和家族必遭清算,再由后一个皇帝来无济于事的平反,郑成功当然不愿如此下场。
所以他既要坚持反清,亦一定要坚持自己势力的独立地位,而不能将军权政权交诸南明皇帝,任其生杀予夺。
事实上,郑成功作为大明的孤臣孽子,和晋王
李定国
一样居功至伟,并为彼时守护华夏、力挽天倾的两根擎天之柱。
镇江之战
,以步克骑,一万五千清军被杀得只剩千人,南京的驻防八旗伤亡惨重;战后郑军一度直抵南京城下,满清顺治帝福临几乎想要亲征应战。而整个长江战役,这也是抵抗满清暴虐民族征服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战役,曾令清廷闻风丧胆,坐卧不宁,各地仁人志士为之兴高采烈、翘首以待。
厦门之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