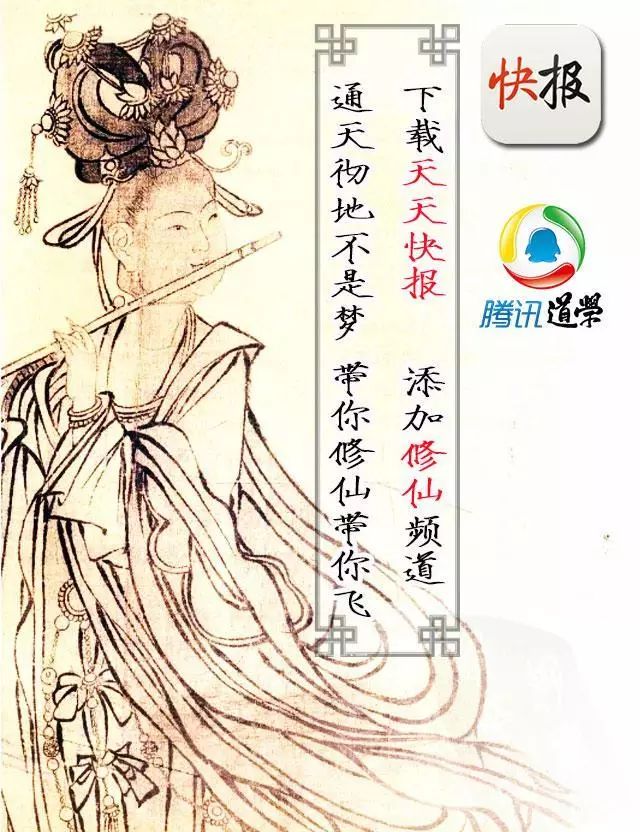本文所说的庄子学术态度的超越性,更多的是指其思想的内在超越。本文将比较庄子和孟子、荀子、墨子、韩非子的学术态度,指出庄子思想的反独断倾向以及孟子、荀子、墨子、韩非子思想的独断性。
王耀辉,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专业为专门史——道家道教研究。
在诸子林立,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孟子、荀子、墨子、韩非子等人都认为自己的学说是绝对正确的,别人的学说是错误的,是需要加以消灭的。
这种学术态度使他们的学说具备了两个基本特征,即绝对性与排他性。
这两个基本特征,鲜明地反映了他们思想的独断性。与他们不同的是,
在学术态度上,庄子认为不存在绝对正确的学说,也不存在普遍的是非判断标准
。同时,
庄子主张超越这些学说的是非争论,去体验逍遥自由的心灵境界
。
这种学术态度使庄子思想具有明显的相对性与超越性,而这正是庄子思想反独断倾向的明确反映。庄子思想的反独断倾向在历史上发挥着重要影响,它启发着人们的质疑和批判精神,为人们采取更为开放的学术态度提供着理论支持。

百家争鸣(资料图)
对庄子思想的反独断倾向,虽然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已经有学者进行了研究,但是一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其实,考察庄子思想的反独断倾向,对我们理解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一般来说,独断性在学术态度上主要表现为绝对性和排他性。王洪水指出,
独断主义在认识论上总是将某种认识成果夸大为绝对真理,在逻辑上总是武断否定异己学说并对其进行排斥。
本文也将从这个意义上来使用独断性这个概念。
以前,人们认为庄子思想的反独断倾向主要体现在其相对性上
。冯契指出,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庄子认为诸子百家之间的是非是无法辨明的,并对他们采取比较合理的宽容态度,这与孔子、孟子、墨子、管子、商鞅等人认为自己的学说就是终极真理,并且强烈反对其他诸家学说的学术态度明显不同。冯契认为,
庄子思想是具有相对主义特征的,是反对独断论的
。陈霞也认为,相比于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家们的独断论倾向,
庄子思想带有相对主义色彩,它否定绝对权威和一元化真理,否定非此即彼的简单的形式逻辑,反对独断论和主观主义。
他们的观点很有启发性,但是他们都没有对独断论作出清晰界定,也没有对战国诸子的独断性思想分别加以阐释。
本文认为,
在学术态度上,庄子思想的反独断倾向除了体现在其相对性上以外,还体现在其超越性上。
刘固盛和涂立贤指出,庄子思想的超越性主要表现为内在超越、外在超越和终极超越,即回归本性、顺应社会以及与道合一。
本文所说的庄子学术态度的超越性,更多的是指其思想的内在超越,即舍弃成见,超越是非,心灵虚静。
本文将比较庄子和孟子、荀子、墨子、韩非子的学术态度,指出庄子思想的反独断倾向以及孟子、荀子、墨子、韩非子思想的独断性。
庄子思想的相对性主要体现在其对绝对真理和普遍标准的否定上。庄子认为,绝对正确的学说是不存在的,他指出: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
”在庄子看来,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而知识却是无限的,用
有限的认识能力去探求无限的知识世界,只会让人疲惫不堪,在这种情况下,人又怎么能建立绝对正确的学说呢?
庄子从人的有限认识能力出发,不仅否定了别人基于感性和理性认识建立绝对正确学说的可能,而且否定了自己通过这种认识途径建立绝对正确学说的可能。
另外,
庄子认为,普遍的、客观的是非判断标准是不存在的,因此,在诸子学说之间也并不存在绝对的对错之分。
在他看来,立场不同,是非判断标准也就不同,世上并不存在恒定的、普遍的是非标准,他指出:“毛嫱、西施,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徒,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庄子认为,因为立场不同,人认为美的,鱼、鸟、麋鹿并不认为美。也就是说,
立场不同,是非判断标准也就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诸子学说谁是谁非根本无法分辨。
综上可知,庄子认为,因为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和判断标准的不固定,在诸家学说之中,没有哪家学说是绝对正确的,诸子学说之间也不存在绝对的对错之分,这种学术态度具有明显的相对性。
与庄子不同,
战国时期,孟子、荀子、墨子、韩非子等人都宣称自己的学说是绝对正确的,这种学术态度使他们的思想都具有强烈的绝对性。
而这种绝对性,正是其思想独断性的明确反映。孟子就坚信自身学说是最正确的,不容怀疑的。
在孟子眼中,自己提倡的仁义之道是治国理民的不二法门,它就像工匠用的规矩一样,具有客观性、绝对性、普适性
:
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资料图)
孟子认为,不论是什么样的统治者要平治天下都要行仁政,就像任何工匠画方与圆必用规矩,任何乐师正五音必用六律一样。
在孟子看来,自身学说就是真理,它是不必反思,不容怀疑的。在坚信自己学说绝对正确的同时,孟子还认为别人的学说是绝对错误的
。孟子声称:“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用激烈的言论抨击了和自己主张相反的杨朱以及墨子的学说,在他看来,这些学说是完全错误的。这种学术态度显现出了孟子思想的绝对性。
战国时期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同样持这种学术态度。
荀子认为,自己的学说是绝对正确的,它足以作为衡量其他诸家学说的尺度,荀子宣称:
礼之理诚深矣,“坚白”“同异”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诚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说入焉而丧;其礼诚高矣,暴慢、恣睢、轻俗以为高之属入焉而遂。故绳墨诚陈矣,则不可欺以曲直;衡诚县矣,则不可欺以轻重;规矩诚设矣,则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于礼,则不可欺以诈伪。故绳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规矩者,方圆之至;礼者,人道至极也。
礼是荀子思想的核心,
在荀子看来,礼义就像绳墨、规矩一样具有客观性、普适性,它是衡量其它学说的标准
,用礼这种尺度去衡量名家之狡辩、法家之典制、陋儒之学说,它们的弊端就显露无疑了。也就是说,
荀子认为,自己的学说是绝对正确的
,相比于自己的学说,其他诸家学说都存在严重弊端。荀子的这种学术态度,反映出了荀子思想的绝对性。
与荀子类似,
墨子也认为自己的学说是绝对正确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在他看来,自己的学说足以成为衡量别人言行的标准,他声称:“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
墨子认为,自己的学说是上承天意的,是绝对正确的,是可以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的。
他自负地宣称:“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犹舍获而攗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犹以卵投石也,尽天下之卵,其石犹是也,不可毁也。”在墨子看来,
自己的学说绝对正确,那些认识不到自己学说的正确性或者抨击自己学说的人都是愚昧的。
墨子完全肯定自己的学说并否定其他诸家学说,这种学术态度反映出了其思想的绝对性。
韩非子的学术态度与孟子、荀子和墨子如出一辙
,他也认为自己的学说是绝对正确的。在他看来,自己的学说是完美无缺的,它反映了客观真理,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韩非子指出:
巧匠目意中绳,然必先以规矩为度;上智捷举中事,必以先王之法为比。故绳直为枉木斫,准夷而高科削,权衡县而重益轻,斗石设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
以法制国是韩非子的核心主张,韩非子认为,法律就像工具用的绳墨、规矩一样具有客观性和准确性,它是不容怀疑的,绝对正确的。其实,
法律是随着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并且不同环境下人们对法律的理解也存在差异。
法律固然具有客观性,但韩非子却把自己所说的法律等同于工匠所用的绳墨和规矩,把它当成不容置疑的东西,这就夸大了法律的客观性,使自己的思想具备了鲜明的绝对性。
综上可知,
战国时期孟子、荀子、墨子和韩非子都秉持一种绝对性的学术态度,而庄子的学术态度却是相对性的。
他认为不论是自己还是别人,都不能够通过感性和理性认识建立起绝对正确的学说,世上也不存在普遍的是非判断标准。在他看来,
诸子学说尽管存在着差异和对立,但它们只是立场不同,认识不同,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对错之分。
这种相对性的学术态度是庄子思想反独断倾向的一个重要表现,同时,它也为其思想的超越性提供了前提条件。
庄子思想的超越性主要体现在其对诸家是非的超越以及对心灵自由的追求上。庄子认为,战国诸子思想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因此,持续争论谁是谁非除了造成人们心灵疲敝以外,并没有太大意义,他指出:
“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
在庄子看来,人们的是非对错没有定论,然而人们为了在辩论中说服对方,终日殚精竭虑,劳神苦思,实在是有害无益。因此,
庄子希望人们能够超越这种是非争论,进入到没有对立、没有是非的心灵境界之中。
庄子指出: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

庄子追求心灵的超越(资料图)
庄子认为,不同思想主张之间的是非争论永远没有尽头,它们的对错与否也无从判断。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最好是超越这些是非对立,进入到没有彼此差异,没有是非对立的心灵境界之中。
那么,如何才能进入到这种精神境界之中呢?庄子认为,
要想体验到这种精神境界,就要站在道的高度上认识事物,
抛弃一己之成见,正所谓“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
在庄子看来,人们总是“随其成心而师之”,用一己之成见把完整一致的事物分割开来,并坚信自己所看到的一部分就是事物的全部,都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的。这样一来,人们相互辩论,谁也说服不了谁,正所谓“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所以,
在庄子看来,当人们摒弃成心,站在道的高度上认识万事万物时,人们就会认识到事物的一致性,从而超越彼此之间的差异,超越是非之间的对立。
综上可知,庄子认为辩论诸子学说谁是谁非是没有意义的,他希望人们能超越这些是非争论,进入到逍遥自由的精神境界之中。同时,
庄子还指出了人们超越这些是非对立的方法和途径
,这种学术态度,显示出了庄子思想的超越性。
与庄子超越性的学术态度不同,孟子、荀子、墨子、韩非子都希望消灭其他诸家学说,统一社会思想,他们的学术态度都显现出了鲜明的排他性。在他们看来,
其他诸家学说都是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要想实现天下大治,就必须消灭这些异己思想。
因此,孟子、荀子、墨子、韩非子等人无不以消灭其他诸家学说为己任。孟子声称:“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
在孟子看来,杨朱、墨翟的学说都是歪理邪说,它们如同洪水猛兽,对社会危害极大。
因此,孟子希望能通过辩论驳斥这些学说的谬误,并最终消灭它们,孟子宣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认为,
自己之所以与这些异己学说进行辩论,并不是因为自己喜好辩论,而是希望通过指出这些学说的谬误,进而消灭它们,最终达到端正人心,统一社会思想的目的
。孟子视其他诸家学说为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并且希望消灭它们,这种学术态度,反映了孟子思想的排他性倾向。
荀子与孟子类似,其学术态度同样显现出了鲜明的排他性,他猛烈抨击异己思想,主张消灭其他诸家学说。他指出:
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它嚣、魏牟也。忍情性,綦溪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陈仲、史鳅也。不知一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悬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听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循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
荀子认为,它嚣、魏牟放纵情欲,行如禽兽;陈仲、史鳅过于高洁,不合大众;墨翟、宋钘不知君臣上下之分,过于节约;慎到、田骈终日讲法而无归宿,不可以治国;惠施、邓析狡辩而无用于社会治理。在荀子眼中,
这些学说都不足以治国平天下,但是它们却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迷惑大众
。因此,荀子希望消灭这些学说,他明确提出:
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六说者立息,十二子者迁化,则圣人之得执者,舜、禹是也。
荀子主张圣人执政,消灭这些学说,统一社会思想。这种学术态度显现出了荀子思想中蕴含的强烈的排他性。
墨子的学术态度同样具有排他性,
他认为其他学说的流行是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
,并希望消灭其他诸家学说,统一社会思想。墨子认为,思想混乱,百家争鸣,正是社会混乱的根源,他指出:
方今之时,复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长之时,盖其语曰“天下之人异议”。是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其人数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相交非也。内之父子兄弟作怨仇,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余力不以相劳,隐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朽余财不以相分,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
在墨子看来,
当时人们各执己见,相互论争,加剧了社会矛盾,因此,他强烈主张消灭异己学说,统一社会思想。
墨子希望君主和各级官吏能够发布政令,确立是非标准,奖励与此标准一致的人,惩罚违反此标准的人,最终实现“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这种思想统一于君主的局面。
墨子视其他诸家学说为社会动荡的根源,他强烈主张消灭异己思想,实现思想统一
。这种学术态度,反映了墨子思想的排他性。
在学术态度上,韩非子思想也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他认为当时的异己思想都不利于国家富强和社会稳定,因此,他主张禁绝异己思想的传播,韩非子指出:
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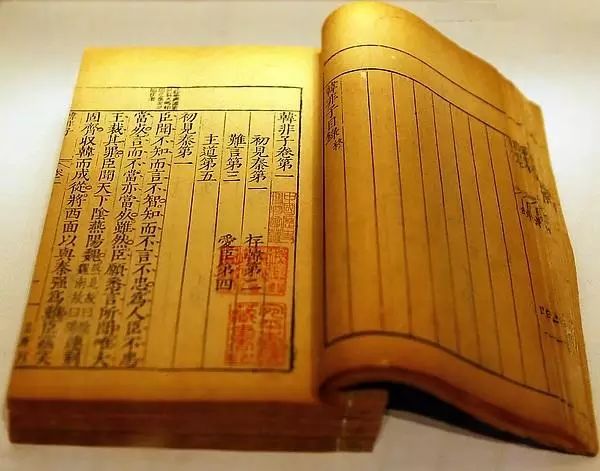
《韩非子》书影(资料图)
在韩非子看来,诸子学说的流行使国家从事耕战的人大为减少,这样就使国家越来越衰弱。因此,韩非子认为,
要想富国强兵,统一天下,就要消灭其他诸家学说。
他建议国君推行这样的政策:“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消灭百家学说,以法令统一社会思想,是韩非子的深切愿望
,而这也正是其思想排他性的鲜明表现。
综上可知,面对百家争鸣的局面,孟子、荀子、墨子和韩非子都希望扫除其他诸家学说,唯独让自己的学说与国家权力相结合,成为国家指导思想,进而辅助国君一统天下。这种唯我独尊的学术态度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而这也正是其思想独断性的明确反映。
与他们不同的是,
庄子希望人们能够超越这些无休止的是非争论,体验到逍遥自由的心灵境界
。在追求超越的过程中,庄子并没有建议君主消灭其他诸家思想,实现社会思想的一统,他只是希望君主能因顺自然,无为而治,庄子指出:“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在庄子看来,君主如果能顺应自然,不凭一己之成见去处理政务,天下就能治理好了。
在政治上,庄子希望君主不要对社会进行过多干预,以使人们能明悟本性,顺应自然。
相比于战国其他思想家,
庄子更多地关注人的心灵自由方面,而不是天下治理方面。
在追求精神自由的过程中,面对其他诸家学说,庄子的学术态度是超越性的,这种超越性,体现了其思想的反独断倾向。
除墨家思想在秦汉以后逐渐消失外,孟子、荀子和韩非子思想逐渐与国家权力结合,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国家意识形态构建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独断性思想固然存在一定弊端,但是他们思想的绝对性也有利于培养起后继者的学术自信
,而其思想的排他性也有利于维护传统思想秩序的稳定。与他们思想的独断性不同,庄子思想具有鲜明的的反独断倾向,
这种倾向在思想史上发挥的不是维护的作用,而是瓦解和开拓的作用
。就庄子思想的相对性来说,其对绝对真理和普遍标准的否定,鼓舞着人们的质疑精神和批判精神,让人们敢于怀疑原来的思想权威,从而创造出新的思想;就庄子思想的超越性来讲,
其对固执己见的批判和诸家是非的超越,也为人们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去看待诸家思想尤其是外来思想提供着重要的理论支持。
从历史上来看,庄子思想的反独断倾向对儒、释、道三家都有一定影响。
就儒家而言,庄子对绝对真理和普遍标准的否定有利于部分儒生摆脱某些伦理教条的束缚,打破对旧有权威的崇拜。以旷达著称的嵇康就深受庄子思想影响,他声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同时,他又“非汤武而薄周孔”。 商汤、周武王、周公和孔子是儒家圣贤的代表,经过汉代的儒学独尊运动,这些人物已经具备了神圣性与权威性,而
嵇康却公开声称自己对他们持批判态度,这种质疑权威的精神是与庄子思想的反独断倾向一脉相承的。
与他同一时期的阮籍也对儒家经典的神圣性提出了质疑,他在阐释庄子思想时指出:
彼六经之言,分处之教也;庄周之云,致意之辞也。大而临之,则至极无外;小而理之,则物有其制。夫守什伍之数,审左右之名,一曲之说也;循自然,小天地者,寥廓之谈也。
阮籍认为,儒家六经重在分别事物之间的差异,从而建立相应规则制度,通过外在约束使事物各安其分;
而庄子思想却重视事物之间的统一,崇尚自然无为,其格局更为宏大
。自汉代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以来,儒家六经就成了真理的渊薮,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人们要想表达自己的思想,只能通过作注的方式依托六经进行阐发。而
阮籍却将庄子思想上升到了比儒家六经更为高远的地步,这种举措无疑动摇了儒家六经的神圣地位
。
明代中晚期以质疑精神著称的李贽,也深受庄子反独断倾向的影响
,他在注解庄子思想时指出:“要见南华之意,直以儆世之愦愦者,直谓世之君子者,皆天之小人也。噫!孰知畸人者,乃畸人而侔天也哉!”李贽认为,《
南华经》也就是庄子思想的宗旨就在于警醒世人,让人们知道合乎儒家伦理的君子,正是损害天性的小人
,而不合于俗的人,却是保存天性,顺应自然的真人。在他看来,“仁义礼乐,皆外也。”也就是说,仁义礼乐,都是违反人的天性的东西,要想保持自然天性,就得抛弃它们。
李贽对当时被奉为神圣的儒家伦理进行了批判,而其批判的重要工具正是庄子思想。
综上可知,在汉代儒家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以后,
部分儒生往往借助庄子思想对儒家伦理的权威性与神圣性提出质疑。
之所以这样,不仅仅是因为儒家伦理和庄子所说的人的自然天性存在冲突,也因为庄子思想本身就有否定权威和普遍标准的反独断倾向。正是这种倾向,为他们批判已具备权威性的儒家伦理提供了思想资源。

要保持自然天性(资料图)
不仅儒家是这样,
佛教和道教中具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也往往深受庄子反独断思想的影响
。魏晋时期,玄学家多谈有无问题,僧肇则以一切否定的精神倡导非有非无的不真空义,他指出:“欲言其有,有非真生。欲言其无,事象既形。象形不既无,非真非实有。然则不真空义,显于兹矣。”僧肇认为,
本体无相,不能偏于有,也不能偏于无
。
僧肇这种一切否定的精神与庄子思想密切相关
,汤用彤指出:“《肇论》重要论理,如齐是非,一动静,或多由读《庄子》而有所了悟。唯僧肇特点在能取庄生之说,独有会心,而纯粹运用之于本体论。”僧肇的这一理论,对禅宗“出入即离两边”的无对观念也有深刻影响。由此可见
,庄子思想的反独断倾向是佛教思想中否定精神的重要源头。
与之类似的是,否定执着是非、有无的道教重玄学同样深受庄子反独断思想的影响,成玄英在阐释庄子思想时指出:
但群生愚迷,滞是滞非。今论乃欲反彼世情,破兹迷执,故假且说无是无非,则用为真道。是故复言相与为类,此则遣于无是无非也。继而遣之又遣,方至重玄也。
成玄英继承了庄子否定绝对真理的学术态度,批判了当时执着于是非争论、偏执一端的学术风气,倡导人们追寻超越是非的重玄境界。可以说,
道教重玄学是深受庄子反独断思想影响的。
对绝对真理和普遍标准的否定是庄子思想反独断倾向的一个重要方面,
它激发着儒、释、道三家内部的质疑与否定精神
。正是这种质疑与否定精神,推动着它们在思想领域不断开拓创新。另外,
庄子超越诸家是非,不执一偏的学术态度也为人们用更加开放的态度看待各家理论提供了思想支持
。在宋代,学术风气开放,思想家们往往力图调和儒、释、道三家理论的冲突,强调其一致性,具有超越性而不是排他性的庄子思想就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王安石就认为庄子思想和儒、释思想是相同的
,他指出:
庄生之书,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祸福累其心,此其近圣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
盖有见于无思无为,退藏于密,寂然不动者,中国之老庄,西域之佛也。
不执着是非,追求内在超越是庄子超越性思想的重要内容,王安石据此加以发挥,将其与儒、释思想统一起来。
在他眼中,庄子的性命学说和无思无为思想与儒、释思想存在一致性,它们是相通的,而不是相互对立的。
王安石仍旧秉持儒家立场,但这种三教合一思想无疑是有开放性的,而庄子的超越性思想则为这种开放性的学术态度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
吕惠卿则运用庄子的“道”思想来强调儒、释、道三教的一致性
,他指出:“道未始有物,而生天生地,神鬼神帝,日月星斗,得之以旋转者也。孔氏之儒,释氏之佛,老氏之道,未始不本与此。”吕惠卿认为,儒、释、道三教都以道为本,而吕惠卿所说的道,正来源于《庄子·大宗师》。可以说,
庄子思想是吕惠卿三教本一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
除王安石和吕惠卿以外,林疑独和黄裳也用庄子思想融汇儒、释、道三教。
宋代是学术风气较为开放的时代,这一时期的学者往往有一种比较开放的学术态度。
尽管他们都有自己的学术立场,但他们对于儒家之外的佛、道二教思想也多有涉猎。他们试图调和三教思想,在这个过程中,庄子的超越性思想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综上可知,在历史上,
庄子思想的反独断倾向对儒、释、道三家都有一定影响,其对绝对真理和普遍标准的否定启发着人们的质疑与批判精神
,鼓舞着人们在思想领域不断开拓创新;而其对诸家是非的超越也为人们秉持更为开放的学术态度提供着重要的理论支持。相比于孟子、荀子、墨子和韩非子的独断性思想,庄子思想的反独断倾向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价值。
在中国传统文化创生的战国时代,孟子、荀子、墨子、韩非子等人的思想已经具备了鲜明的独断性。在学术态度上,这种独断性主要体现为绝对性和排他性。
他们视自己的学说为绝对真理,认为别人的学说是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强烈主张消灭其他诸家学说。
这种绝对性和排他性的学术态度,正是他们思想独断性的鲜明表现。这种独断性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
它一方面有利于鼓舞后继者的学术自信,维护中国本土文化的稳定传承,另一方面它那种不容置疑的绝对性和摒弃异己思想的排他性也阻碍着思想的交流与进步
。正是在这一片自以为是的喧嚣中,庄子展现出了与他们截然相反的学术态度,发出了另类的声音。

逍遥自然(资料图)
庄子认为,不存在绝对正确的学说,争论诸家学说的是非是徒增烦恼的
。他希望人们能超越这些不同学说之间是非争论,进入到逍遥自由的心灵境界之中。庄子的学术态度展现出了鲜明的相对性和超越性,而这正反映了其思想的反独断倾向。尽管相比于战国时代那些自信满满的思想家,庄子的声音显得微弱,但
他的思想却总是启发着那些质疑绝对权威和普遍标准的后来者,让他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文明进程、社会秩序以及个体生命
。尤其是当儒家思想在汉代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以后,它就具备了强烈的神圣性与权威性。它在维护社会秩序和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也禁锢着人们的思想。
而当社会发生变革,人们的思想也随之改变的时候,庄子思想总是会重新焕发出活力,启发人们反思儒家思想的合理性。
正是他们的质疑、批判与创造,中国的思想世界才在儒家思想之外有了新的天地
。
同时,在学术风气比较开放的时代,庄子思想对诸家学说的超越而不是排他也为人们秉持较为开放的学术态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尽管庄子思想的超越性不等同于开放性和包容性,但是它有利于打破那种绝对封闭和排他的思想倾向,后继者也更容易在此基础上阐发自己更为开放和包容的学术态度
。可以说,正是在庄子思想的启发下,中国传统的思想世界才有了一种别样的风貌。
在传统文化复兴的今天,人们对战国诸子之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在了解和学习诸子学说时,对那些独断性思想,我们需要警惕,而对庄子思想的反独断倾向,则要加以批判继承。
面对世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局面,我们应该少一点武断,少一点门户之见,用一种更加理性和开放的学术态度去看待古今中外的各家学说。(编辑:忆慈)
参考文献
1、(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
2、(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
3、崔大华:《庄子思想与道教的理论基础》,《哲学研究》1990年第5期。
4、崔大华:《庄学研究——中国哲学一个观念渊源的历史考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5、李霞:《庄子与禅宗的超越意识》,《中国哲学史》1993年第1期。
6、安继民:《简论庄子社会批判观的基本思路》,《中州学刊》1997年第6期。
7、麻天祥:《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8、张祥明:《宽容:庄子的认识论精神》,《齐鲁学刊》1998年第6期。
9、刘士林:《论庄子“三无”说及其与儒、墨、杨朱之关系》,《孔子研究》1999年第2期。
10、王晓毅:《阮籍与汉魏之际庄学》,《史学月刊》2004年第2期。
11、杜志强:《庄子认识论新探——兼论庄子认识论并非相对主义》,《甘肃理论学刊》2006年第1期。
12、刘固盛:《唐代重玄学派道论的特点》,《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13、徐莹:《庄子学说之独立性研究——以内七篇为中心》,《文史哲》2009年第6期。
14、张耀南:《中国哲学批评史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15、王斯斯:《庄子思想的内在超越性》,《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1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7、刘固盛、肖海燕、熊铁基:《中国庄学史》,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18、刘固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精神与现代启示》,《长安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19、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道化天下 世界玄同”有奖征文活动投票环节开始啦!
欢迎投下您尊贵的一票。投票以后,
移步评论区留言
,就有机会在投票结束后获得
精装版《白玉蟾真人全集》一套哦,快来吧!
点击文末
阅读原文
,更多精彩道学参赛文章等你哦。
(本文为“道化天下 世界玄同”道学全球有奖征文比赛作品,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文:王耀辉,文章原标题为《论庄子思想的反独断倾向——兼与战国诸子思想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