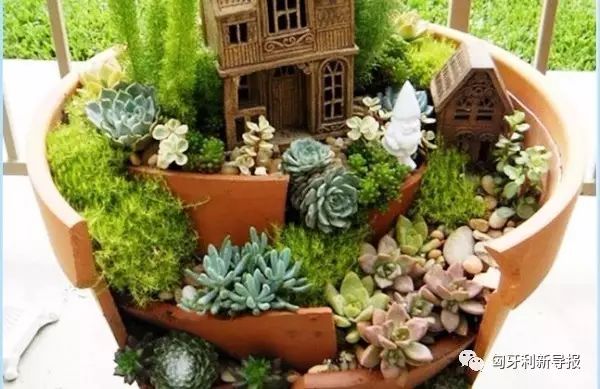2023年2月4日早上八点,飞机降落在浦东机场,十一个小时的长途飞行我一分钟都没有睡着,却丝毫不困。落地,过关,打车,一路不停息地抵达亚洲大厦的剧场,这场伦敦-上海千里飞行的终点。
四小时后我坐在剧场里,灯光暗下的瞬间我屏息,身边嘈嘈切切的声音突然安静,钢琴声响起,一束蓝光照射向舞台中间,人影带着手铐缓缓走出,这是中文音乐剧《危险游戏》在上海的封箱轮演出,我跨越千里也要看到的末场,也是我2022年以来观看的第11场《危险游戏》。散场后我穿过人群匆匆打车,去奔赴和好朋友的晚餐,因为三小时后我还要再回到亚洲大厦,继续观看另一场音乐剧《阿波罗尼亚》。
2023年这样极限的伦敦-上海往返飞行总计三次,在上海总计三周的时间里,我观看了14部35场音乐剧。在伦敦感到孤独、感到枯竭的时候,我就会给自己订下一场上海音乐剧的票,像骡子为自己寻找挂在眼前的胡萝卜走下去。
这种疯狂的狂热始于2021年末,常驻北京的我来到上海过圣诞。和话剧文化浓郁的北京不同,上海有它独特的音乐剧内容圈,沉浸式小剧场往往“足不出沪”。好奇心驱使下,我在大麦上购买了中文音乐剧《危险游戏》沉浸版的门票。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沉浸式小剧场,剧场甚至没有教室大,四面环形的座位席最多能容纳两三百人,中间凸起的舞台是水泥地质地,离最近的坐席触手可及。我带着困惑坐下,灯光暗下来,漆黑一片的剧场只能听见呼吸声,一束蓝光亮起,带着镣铐的演员缓缓走到舞台中央,极近极近的距离下甚至能看见演员眼睛里蓄着的泪。我不由自主屏住呼吸。当他开始缓缓讲述这个故事,当他开始歌唱,仿佛这个空间只剩下舞台与我。
这是一个情感浓度如此之高的故事,一个人唱着他跨越了三十年的爱与恨,激烈的爱欲与谋杀的快感交织,如此危险又如此华丽,而一旦想起这一切都已经是三十年前的旧事,斯人已逝,爱恨都再不可追,又是浓烈的悲伤。我好久好久没有过这种感受,感受力完全被打开,充分地、百分百地被情感裹挟其中。
这是一种纯粹感官的快乐,我曾经在追KPOP偶像的岁月里或多或少有过相似的感受。舞台上的偶像是情感的承载者,也是被投射方,当我被某首歌或者某个舞台打动,情感的联结也在这一瞬间建立。快乐也好,悲伤也好,偶像通过舞台或者综艺传达出的情感将我包裹,构成我贫瘠日常生活里的亮光,白天上班再烦躁再无聊,只要晚上回到家打开社交媒体看到新的现场视频,无限爱意和快乐就会蒸腾,洗去所有现实的烦恼。但这种联结通常单向度且容易枯竭,偶像毕竟本质是一种内容形态,且是一种很单薄的内容形态,当它能给予的所有情感能量都被消费殆尽,它能带来快乐也就逐渐消弭。
音乐剧是不一样的,现场,尤其是在这么小的剧场里,演员的情感表达被音乐无限度的放大回荡,那样充沛的情感能量大概可以与万人演唱会现场相比。剧本本身有多重被解读的空间,不同演员不同的理解与演绎,不同演员组合之间带来的差异性火花,甚至小剧场观众座位改变带来的不同视角都让它作为一种内容形态有了上限极高的丰富性。
那一场演出之后,我取消了第二天回北京的车票,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又看了10场不同卡司、不同座位视角的《危险游戏》。
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人生中很特别、很特别的一段时间。工作了四年的大厂要把我从北京调动到伦敦,机缘巧合之下我获得了两个半月的假期。是真正的悠长假期,没有工作烦恼,没有经济压力,也不用担心下一步去哪里,像是和现实隔绝的一种美梦泡泡里的生活。只是看到《危险游戏》的时候,我随心所欲随意挥洒的时间已经进入一个月倒计时:一个月之后,我需要飞往伦敦,开始全新的也是陌生的工作和生活。在一种像是末日狂欢一样的心情里,我改掉所有其他计划在上海停留了两周,只做一件事,看音乐剧。每天至少一部,情绪也跟随着观剧体验的好坏起起伏伏。像是燃烧一切的渴望与狂热,生活中的其他所有感受都暗淡甚至被略过,只有走进剧场的时候心脏仿佛才开始跳动。
那时候真的想过,是不是就这样留在上海。但从既定的轨道抽离需要很大很大的决心和勇气,而那一向是我缺少的东西。2022年2月,我还是如期飞往了伦敦,带着对被迫抽离的音乐剧的快乐的无限留恋。
那时候我想,没关系吧,伦敦也有很多音乐剧,还有很多可以期待。
我记得抵达的伦敦的第一天,疫情的萧条仍然弥漫在欧洲大地。下午两点,哥本哈根转机休息室外的天光暗淡灰沉,我走到饮水机前接水,面目严肃的机场工作人员走过来拦下我,她说出于Covid安全考虑,我不能直接用自己的杯子对饮水机的出水口,我愣了愣,一下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
到达伦敦的时候是傍晚,但天已深黑。第一次在机场碰到Uber打不车情况的我决定坐地铁,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不是所有的伦敦地铁站都有电梯。我拎着两个行李箱,在两个换乘站爬上爬下艰难地爬到站台上,百年历史的Piccadilly Line的轨道黑黢黢,一眼看不到头。Google导航的路线穿过泰晤士河岸,穿过Covent Garden狭窄的街巷,上坡下坡,两边优雅的英伦建筑在夜色里闪烁着黄色灯光,河对岸的National Theatre招牌明亮,映衬着伦敦眼和远处的城市亮光,很美丽,但我只顾得上吃力地拖着行李箱,数着还有多久才能到。
而那只是第一天,以后每一天的挣扎都只更甚。找房、办银行卡、搬家,这些让人晕头转向的课题先不提,“今天吃什么”就已经足够难倒在国内从来不做饭的我。社会规范、生活秩序、语言环境每一件事都让人焦虑,我从轨道上掉落,想把自己拉回那个至少可以匀速前进的生活能量系统,却毫无头绪。
我想到上海剧场里充盈的巨大的能量与快乐,选择诉诸音乐剧。在伦敦第一周,我去看了三场剧,《歌剧魅影》,《Six》,《Witness for prosecution》,但大概是语言和文化差异带来感受的开关不同,我再也没有获得那种被情感包裹的快乐。走出剧场的我无法停止地开始想念上海,人民广场附近的剧场永远充满熙熙攘攘的人流和明亮的黄色灯光,快乐又充满活力。走进剧场的快乐是确定性的,不用为哪里买票、剧院进场分区担忧,不用分神理解这段在说什么,为什么旁边的人都在笑。
不要误会,西区的戏剧质量当然是世界一流水准,但是它在我熟悉的世界之外,令我焦虑和摸不着头脑。就像在伦敦的新工作。在北京的时候我做着和业务密切配合的分析工作,一切都清晰明确有反馈,互联网大厂的工作节奏固然十点前下班是不可能的,但我有已经成为好朋友的同事,打工累了去买咖啡、楼下遛弯、晚上下班去半夜的711买零食,这么多年下来早已习惯这种苦中作乐的生活。
伦敦的工作变成虚无的行业研究,我找不到标准也找不到入手点。疫情间大家一周只用去一天Office,在家工作的时间没有边界,没有同伴,就像当年刚刚结束小镇高中早7晚10的生活进入大学,我无法与这些空白的时间好好相处,无法心安理得的做其他自己的事,也无法好好专心做找不到头绪的工作。最焦虑的状态其实是想躺躺不下,想卷也卷不了的45度状态。
在这种糟糕的状态里煎熬了三个月,我迎来了职场生涯的巨大转折点。那天我在办公室对着空白的文档发着呆,忽然收到直属上级给我发来消息约我现在聊聊,我心中一紧,心想是不是最近产出太低要被说了,但又像偷糖吃的小孩终于被抓住,那一瞬间甚至有点释然的平静。
这是我跟随了两年的老板,我是她招聘的第一个人,她把我从北京调动到伦敦,然后现在她告诉我她要被调动去美国了,我的汇报线会调整给原本平级的一个法国同事,他会成为我们团队新的leader。
一周之后,我和新的老板第一次视频1:1,网络信号很差磕磕绊绊,就像两个非英语母语的人的对话。又过了一个月,他再次约我1:1,这次10分钟就快速结束,他告知我,因为新的架构调整,他希望我可以汇报给我目前的平级同事,从他的-1变成-2。
如果现在问我,当时为什么不立刻开始找工作,我好像能找到很多理由,但好像又一个都站不住脚。我已经在这个职位做了两年,理论上是升职的窗口期,离开大概一切都要从头来过。毫无成就的工作和社交圈,让我对在英国找工作不抱希望,但海的那头正经历最严格的封控。
我好像被困在了原地,无法移动。离开上海之后,我的微博置顶一直是离开前最后一晚拍摄的亚洲大厦剧场门口的照片,温暖的黄色灯光,巨大明亮的音乐剧海报,熙熙攘攘的车流和剧场门口队伍排到马路上的等待演员签名交流的人群,那是我没办法停止想念的美梦结界。在伦敦孤独找不到意义的生活里,我反反复复地在这条微博下写下想看的剧目清单,直到上海封城的开始,我才意识到,那种明亮的不带一丝杂质的纯粹快乐大概再也不会回来。
我取消了那条微博的置顶。
我记得如此清楚,22年12月,逐渐传出国内对境外航班不再强制隔离的消息,1月8日,靴子落地,延续了三年的隔离政策被正式取消。2月3日,我拿到伦敦的外派还可以再延期一年的确认,立刻请假订了第二天的机票飞回上海。
就这样,2月5日,我终于又坐在了我最爱的的剧场,还未开场,熟悉的温暖的黄色灯光落下的时候我已经几乎要落泪。在伦敦半窒息半麻木的生活里,我最想念的就是剧场,直接的、浓烈的高强度的情感冲击,那样真实而纯粹的快乐,在远离它也找不到替代品的日子里,生活就像蒙上一层布,一切都雾蒙蒙的。坐在剧场里的时候渴望终于把这层布燃烧殆尽,我终于能直接触碰到他人的情感、真实的生活质地。
最爱的歌曲响起的时候,我哭了出来,剧中的女主角被爱人抛弃,对生活失去了一切希望,父亲的召唤是来自过去的,熟悉而平静的生活的召唤。我想到离开之前在伦敦的圣诞假,朋友们都离开了伦敦,我在loft躺着,看着一线光从遮光窗帘里漏进来又暗下去,耳边除了对面医院尖锐的救护车声什么都没有,无休无止的孤独让人发疯。
我想到在英国无法找到任何成就感和方法论的工作,失败的presentation对面听众游移的眼神下沉的嘴角。这次飞回来之前我其实终于下定决心要开始找工作,但拿到的Offer在最后一刻被HR告知伦敦的headcount冻结。在上海的这几天我收到当时的面试官的消息,表示国内仍然有headcount,询问是否愿意回国,我没有犹豫,告诉他我已经决定留在伦敦继续外派一年。
伦敦的生活其实没有那么糟,我搬到好朋友居住的公寓旁边,新家有漂亮的三面落地窗,可以远眺Canary Wharf闪烁的城市灯火。离开优雅但冷寂的西伦敦,我终于感受到了一点城市烟火气。依赖着在上海的一周储存的快乐,我开始有一点点能量装饰新家、探索附近,慢慢建立生活秩序;我去打拳、去游泳,开始感受到身体对“好”的生活的渴望的复苏。
随之而来的就是精神力量的复苏,我去看KPOP演唱会,两周去一次剧场,逐渐意识到西区剧场的美更多是在于话剧,比如《雷曼兄弟三部曲》,比如《欲望号街车》,精炼的文本与精湛的表演,抛开那种对情感浓度的期待之后,我也可以在伦敦获得剧场的快乐。除了找工作仍然像被诅咒了一样总是在最后一步出差错,这种生活有时候甚至让我有一种岁月静好的错觉。
但这种平静与快乐,都是建立在对下一次回上海看剧的期待之上。回伦敦之前我就早早订好了复活节回上海的机票,完全跟着想看的剧目的上演时间和地点来,其中我最想看的一部,于2022年10月末第一次在上海首演,中文音乐剧《卡拉马佐夫兄弟》。
如果说2月的上海仍然让人感到萧条,那4月的上海则有一种报复性的繁荣,春天终于到来不管不顾燃烧盛放的繁华,浦东机场大门紧闭了三年的免税店终于打开了,亚洲大厦门口关门的茶餐厅被新的剧场取代,招牌明亮,静安寺门口的队伍排成长龙,对面静安公园的花树灿烂,树下是快乐跳舞的人群。是我睽违已久的城市的生命力,就像过去的一年什么也没有发生,我给即将从北京飞来和我一起看剧的好朋友发消息:我在最快乐的时候离开的那个2022年的春天,它又回来了。
演出结束之后我和好朋友一起去吃烤鸟,喝酒,散漫地聊我们最近在上海看的这些剧,我还沉浸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巨大的冲击里不能自拔, 拉着好朋友喋喋不休,一个晚上大概说完了在伦敦一周要说的话。我们走过夜色中的上海大剧院,宽阔的柏油马路两边高大的绿树在晚风里轻轻摇动,映照着剧院明亮的建筑和远处淮海路的灯影,美丽的不可思议。2022年的春天之后,我以为那些精致的美好的东西会被摧毁不再回,但眼前的这个春天,它似乎精致美好更甚从前。那一刻,我是如此想留在这里。
最爱最爱音乐剧的时候,被困在伦敦看不到那些心心念念的剧目的时候,我曾经不断地后悔,为什么没有早点离开北京去上海。2020、2021年我都接到过上海工作的offer,但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拒绝。我一一历数当时的上海上演的剧目,描摹着一个不可能存在的时空,一个和北京毫无美感的生活截然不同的时空。但是人是如此容易陷于惯性的生物,我花了接近八年的时间,才能下定决心离开北京。伦敦是不快乐,但仍然是一种60分过的下去的生活,我难以决断。
我回到了那种60分的生活中,没有糟糕到我必须要马上离开,但能量也就刚刚好应付日常生活,麻木是更通常的生活感受。
新的组没有想象中糟糕,做的事情是我更擅长更熟悉的,而且是业务方主动要我过去,让我已经万分脆弱的自尊心感到好受了一点。我开始读心理学,试图理解自己,从从前那个给自己设定的应然的世界里走出来。小镇做题家的世界里不努力、不优秀好像是一种“不应该”,空白的无所事事的时间也是一种“不应该”,但现在当最坏的结果已经发生,我必须要开始正视这种“不应该”,承认它们存在即合理。而当我终于可以坦然地面对真实的自己和时间,生活好像变得容易起来。
我也逐渐习惯了八点起床,九点开始工作,六点之后再也不看工作软件的生活,甚至在偶尔加班到八点半下班的时候觉得真是太晚了。我开始理解自己的能量系统,接受自己就是一个月会需要有一天谁也不见什么也不干躺着不动的断电日的事实,接受自己枯竭几天之后就会慢慢好起来,从渴望运动再到渴望精神生活。有一个五月的周末我在清晨醒来,突然觉得充满能量,我梳洗出门,沿着河一路走到Tate Modern, 在明亮的咖啡厅点了一杯咖啡和蛋挞,是我在伦敦吃过的最香甜的蛋挞,之后在伦敦难得的阳光下漫步到Borough Market买调味料和肉,回家煮腌笃鲜。这是在北京的我从未想象的生活,它的吸引力在慢慢浮现,偶尔,要不要就这样留在伦敦的闪念也会出现。
但这种闪念也总是被一些消失的快递、消失的地铁和消失的政府缴费工作人员打消。而且在大多数时候,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上海。
这种平静没有波澜的生活里,我最想念最想念的音乐剧叫《粉丝来信》,它关于文学理想,关于被时代压抑的文人的表达与反抗,是我所有的精神母题里最痛也感触最深的一个。在伦敦空洞的日子里,我反复播放其中的一首歌,《无人知晓》,我想起在伦敦的生活,越过了那些生活的基本困难之后,最痛苦的其实是所有的悲伤也好快乐也好,都无人分享、无人知晓。就像我没办法和任何一个在伦敦认识的朋友解释这种对音乐剧发疯一样的狂热,解释背后的那些爱与痛,本地朋友觉得音乐剧是四五十岁中老年人的爱好,华人朋友总有别的更关心的话题,我们聊吃喝玩乐欧洲旅游,从来不谈书籍电影,不谈为什么与对与错。
这种空荡荡的时候,我就打开大麦看接下来上海上演的剧目,给自己订票,获得继续过下一天的动力。陆陆续续攒了十几张音乐剧的门票之后,七月末,我又坐上了回上海的飞机。在那种燃烧一切的渴望的狂热里,看剧的花销、请假的麻烦都显得毫不重要。音乐剧是一种解药,我那岌岌可危的生活能量储蓄罐见底的时候,我就迫切地需要它为我充电。
但解药也有不灵的时候,这次我带着对诸多新剧目的期待而来,走出剧场的大部分时候,却觉得平静甚至遗憾,少有那些被快乐或者情感包裹的时分。《阴天》,《莎士比亚的罗朱》是关于自由追寻与自我表达的题材,此前演出的时候颇有好评,这一次我却遇上了删改版本,灵感迸发的瞬间都被改写,成为俗套故事。《人间失格》是此前颇为期待的中文原创音乐剧大制作,确实气势恢宏,弦乐器乐轰鸣在耳边的时候甚至让人落下生理性泪水,但它让我幻视西区那些我熟悉也厌倦的大剧场音乐剧,曲折剧本大气舞美之下,是平直而空洞的情感。
我想,是不是到时候了,音乐剧能够点燃我,给予我能量的瞬间大概也是有限供应,当情感阈值被提高或者情感主题不再能百分百契合,解药也会失灵。
回到伦敦之后不久,HR约我谈话,告诉我外派在明年二月到期后不会再续,我需要考虑回国,并给我推荐了国内的团队,告诉我这个团队虽然在北京,但可以允许我一个人base在上海。就这样,伦敦还是上海的选择比我料想得早得多的来到了。
那段时间我其实在工作上已经非常得心应手,比从前在北京十二点上班凌晨下班健康得多的作息,相似的成就感。在伦敦的生活秩序也趋近稳态,做饭、健身、购物都有了固定频率,有了固定的饭搭子和就住在隔壁想聊天发条消息就可以去她家坐下的朋友。甚至看剧的运气也大大地好了起来,《死亡笔记》,《Next to normal》,《Sunset Boulevard》,我逐渐习得了怎么挑选西区我应该会喜欢的剧,也开始在剧场中感受到那种被情感浓度包裹的快乐。是一种进入了舒适区的生活状态。我不由得想到22年的1月,好像每一次,当我开始喜欢一种生活,我就要离开它了。
但是好像也没有别的选择,10月初我决定开始在英国投简历,几十封投递出去,三周过去一点回音也没有。我决定11月先回国出差一个月,感受一下新组的工作。
在北京的三周,我每天7点就穿过热火朝天工作的人群离开办公室,回到酒店开始准备面试——非常离奇地,在我即将飞往北京的时候,之前投递简历的回应一个个的都来了。最疯狂的时候我一个晚上面了三个公司,回答了三遍的behavioral question的答案甚至梦里都在脑子里回荡。
到12月初回到伦敦的时候,我已经完成了3家公司的终面,2个外部公司,1个内部转岗。我当时意气风发,挫折已久的职业自信好像终于回来了。我还记得是在12月中,我去伦敦我最喜欢的剧院之一Almeida Theatre看《Cold War》,讲述一对波兰音乐家情侣在冷战前后的畸零人生,其实是话剧,但是有大量的音乐穿插其中,澎湃的情感扑面而来,是我最喜欢的那种剧。
我在中场休息时打开手机,看到内部转岗的HR发来消息约我聊一聊,下半场结束我急匆匆冲出去打上车开始和她打电话,她给出了一个我无法拒绝的offer,我可以维持目前在伦敦的生活水平,同时相对频繁地回上海出差,这是我所有设想的情景中最完美的一种解法,同时兼顾伦敦我无法舍弃的生活和上海看剧的快乐。我在公寓楼下打完电话,像是烟花在心里炸开一样快乐,恨不得围着公寓跑两圈。我立刻给我目前的HR发去了消息说明了我的转岗意向。
两天之后,其中一个外部公司给我打来电话拒绝了我。晚上我给内部HR发去消息,问她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处理签证,聊天软件上一直显示“typing”,过了一会儿,也可能是很久,她告诉我,由于一些内部决策变化,他们最后决定撤回offer选择另一位候选人。我的完美选择就这样突然消失了。
那时候我还剩下最后一个外部公司的offer,是我很喜欢的团队和方向,但是需要我降薪。
在巨大的愤怒和失望之下,人会生出比平时更多的能量。失眠了一个夜晚之后,第二天我独自在伦敦游荡了一天,去看电影,去逛街,买了香薰蜡烛,晚上在温柔的玫瑰花香里盖着毯子在沙发上看了通宵的古偶,第二天又买了桂花和米粉开始做桂花糕。好像想用行动来给自己证明伦敦仍然是我可以生活的城市。
一周后,我给最后一家公司的HR打了电话接受了offer,这就意味着,我将继续留在伦敦。
从那时候到现在,其实也只过去了一个多月,但感觉像是一年那么漫长。我处理掉过去五年工作上累积的工作材料,出于未来通勤的考虑从东伦敦又搬到了西伦敦,开始研究也许能让我在英国更快获得永居的签证。这些两年前搬来伦敦时让我焦虑万分的冗长又琐碎的事务,现在反而让我觉得充实而平静。当然也会有受挫的时候,消失的快递,消失的地铁和消失的政府工作人员并不会因为我心态的改变就突然出现,我也常常会想,如果当时回了上海,是不是这些烦恼都不会有,但我也知道这样的what if, 如果我回到上海也会一样出现。
11月回北京出差的时候,我在万般忙碌之中极限找了一个周末去上海,看了我的最后一场《粉丝来信》,它仍然美丽的不可思议。当微岚把曾经用来写作的笔刺进手心,杀死在绝望的时候拯救他的“光”,当海鸣写下临死前的书信,“在文字围起的城墙里,守护这个梦境。”,当一切都过去,微岚在海鸣的追悼会上含泪说出:“海鸣先生于我,就像春天一般”。我的眼泪也控制不住地流下。
这段流离迷茫的时间里,音乐剧于我,也像春天一样。而现在,我要和这段春天说再见了。
本故事由短故事Life Writing学院导师指导完成。
4月 “短故事”报名中
,
邀请你来写下属于自己的个人故事。
“短故事Life Writing学院”
4月报名中!
4月16号-
29号,
新一期短故事Life Writing学院
即将开始,
我们希望用14天时间帮助你寻找并写出自己的故事,资深编辑将和你一对一交流沟通,
挖掘被忽略的感受和故事,探寻背后的人文意义和公共价值。让你的个体经历与声音通过你自己的独特表达,被更多人听见和看见。
►在活动开始之前,如退费,需扣除 10% 的手续费
►
作品如获三明治头条发布,可半价参与一期短故事,累积发布5期头条,可免费参与一期短故事。以上作者激励请在6个月内使用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