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特·尼尔逊,
1943
年出生,美国当代作家。生于辛辛那提,毕业于耶鲁大学政治学系。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冷风河》
(1981)
、《周围静悄悄》
(1989)
、《血中语言》
(1991)
,短篇小说集《网球手》
(1977)
、《无处之中》
(1991)
。肯特·尼尔逊曾获得“爱德华·艾比生态小说奖”,他的短篇作品曾入选《美国最佳短篇小说》。
在《不合常规的飞翔》里,作者给人类的自然属性——性爱,找到了一个最恰当的发生地——美丽的大自然。
肯特·尼尔逊作
韦清琦
译
克莱尔听说了洛杉矶鸟类监视录像带上发现了那只游鸟,并在图森打电话给我。她早先在实验室开会无法脱身,但五点时到印第奥的邮局和我碰了头。我到达时她正坐在她那辆“陆虎”越野车的阴影里,身着短裤和宽松的咔叽布衬衫,足蹬旅行靴。上次见面后她把头发剪了,看起来也苗条了些,似乎一直在锻炼。不过她起身时给我的最初印象并非她的外貌,而是别的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她慢慢地直起身子的样子,她偏开脑袋,眼睛避开目光的样子使她显得更年轻,更有耐心,而且更具威胁性。“坐我的车,”她说。“天色暗得很快,所以我们得赶紧。”

我从自己的花冠牌汽车里取出双筒望远镜、潜望镜和小旅行包。克莱尔打开“陆虎”的后舱,我把东西丢进去,它们挨着冷却器和克莱尔的野营用具。“鸟是谁发现的?”我问。
“斯特拉琛·多内利。”
“你觉得可靠么?”
“百分之百。”
“你也知道方向?”
“录像带上有。北岸,萨尔顿海。”
“海燕哪儿都会有。”
“说不定已经飞走了。”
我们钻进“陆虎”,克莱尔发动了引擎,我们向南驶去。我摇下窗玻璃,让微风吹进来。
很难说清我和克莱尔交往的历史。在图森相识时她已经结婚了,我从没见过她丈夫。她是生物学家,体态略胖,深色头发。有一年多时间我们合开一辆车去我们工作的研究所——跑一趟要二十分钟。我们主要谈正在进行的项目,就是研究政府在西南部的核实验区里核辐射对动植物群的影响。我们的关系是职业性的:她从未问过我私人的问题,也只字不提她自己的家事。同时,也许因为没别的人吧,我也把她当作朋友。我感受着她的情绪——我们下午开车回来时她的注意力是如何更加集中的,某一天她是如何意识到起北风了;或者有时候我感觉到她隐隐的火气,好像她知道自己并不开心。
可她对我一无所知。我孑然一身。小时候父亲就过世了,而母亲倒也没受多少打击,并搬回东部住在新英格兰。我不善交际。当然我上过大学,读了化学专业的研究生,但从来就没有和别人待在一块儿的需要。我没有任何的期待或愿望。可我在这样的孤寂中仍安之若素。我不要人作伴。我喜欢我的工作,也为鸟类所着迷,还津津有味地关注着世界上发生的别的事情。
我有严重的失眠,为了好过一些我就常常整夜看国际新闻。我看见了卢旺达的屠杀,或是一个人走在月球上,或是炸弹落进了伊拉克的一幢房子里,这些都让我激动不已,并非为这些事情本身,而是为它们的广泛性——我能同时知道所有地方的所有事情。
我是偶然发现克莱尔爱鸟的。有一天我们几个人到一座导弹试射场去作实情调查。共有六人,我开车。半路上,我瞧见一只鸟低飞在河岸的灌木丛上方。我没能看清楚——只是一块模糊不清的灰色——但我明白那是一种猛禽,比红隼大些。我放慢速度,跟随着它的飞翔,克莱尔在后座上说:“密西西比鸢。”
我把车开到路边停下。“你肯定么?”
“是一只鸢,没有盘旋着飞,而且还有黑尾。”
我用双筒望远镜瞄着车窗外,看见了一只鸢长而尖的翅,以及克莱尔注意到的那水平伸展的黑色尾部。她的精确观察使我大为惊讶,她总能在这么局促的时间看到这么多的东西,而且居然一直向我瞒着爱鸟这个秘密。
“好啦,斯雷特,继续开吧,”一个同事说。“我们想快去快回呢。”
以后在上班的路上我们就谈鸟。克莱尔曾为追寻珍禽异鸟走了不少地方——去过阿拉斯加、南得克萨斯,以及东西海岸附近的岛屿。她的知识比我广博。她懂生物学,知道鸟儿的求爱仪式、在田野里留的记号、食物源、栖息地和分布区的重叠处,比起她,我只是个业余爱好者。

日子长了,上班的路程似乎反倒短了。我从中获得的鸟类知识,克莱尔去过的地方,她野外生活的具体情况都让我吃惊不已。比如我发现她曾花了一个星期独自待在白令海的一座岛上,研究北极狐和三趾鸥的筑巢习性。狐狸是被引进来捕杀烦扰阿留申人的啮齿目动物的,可一旦后者销声匿迹了,狐狸便开始捕食鸟类。鸟儿就进化出一种保护幼雏的办法。当狐狸出现时,鸟儿便从筑在悬崖边上的巢里飞出来,狐狸发现被遗弃的小鸟,就禁不住诱惑来到陡峭的地段上。看它走得足够远了,鸟儿就猛扑下来,打得它坠下峭壁,落入离崖顶一百英尺的水里。使我感兴趣的倒不是三趾鸥的行为,而是克莱尔做的研究。她有去那儿的欲望,有忍受刺骨的海风和崎岖的地形的耐心和毅力,还这么津津有味地诉说这段经历。
我的生活渐渐有了变化。夜里睡眠改善了,也因为如此,我不再从头到尾地看时事节目了,尽管仍对其很着迷。到了周末我就驾车去城市以南的山谷,那里终年流淌的溪水为鸟类营造了理想的居处。我在那儿宿营,一大清早就醒来,聆听硫磺色肚皮的鹟、格雷斯刺嘴莺以及飞得更高的棕红色唐纳雀的鸣唱。
然后在春天一次回来的路上,当我们停在十字路口等待路灯时,她扭头看了看驾驶座前的我。外面很热,而我俩都不喜欢空调,所以车窗是开着的。我的左胳膊松弛地搭在窗边。她的表情呈现出一种我从没见过的柔和——还有些愁苦。
“我丈夫晋升了,”她说。“我们要搬到洛杉矶去了。”
我听到了这些话,但并不相信。绿灯亮了。我加速穿过十字路口。各种颜色在我周围的空气中漫溢。我闻到了尾气的味道。这是我第一次得悉了一些她的私人生活,我还有点想问她——那你的工作呢?你怎能离得开沙漠?这是你所希望的么?可我什么也没问。
我们追踪的鸟是科克海燕,一般筑巢于新西兰附近的岛屿。它个头不大——从头到尾十三英寸——一个黑色的
M
形图案伸展在它灰色的羽翼及背上。科克和其他爱忙碌的海燕品种一样,除繁殖季节外都在海上度过一生。它在飞行中捕食,极少落在水面上,漫无目的地遨游于整个太平洋水域。它在加州海岸附近出没的情况很不确定。人们每年在远洋航行时能拍摄到零星的几只,但从没有人在内陆看到过,就是在萨尔顿海也不见其踪迹。
我们沿从印第奥到麦嘉的主路行驶,经过了十几个身穿红色、黄色及蓝色衬衫或裙子,锄着莴苣的季节工,还掠过一丛丛枣椰树和橘树。西边十英里远的地方是光秃秃的圣罗莎山脉,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无精打采;东南方向则有奥罗科比亚山脉和巧克力山脉,它们勾勒出的锯齿状地平线成为这一河谷的背景。我不知道对克莱尔说什么。她的离我而去——那是我所感受到的——使我有点怕她。

我们缓慢地穿行在麦嘉镇上,那儿有几座颜色柔和的建筑,大都已破败了——一家杂货店、一座加油站和一间餐厅。这些建筑和车房上都搭着爬满了九重葛的棚架,空水果箱高高地堆在满是灰尘的院子里。在小镇南端,克莱尔开上了一条没有标识的土路,我们越过了一条灌溉渠。她递给我一张纸。“你报路线。”她说。
我大声念着方向。“我们沿这条路一直开到下一座桥,”我说。“离那儿不远的地方有座土砖房。我们到那儿向左拐,朝海的方向开。”我透过车窗看看笼罩着群山的暮色。看不见海——只有海水肯定覆盖过的无树的空地以及辽阔的天空。
“工作怎么样?”克莱尔问。
“还行。”
“没什么新发现?”
“我们在卡韦萨
·
普里塔发现了污染物质。”我说。
“你们早就知道那儿有的。”
“但即使有证据,政府也不可能让我们公布的。他们为这项研究付钱,再把结果隐瞒起来。”
“别那么愤世嫉俗。”克莱尔说。
“有什么不好?”
我们车后的土路上扬起了灰尘,而前方那座小钢铁桥出现了。我们当啷当啷地驶过去,接着就沿一排破旧的栅栏奔驰起来。微风中传来浓郁的橘花香。我们超过一辆在路上抛锚的“福特”,然后开到那座土砖房前,一条狭窄的小径出现在左首。路两边都是牧豆树丛,克莱尔驾着“陆虎”穿行于其间。
我们开过了一座几近干涸的盐碱池塘,四只黑颈长脚鹬将其细长的喙伸进浮藻中。几只唧唧鹬飞起来,并在运河上方打了个旋,而当我们快到池塘尽头时长脚鹬也飞起来,盘旋着向西飞去,那儿的群山已成为朦胧的深蓝色。我们爬上一座低矮的山丘——约十英尺——然后海就呈现在眼前,那是一大片蓝灰色的光泽面,其上既无风也无阳光。高高飘浮在山上的白色卷云倒映在水里。
当克莱尔离开图森时,我在试验室里感到了孤独。我带着报复心理躲进了自己的研究中,可我明白我的工作做得很糟。我就像音乐家,虽然有才华,却无法经受情感上的风险,而赋予音乐以生气的正是那种风险。谁在乎基因的染色图多年前就因沙漠核试验而发生了改变?谁又关心地下水的放射性已足以使蜥蜴生病?
到了周末我去沙漠而不是进山。我在长着墨西哥三齿拉瑞阿的平地上或者在假紫荆属树木的树阴下找干枯的沼泽地边缘安营扎寨。我坐着晒太阳,仿佛要让沙漠侵蚀掉我整个身与心。夜晚我就倾听埃尔夫猫头鹰刺耳的笑声,它们在奚落我沉迷于世间的虚荣,而波尔威尔鸟轻柔的鸣叫又让我低声饮泣。
萨尔顿海位于几千万年前的造山运动所形成的盆地中。科罗拉多河曾在加州湾即这个盆地的南端被淤塞,并改河道向东,留下了一座无水的河谷。
19
世纪初,美国陆军工程部队决定修筑运河,以灌溉帝国河谷,但他们犯了计算错误,这是政府所作所为的典型(就像他们在所有导弹发射场里干的那样)。河水有一年在春汛时冲出了一条新水道,并注入尚未完工的运河,而在接下来的十八个月里全部河水都倾泻在萨尔顿盆地里。一片海域就此降生。
“这里是目击那只鸟的地方,”克莱尔说。“是从这儿的沙滩上看到的。”
她朝前驶向灰色沙地狭长的一角,与之接壤的两边都长满了繁茂的萨尔提略树。我们下了车,用望远镜很快地扫视着海面。野鸭和䴙䴘在附近的水面上浮游,几只海鸥盘旋在我们头上。一行黑鸬鹚排成纵列朝南向远岸飞去。
“再远处是什么?”我问。
“燕鸥,基本上都是。普通的燕鸥,还有一只黑色剪嘴鸥。咱们用高倍望远镜看。”
我们在沙滩后的土丘上支起三脚架和高倍望远镜。我的望远镜是科斯塔牌的,有高达四十倍的分辨率,透过它,那些在远处水面上飞翔的、不易辨认的鸟就成了克莱尔所说的:一群普通燕鸥,两只黑色剪嘴鸥,一群红褐色短颈野鸭。三只白面鹮在越发暗淡的群山的映衬下如同飞翔的剪影。
“我看不出什么反常情况,”克莱尔说。“你呢?”
“问题是现在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其他鸟。”
“但海燕飞行时的那种跳跃式的弧线是可以辨认的。”
我看不见跳跃式的弧线。太阳从高空云层里消失了,没有了那折射出的白光,海上的光线便消退成凝重的灰色。我不再扫描水面,走下去来到海岸线上,海水的咸味刺激着鼻孔。我跪下来将手放进水里。水和空气一样温热,我脱掉鞋袜——我已经穿短裤了——围绕沙滩边的萨尔提略树趟着水。
运河入海口的另一头是个爱尔兰松糕状的小水弯,里面满是泡死的树木。那儿以前肯定是一片海滨林地,在它被改造为橘园之前,在运河带来废弃的化学物质之前,在那次泛滥之前。水很浅,海藻使其表面平静光滑,也不见怎么流动。树上的黑色枝桠似蜘蛛网一样向空中伸展,苍鹭和白鹭栖息在上面,如同巨大而怪诞的浅色树叶。我感到仿佛走进了一个已被毁灭的世界。
是克莱尔使我以这样的眼光看这地方的,尽管我责怪着自己。我创造了此刻的我,这个孤独的人。我让自己受着那么多事情的烦扰:开车去上下班时的含糊的谈话;我希望获得的她的鸟类知识;我愚蠢地以为对她有所了解。还有,自己如此软弱,以至于和她在此见面……

一时间里,我想到此刻马来西亚准是在地震,或者法国的火车出了事,要么是埃塞俄比亚的儿童正在挨饿。可是我所清楚的只有眼前这个世界——小水湾和远岸上黑暗的沙滩,除此之外,还有枣椰树在荒山的映衬下摇动着尖利的枝叶。
“斯雷特?”
“在这儿呢。”我说。我扭过头,但透过萨尔提略树没看见她。
“向西看,飞得很低。”
“在哪儿?”
“九十度角附近。”
我涉到较浅的地方,避开灌木丛,举起望远镜。黑色的鸟儿在水面上展翅飞翔。
“我看见的那只鸟你看见了吗?”克莱尔说。
“不知道。”
我绕过灌木来到她所在的地点,她从高倍望远镜前直起身。“有可能有可能,”她说。“但光线暗得无法确定任何东西。”
“但有可能是的吧?”
“是什么都可能,”她说。她抬起高倍镜,折起三脚架,将它靠在“陆虎”的挡泥板上。“饿了么?”
她的语调让我意外,还有她这么轻易地放走了那只鸟儿。
她绕到“陆虎”的后面,掀起车后门。“我准备了火腿乳酪三明治、土豆沙拉,还有啤酒。”
我本来没顾得上肚子,但我的确饿了。我拿了一块三明治和一罐啤酒。
克莱尔钻到长得更高的灌木丛里去方便,我则爬上“陆虎”的前盖,将背靠在挡风玻璃上。啤酒是冰的。苍白的海、徐徐的微风以及波浪柔和的拍击使我懒洋洋的,几乎昏昏欲睡。我闭上眼,听着虫子嗡嗡的鸣叫。
我肯定打了会儿盹,因为我再次睁开眼时已是夜晚了。我看见远处的群星中一架飞机闪烁的红灯。克莱尔在我旁边,靠着挡泥板,但在黑暗中我无法看清她。
“你爱我么?”她问。
她的嗓音让我惊讶。“你已结婚了,”我说。
“这算回答?”
“不是么?”
“在一起相处了那么长时间,你从没有给我打过电话。”
“你也没给我打过。”
“我今天打了。我使劲儿想有什么能让你见我。”她停了一会儿。“你有什么感觉,斯雷特?你从来没感觉到什么?”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于是我扭头去看海,远方小镇上的灯光在黑色的海岸上闪烁。
“你没必要扭过头去,”她说。
她绕到“陆虎”前面,站到了保险杠上,让我没法不看见她。她解开衬衫的扣子,提起衣角,如展翅一般。她的皮肤在温热的空气中显得很白皙,发着亮光。我不明白是什么给她勇气来这样冒险。她一定是厌倦了终日的工作,于是从洛杉矶驱车穿过酷热摸到了我们所在的这片沙滩。而她还能唤起我从没想象过的那种欲望。她脱去衬衣,挨着我跪在车前盖上。
“能看见我吗?”她问。
“能。”
“那?”
我没有回答,于是她俯身向前,将手伸进我的短裤,触摸我。
“没问题吧?”
我周围的一切都化作一种知觉。我站在悬崖的边上,同时怀着失足落下的恐惧和愿望。我去抓她的手,将它推开。
“别拦我。”她说。
她松开我短裤上的纽扣,把短裤拉下来。我没有反抗。我感觉着潮湿的、流动的空气,还有她的再次抚摸,平生第一次感觉到了欲望的那种奇异的无助。我们就在“陆虎”的车前盖上度过了这个夜晚,轻柔的空气如水一般在我们身上流动。黎明时分,我们穿好衣服,用野营炉烧水煮咖啡,又在沙滩上巡视起来。我们用高倍望远镜来来回回地扫描着,追踪着那只也许并不存在的海燕的不合常规的飞翔。
原载于《世界文学》2003年第3期
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经公众号责编授权。
相关阅读:
小说欣赏|尤•海尔曼【德国】:蓉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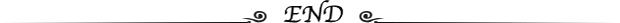
《世界文学》征订方式
订阅零售
全国各地邮局
银行汇款
户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开户行:工行北京北太平庄支行
账号:0200010019200365434
微店订阅

★ 备注:请在汇款留言栏注明刊名、订期、数量,并写明收件人姓名、详细地址、邮编、联系方式,或者可以致电我们进行信息登记。
订阅热线
:010-59366555
订阅微信:
15011339853
订阅 QQ:
3076719982
征订邮箱:
[email protected]
投稿及联系邮箱:
[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