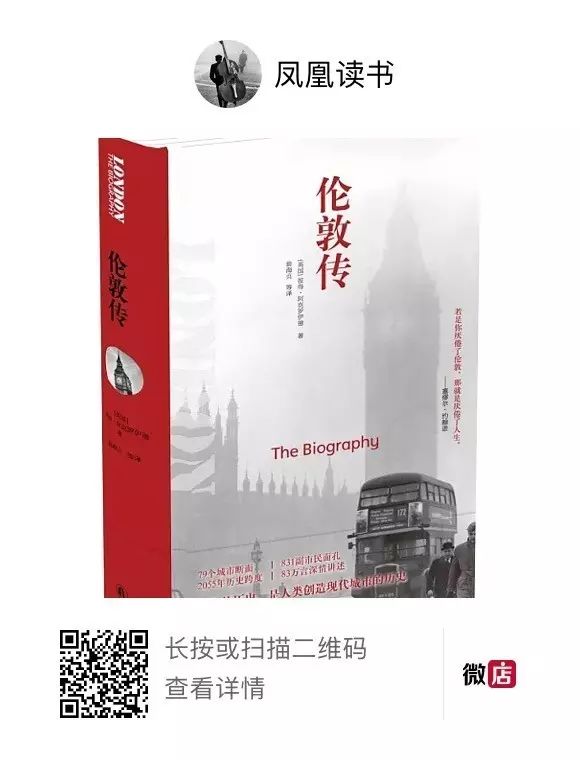文 | 彼得·阿克罗伊德
伦敦是一座万劫不复的城市。这座城市一向被视为先知们所痛斥的耶路撒冷,以西结的预言总是被人用来节制这里的骄气:"所以你要对那些抹上未泡透灰的人说:墙要倒塌……狂风也要吹裂这墙。"(《以西结书》第十三章:第十一节)14世纪的约翰·高尔悲叹厄运将至,1600年,托马斯o纳什写道:"伦敦让人忧伤,兰贝斯一片荒凉,生意人悲叹,人生出世就是一场受苦受难……自冬天以来,瘟疫与灾祸,主啊,救救我们!"1849年,沙夫茨伯里伯爵形容伦敦为"瘟疫之城",乔治·奥威尔的《叶兰在空中飞舞》里有一个人物说这里是"死人之城"。
瘟疫很早就降临伦敦,最早的记载见于7世纪。1563年和1603年之间,记载有五次厉害的袭击,1603年那次,近三万伦敦人丧命,"恐惧与战栗(死神的两大套索)攫获每一个人……听不见丝毫声息,只听到杀,杀",沃特林"如同空荡的修道院回廊"。无一人安全。城里没有一人能够安然无恙,"到处坑坑洼洼,到处是泥沼,十分危险、恶臭"。污秽,弥漫着"腐味"。伦敦城成了疾病的水槽。然而,伦敦历史上没有哪一桩事件,能够给市民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有备无患地遭遇1664年至1666年间所发生的劫难。
毗邻高斯维尔路的那片地区被称为山间磨坊,如今是一片空地,用作停车场。伦敦这个地区竟有一块荒地,实属罕见。答案在于其历史。在这里,根据丹尼尔·笛福的《瘟疫年纪事》所载,"高斯维尔路外有一块地,靠近山间磨坊……无数来自市府参事门和克拉肯维尔堂区的人被乱葬于此,甚至还有城外的死人"。换句话说,这里是瘟疫坑,1664年至1665年间大瘟疫之时,千万人被装上"死人车",扔进这边的松土里。
这里堪可比拟为狗沟的乱葬坑,近四十英尺长,十六英尺宽,二十英尺深,埋有一千具尸体。有些尸身裹着棉床单,有些裹着破布,有些几乎赤裸,或者布头裹得松散,抛出板车之时便已掉落。据说,有时由于绝望,活人也跟着跳进死人坑。派伊酒肆就在狗沟死人坑旁,夜里,酒鬼们听见死人车的轰隆声、车上铁铃铛的响声,就会奔到酒馆窗前,嘲弄哭丧的人。他们也会说些"亵渎神灵的话",诸如没有上帝,或者上帝就是撒旦。有个赶车人,倘若死人车上载着他的孩子,就会一路喊着"炸肉丸、炸肉丸,六便士五个",说着抓起孩子的一条腿。
今天,山间磨坊周边依然是一片荒地。
这些都是摘自笛福的记述。瘟疫之年,他年仅六岁,大多叙述基于道听途说,但也有同时代的一些记载,可以提供额外的思考材料。在瘟疫时期,任何肯进城的观察者都会首先留意到沉默。除了死人车,没有任何交通,店铺与市集全都关张。不曾逃出城的人,就把自己锁在房屋里,河畔荒凉得不见人影。壮着胆子上街的人,便走在街道中央,远远地躲开街道两侧的房屋。他们也避免跟人碰面。整个老城静得连桥下的流水声都听得分明。十字路口和大道中央燃着大篝火,于是街巷里弥漫着烟气、死人和临死之人散发的瘴气。伦敦的生命似乎即将终结。
在笛福的叙述里,伦敦变成活生生、受煎迫的生灵,而不是W.H.奥登诗里所谓的"抽象的市民空间"。伦敦备受"高烧"煎熬,"泪流满面"。其"容颜顿改","蒸汽和烟气"在街巷盘绕,如同被感染之人的血液。至于伦敦这具病体是从市民而来,还是居民是这座城市的散发或投射,这个问题不甚清楚。诚然,城市的状况导致了很多死亡。在这个手工艺和商业的中心,买卖的过程本身便毁了市民:"在很大程度上,出门购买生活用品这一必要葬送了整个城市。"人们做买卖之时,"在集市当场死去"。他们"原地坐下,当场死去",口袋里仍装着被感染的硬币。
笛福的文字里还传递了另一个让人悲伤的形象。在这座城市里,"因每户人家门户紧闭,显得城里监狱之多"。关押的隐喻在伦敦作家笔下反复出现,但在大瘟疫时期,出现了鲜活又真切的都市监禁比喻。这座城市的神话作家不曾辜负红十字架和"主啊,垂怜我们"这句祈祷的象征意义,但人们也许不曾完全认识到社会控制的措施。当然,很多人逃生去了,通常是窜过公园护墙或者屋顶,甚至谋杀守夜人,以便确保自己能够自由逃生。然而,理论上说,每一条街、每一幢房屋,都变成了监狱。
当时法令规定"所有墓地须至少六英尺深",这条法令贯彻了三百年。乞丐全都被驱逐。禁止公众集会。在一座以千百种方式展示其狂躁习性的城市里,法令与权威必须断然、严酷地强制执行。因此,以"禁闭"将房屋变成监狱,即便在瘟疫之时,很多人也认为这一措施既武断,又无意义。然而,在一座监狱之城,这是城市权威所能做的最自然、本能的反应。
笛福借助轶事与间接推测的细节,提供了一个伦敦人对当时这座"完全陷入绝望"的城市的想象。从他的记述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市民旋即返投迷信,并且显然是原始的信仰。街头陷入彻底的疯狂,先知、解梦者、算命者、占星师全都"把人们吓唬得魂飞魄散"。很多人怕暴死,冲到街上忏悔"我杀过人","我是小偷"。瘟疫最猖獗之时,全城都相信"上帝决心要叫这座悲惨城市的居民死绝了",于是,市民们"发了疯、心烦意乱"。丹尼尔o笛福十分熟悉伦敦(也许胜过当时所有人),他声称"在当时,伦敦人的古怪脾性,极大程度上造成自身的毁灭"。
当时有"魔术师、女巫……江湖郎中、卖膏药的",全都在街头张贴告示,推销自己的服务,向绝望之人出售药丸、饮料、糖浆、"瘟疫水"。"切普赛德大水渠旁天使路标酒肆"张贴了一张疗法清单,声称有"一剂上好的糖膏,可以预防瘟疫,切普赛德绿龙酒肆六便士一品脱"。
药物也跟着时代的潮流来了又去。在17世纪,市面上流行的药有苔藓、烟熏马睾丸、5月朝露、莨菪。在18世纪,常见的有豆蔻、裹着蜘蛛丝的蜘蛛。在19世纪,我们读到"掌叶大黄、硫酸"。在20世纪早期,东区闻名的有"铁凝胶、扎姆布克万用乌青膏、艾诺水果盐、欧桥养肺滋补水、克拉克血膏"。安德森的苏格兰人药丸于1635年面世,"1876年仍在出售"。
瘟疫之时,人们看见幽灵在大街上穿行。确实,伦敦向来受鬼祟困扰。克拉肯维尔墓地南侧有一幢精致的砖房,因名声不好而"极难招到房客"。德鲁里巷派克街七号是出了名的"不祥",最终被拆毁。同一条街上另一幢房子,二十三号,有个死过人的角落里闹"可怕的声响"。伯克利广场有一幢鬼怪作祟的房屋,"空了很长时间",王后门也有这样一幢房屋。
P.J.格罗斯莱在18世纪访问伦敦,评论说伦敦人"实在怕"鬼,而同时又"在理论上拿它们开涮"。同一时期,另一外国人拜访剧院,发现莎士比亚戏剧里的鬼魂激发观众的"惊异、害怕,甚至恐惧……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好似他们看到的场景是真实的"。时常有人指出,在这座热闹不断的城市里,伦敦人难以分辨戏剧与真实,但这里更耐人寻味的是,这类描述暗示着伦敦人那股惊人的盲目轻信。在16世纪中期,市府参事门旁有一幢房子里有个年轻女孩,捏造出一种神奇的声音,"全城人都受到极大的侵扰"。我们须想象那些飞短流长、传闻、畏惧。
伦敦作家"阿列夫"记载了另一个故事。1762年最初数月里,人们相信考克巷,那条曾经"肮脏、逼仄、昏暗的巷子里",其中有一幢屋里住着一个幽灵,人称"挠痒痒的芬妮",爱敲别人家的门。有个年轻女孩被认为中了这个幽灵的魔,"身边总响着神秘的声响,尽管她的手脚都被捆绑起来"。成千上万的伦敦人拥进考克巷观看,较体面者则可以参观女孩的卧室,一次进五十人,"恶浊之气几乎令她窒息"。一些德高望重的伦敦人成立委员会,调查这些传闻(其中一人是迷信的塞缪尔·约翰逊),最后得出结论,这个女孩"赋有捏造声音的邪术"。她的父亲在考克巷尽头被戴颈手枷,"人们同情地对待他"。于是,在伦敦再次被"极大地侵扰"之后,此事便这般告终。这简直好似这座城市本身就是幽灵之城,到处是过去的影子,纠缠着居民。
"伊斯灵顿鬼魂"出没于克劳兹利广场三一教堂的一片空地上,导致"各处奇妙的骚乱,地面拱起,每个角落都翻起地皮"。据说迈克尔o法拉第的鬼魂捣乱布莱德街的一个电话交换机,这里曾是他的萨德曼教派集会的礼拜堂。霍兰勋爵、丹·利诺、迪克·特平、安妮·查普曼的鬼魂都曾有人见过。老医院和教堂是最常看见幽灵的地方,海格特公墓边史威恩巷一直是"见鬼"的地方。大英博物馆东方馆显然有个幽灵;数世纪以来,有只幽灵黑鸟在迪恩街一幢房子出没。霍兰伯爵的女儿在肯辛顿公园散步,"遇见自己的幻影、拥有她的习惯,以及种种一切,好似照镜子"。她一个月后死去。史密斯菲尔德的圣巴塞洛缪堂区牧师长在布道坛上看到一个神灵的幽灵"身披日内瓦黑袍……热忱高昂地激劝一群不可见的教众,慷慨激昂地比画手势,时而俯向布道坛右侧,时而俯身左侧,重击面前的垫子,嘴唇一直在动,似乎话语从嘴里滚滚而出"。
伦敦塔当然是无数幽灵的天然栖息地。很多熟悉的人物在这里出没,其中包括沃尔特·雷利、安妮·博林。后者曾被三个目击者看到她的"白色人影",一名当值士兵在中尉宿舍门口"昏倒"。他被依军法判罪,但后来无罪释放。一只黑熊幽灵从伦敦塔内珠宝厅"门下钻进来",目击此景的哨兵两天后死去。伦敦塔内确实有一间动物展览室或者动物园。狱长及其妻所透露的幽灵最模糊,两人坐在众人皆知的珠宝厅客厅桌前,"突然一支玻璃管子,跟我的胳膊一般粗",在空中盘旋。里面装着"浓稠的液体,白色、淡蓝色……在管子里不定地翻滚、搅动"。它靠近狱长的妻子,她叫道:"哦,基督!它抓住了我!"然后穿过客厅消失了。
还有其他一些依然被伦敦人畏惧的地方。1290年驱逐犹太人之时,被谋杀、被溺死的犹太人的叫喊声,如今依然能够在格雷夫森德退潮时听见。现今处于戈登广场地基下的"四十步原野",视各人看法各异,曾被视为"着了魔道"或"受了袭击"。人们曾经到这里采芭蕉叶,据说可以影响梦境。但更重要的是,在同一块地面上,两个亲兄弟在决斗中杀死对方。据说,两人最后的脚印依然留存,杀戮的地面则寸草不生。骚塞确实找到七十六只脚印轮廓,"人类大脚型号,约三英寸深";1800年夏天,这片地区重建前夕,莫泽"数出四十多只脚印"。
有一幅画十分耐人寻味,大约绘于1930年,题名为"切普赛德街卖乳酪乳清的人",画面描绘一个盲女坐在切普赛德街水渠下,把手伸向三个扫烟囱小伙。这条水渠是他们经常出没的地方,他们的表情活泼得让人吃惊。其中两人的脸黑得仅露出眼睛和嘴。他们都很瘦小,其中一人似乎驼背。他们看似确实类似这座城市的恶劣行径,似乎在威胁或恐吓这个瞎眼苍白的街头小贩。因此,或许可以说,扫烟囱小伙在五月节游行里再度上演其威吓,这种威胁须象征性地用笑声缓解。然而,正如伦敦所有的仪式,这个庆典逐渐演变得别出心裁。在18世纪晚期,引入全身覆盖枝条树叶的"绿人",人称"绿杰克",或者单纯称之为"绿人",由牛奶妹和扫烟囱小伙陪同,作为春天的俗艳象征,在各堂区游行。五月节后来转到街头艺人手里,最后彻底地消失。
然而,伦敦的迷信行为不曾全然消失。这座城市本身依然赋有魔力。这是神秘、混乱、非理性的地方,唯有借助私人的仪式或公众的迷信活动,才能让此地组织有秩,处于控制之下。伦敦的伟人塞缪尔o约翰逊走过弗利特街之时,不由自主地触摸每一根柱子。同样地,伦敦很多马路不容许出现十三号这个门牌,譬如弗利特街、公园巷、牛津街、普拉德街、圣詹姆斯街、秣市、格罗夫纳街。
然而,对一些人来说,大道的路线本身更赋通灵意味。一直以来,人们试图规划这座城市的轨迹,想借助"对准线"以直线联接某些地方。诸如,这样一条直线将海格特山与诺伯里南边的泊拉特山相连,一路连接数量惊人的教堂和礼拜堂。人们也试图连接尼古拉斯o霍克斯默建造的各座教堂,或者以意味深长的地形学描绘圣潘克拉斯老教堂、大英博物馆,或者格林尼治天文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复兴曾在这片地区活跃的凯尔特土地魔法,同时也赋予地方神力应得的认可。
威廉·布莱克描述洛斯走过伦敦之时,所想象的便是这股神力。"直待他走到老斯坦福特,/从这里走向斯特普内,/再前往勒萨狗岛/从这里穿过河边的小巷/一路把细节看在眼里。"如同瘟疫时期那些哭丧的日子,这座城市的生命和历史或许能够在这些细节里复苏。
——本文节选自彼得·阿克罗伊德《伦敦传》(有删节)/译林出版社/2016
《伦敦传》,
彼得·阿克罗伊德 著,
译林出版社,2016
一部呈现伦敦上下两千年的史书。
从正史和民间传说到饮食和消遣娱乐。
从黑衣修士会和查令十字街到帕丁顿和疯人院。
从威斯敏斯特教堂和圣保罗大教堂到伦敦佬和流浪者。
从移民、农民和妓女到大瘟疫、大火和二战空袭。
阿克罗伊德用恢宏的城市历史、敏锐的观察、无数市民和访客的话语,揭示了伦敦如何在从远古到现代的历史洪流中淬炼成形。
了解更多伦敦故事
点击
阅读原文
或
扫描下方二维码
购买《伦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