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点
虽然我们一直倡导全民阅读,但实际状况差强人意。外滩教育特约作者,上海三林东校老师郑钢认为:阅读是一切学科的基础,因此我们要致力于培养终身阅读者,并建立一套完整独立的阅读体系。下文中,郑老师也介绍了提升阅读能力的“三驾马车”,帮助父母明晰培养孩子阅读能力的关键点。
说起阅读,很多人不满意,阅读还远远未能蔚然成风,成为全民风尚。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调查显示:2017年中国人均纸质书籍阅读量为4.58本,与世界阅读大国的数量相差甚远;
还有个数字是关于儿童阅读,美国伊利诺大学阅读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美国儿童的阅读量是中国儿童的
六倍
,相距之大令人咂舌。
对于阅读的重视程度与其收效程度并不匹配,阅读如何变革——是当今人们关注却又无奈的话题。


阅读应该是教育,而不是教学
讲到阅读,很多人的脑海里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阅读教学,是语文或英语课堂里的阅读:学生打开课本,阅读文章,然后围绕作者、时间、地点等基本要素梳理文本,之后就是引导学生分析中心思想或者中心主旨。
这样的阅读教学是围绕考试展开,一招一式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考试技巧,目的是如何在考试中得到高分。对于文本的理解更多的是迎合出题者的“预设”。
相应的教学对于批判性思维、创造性等高级思维培养较少关注,学生的审美体验也只是停留在浅尝辄止,浮光掠影。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好像还有点困难。
我们绝大多数的孩子还远远没有养成“好读书,读好书”的习惯
,
远没有将阅读作为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安身立命的依靠。

如此的现象,一个原因归咎于当前教育的功利和浮躁。
如今教育诸多行为局限于考试的应付,非考试要求的不做,非升学要求的不重视,赤裸裸地将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凌驾在人性和人文上,将知识的记忆、背诵简单等同于教学的所有行为,忽略对于方法、过程的关注和学生的情意发展。
在应试观念的裹挟下,阅读也无法“独善其身”,只能随波逐流,投入到应试的洪流之中。
有个同事告诉我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她让学生去买一本名著阅读,可是学生居然带来了好几本“考点版本”,翻开原文一看,里面居然穿插了很多阅读题和解答。
这样将一次原本“心灵滋养,精神成长”的阅读之旅活生生地变成了“索然无味,强迫无奈”的应试准备,如此功利化的阅读可谓是比比皆是。

对于阅读的定位也是影响阅读成效的重要因素。
我们很大程度上将阅读视作是课堂内的事,是语文老师或者英语老师的责任,是课堂里教学或学习行为。
一旦如此定位的话,阅读就沦落为应付考试以及个体的行为,而脱离了阅读的本身要义。
朱永新先生对于阅读的重要性论述可谓家喻户晓: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
如此的定义是将阅读从“教学”的定位提升到“教育”的定义。
朱先生还进一步解释了阅读的误区:
很久以来,我们一直都仅将阅读看作个体的行为。这样的认识是片面的。
我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共同阅读决定了其精神力量,而精神的力量对于一个国家软实力与核心竞争力的培育,起着关键作用。
由此可见,朱先生是将阅读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将阅读提升到“育人”的高度。
在美国的K-12年级教育体系中,阅读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贯穿着整个基础教育阶段,现在已经形成了一套系统的阅读教育体系,原因在于美国对于阅读的定位,强调阅读以教育的方式,出现在整个国民教育系统中。
在此理念影响下,国家宏观引领全国学生阅读教育实施的政策文本不断颁布,持续深入地推动全民阅读的深入开展。
要解决当前阅读的困境,重要的一点在于观念的转变,将阅读提升为国民人文素养的奠基工程,将阅读教学转变为阅读教育,并致力于培养终身的阅读者,而不是停留在考试的应对者。


阅读能力不仅仅影响语文
最近关于语文高考改革的说法一直牵动着老师和家长的神经,原因在于考试中阅读的变化,首先是阅读量的大幅度增加。
权威人士透露:以前卷面大概7000字,现在是9000字,将来可能增加到1万字;还有是阅读题量也增加了不少,而且高考的阅读面也在悄悄变化,哲学、历史、科技什么类型的内容都有。
-
有文学类文本,
例如答题要点很难把握的记叙文;
-
有长篇文言文,
例如《史记》中的人物传记;
-
有诗词鉴赏,
或许并不难,但存在陌生的诗词。
也就是说,学生仅仅只读教材的文章或者四大名著,不可能得高分。
不仅仅是语文高考改革,几乎所有的科目改革中都涉及到阅读的要求。
如今都在讲核心素养,核心素养是学生面对真实的生活场景,用所学习的知识处理真实问题的能力。
考试的命题也将随之发生变革,基于真实的生活场景常常融入到复杂的题干中,需要学生能够在短暂的时间内阅读题目,提炼关键的信息,处理蕴藏的信息,并建立学科本质的联系,这样才能解题。
也就是说阅读是一切学科的最重要基础,如
果家长依然说自己的孩子没时间读书,等同于说要自己的孩子放弃所有学科。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Cromley教授,曾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好几个国家,研究孩子的
阅读量和科学课
的表现之间的关系,最后发现,这两者
具有非常大的正相关性
——所有国家的平均值为0.819。
还有数学学科与阅读的关联,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心理学系博士Aunola就发现,
阅读时更注重技巧的孩子,在理解、解决数学问题时能力更强。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Grimm教授也抱持同样的观点:他曾分析了大量三年级的学生,最后发现,
有高水平阅读理解能力的学生
,比起阅读能力差的学生,
能够更快地学会解决问题和掌握数据处理能力
。
多伦多大学应用心理学和人类发展学教授基思·斯坦诺维奇曾借用莫顿的“马太效应”去解释他发现的早期英文阅读能力与孩子间学术成绩之间的关系:
一个孩子启蒙阶段阅读能力越强,他随后的学习能力越强
;
到小学三年级或四年级之前还没有打下良好阅读基础的孩子,在学习其他技能方面终身会面临挑战和困扰。
斯坦诺维奇还说:
阅读能力增长缓慢,会导致孩子在认知、行为和动机方面的负向累积,会阻碍孩子学术能力和认知能力的发展,并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
这种状态持续时间越长,孩子在更多的认知和行为领域表现会越差。
2018年的一项最新的学习研究呈现了阅读不仅丰富认知,还能塑造大脑的证据。
在该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对学习中的受测对象进行观测,发现在阅读能力测试中表现越好的受测者,其被观测到的大脑各区域的互动也最活跃。
所以“得语文者者得天下”,这句话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真真切切地会发生。
此天下,不仅仅是语文学科,还是学生学习的所有学科,具有足够的理解和分析能力应对考试。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阅读能力和习惯的培养,学生有足够地力量、自信去建构自己的人生,获得自我的救赎,并用阅读中培养的学习应对信息爆炸的时代,成就自我的“天下”。


建立完整、独立的阅读体系
纵观世界众多重视阅读教育的国家,尽管他们关于阅读政策、制度、方法和评价等方面会有所不同,但是有一点却如出一辙,极其相似,那就是具有一套完整,独立的阅读体系。
说到独立,也就是说阅读体系具有内在的系统性、完整性,并不仅仅从属于母语或者外语,而是从本国语言的特征出发,具有相对独立、科学的标准、教材、评价和教学等课程要素。
如何架构阅读体系?
建立分级阅读体系是普遍采取的方法。
分级阅读体系从语言的词汇、拼音、理解等方面设定不同的等级,让不同年龄段的学生达到相应维度和要求。
当然,分级阅读根本目的不是让相同年龄的学生达到相同的标准,而是为学生创造一个最理想的阅读区间,允许先进,鼓励落实,始终让每个孩子一直在阅读的道路上。

有了分级系统的支撑,家长和老师更容易为孩子选择适合他们的书籍,对学生来说不太难也不太简单,需要花一些力气,但不至于造成困扰,孩子能够体验到阅读的乐趣,同时兼顾阅读的深度,在持续阅读中不断向阅读深水处探索。
阅读分级系统的另外一个好处能够比较清晰地评判断和衡量学生的阅读能力。
-
孩子正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
是超越应有的标准还是低于?
-
下一步将往何种方向努力?
-
学生的阅读始终在即时反馈和目标导向下进行,慢慢地,孩子们在循序渐进的阶梯式读书中离不开阅读,无论是物理空间还是在精神空间中。
一旦阅读习惯养成,阅读对于孩子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根本不用外界的督促。

早在100多年前,英语阅读研究者就已经开始研究儿童分级阅读的问题。目前国外比较知名的分级体系中知名度最高、应用最广泛的就是
“蓝思分级阅读体系”
。
这套分级标准比较精确、量化、可操作性强,其意义不仅在于“课外阅读”,更是一个语言发展、阅读能力、写作能力的综合训练工具,是一套行之有效的训练模式。
它让学习语言、阅读和写作,变得目标清晰、有章可循。
美国每年有超过3500万的中小学生使用蓝思分级,来衡量自己的阅读水平和选择合适的图书,学校将蓝思分级系统视作推进学生阅读能力培养的重要工具。
他们的学生可以没有学科的家庭作业,但是每天会化一定时间完成蓝思系统的在线阅读或文本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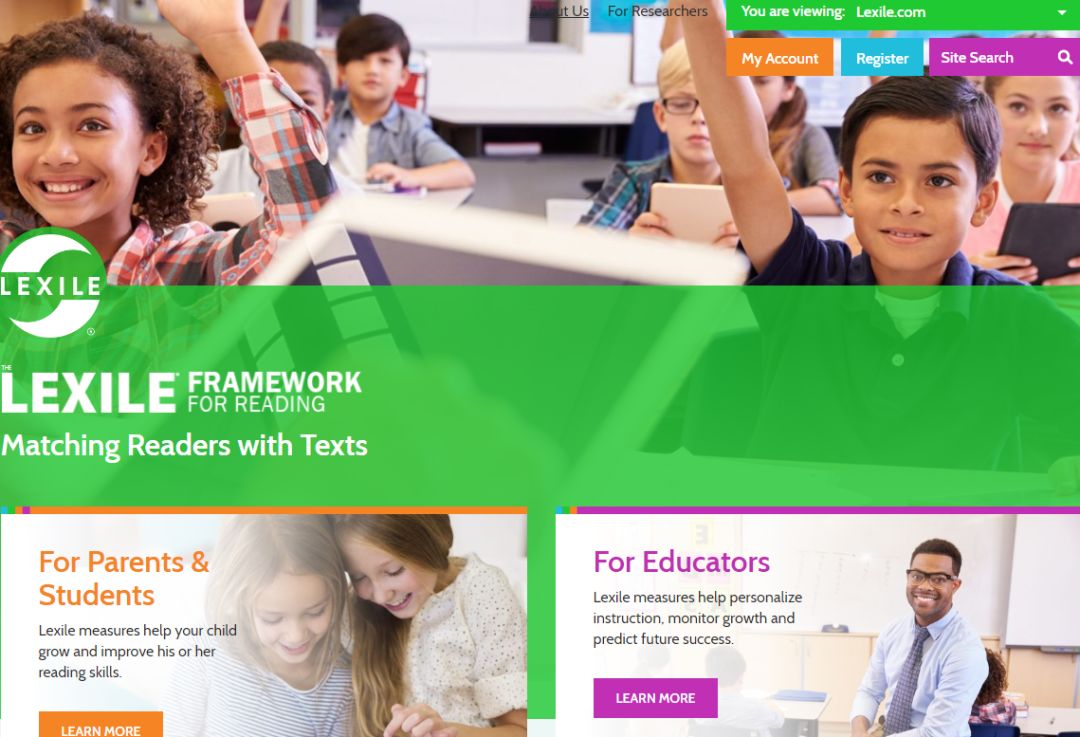
全球超过180个国家的学校都在使用该体系
加拿大、英国、德国等20多个国家也在使用蓝思系统,建立了英语阅读能力培养的量化指标。
然而直到现在,国内还没有一个权威部门和专业机构,出台基于中文特征的阅读分级系统和详细的方案。
社会上冒出了很多中文版的儿童分级阅读,不过相当部分的分类
缺乏权威性和科学性。
科学的分级系统是以儿童读者为主体、以儿童阅读能力为基准,符合中文语言结构和读者认知思维的系统化分级。
要推广阅读,亟需从国家层面组织力量研究中文分级阅读,建立数据模型,制定儿童阅读能力标准,并提供相应的书目、评估、分析、指导等配套资料,并进入学校系统,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部分。


政府、社会、学校和家长
是阅读推广的“合伙人”
教育在任何一个国度从来不是孤立产生和发生的。正如植物生长一样,阳光、土壤、水分以及必要的栽培必不可少。
推广阅读,推进全民阅读,不仅需要学校,还需要政府、社会和家长,他们是阅读推广责无旁贷的“合伙人”。
人们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在阅读上父母同样也是第一任老师,言传身教尤为重要。
要让孩子喜欢上读书,那父母自己首先要酷爱阅读。
如果父亲或母亲手不释卷的话,从小在阅读环境长大的孩子,就会对阅读具有天生的亲切感和认同感。
其实读了还不够,还要交流,父母要把自己的阅读经历、收获、兴趣与孩子共享。
更为重要的是,家长要引导孩子将他们所阅读到的与大家分享,交流和对话。
譬如在阅读故事后,让孩子讲一下故事情节,培养他们的表达能力及逻辑思维能力;还可以讲讲里面的人物,他们的情感、性格、爱好,关系等等;也可以谈谈故事所要传达的观点和主旨。

交流和分享既是促进孩子理解文本的过程,也是培养孩子阅读效能感和成就感的过程,共情陪伴孩子,引导、鼓励和肯定孩子的阅读成就。
所以家长并不是将一本书扔给孩子就好了,而是不断与孩子交流和分享。
权威的研究和数据说明,人生的黄金阅读时间在于童年,要让一个没有阅读习惯的成人喜欢阅读,则非常地困难。
抓住了童年的阅读,就解决了一生的阅读,就打开了全民阅读的大门。
从政府的角度,则需要将阅读提高到提升国民素质和人力资源的高度,通过立法的方法调动和整合多个系统,整体推进阅读。
社会的力量同样必不可少,每个人都应该为孩子的阅读教育负责,包括研究机构、社区、家庭和图书馆等等,开展研究,组织活动,营造氛围,鼓励孩子阅读和学习。
如果说孩子阅读培养在进入学校前的第一责任人是家长的话,那进入学校阶段后的主要责任应该转移到教师。
孩子进入了学校,在六七岁的阶段,是指导他们如何阅读,学会阅读的关键阶段,而不是仅仅是培养兴趣而已
。
教会孩子如何阅读,如何思考,提升阅读的品质和思维,这一点对于学校阅读是尤为重要,也需要教师用专业的方法和目光指导。
阅读一定是具有阶段性的,对于不同年龄的阅读者要求是不同的,对于家长和老师的指导要求也是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