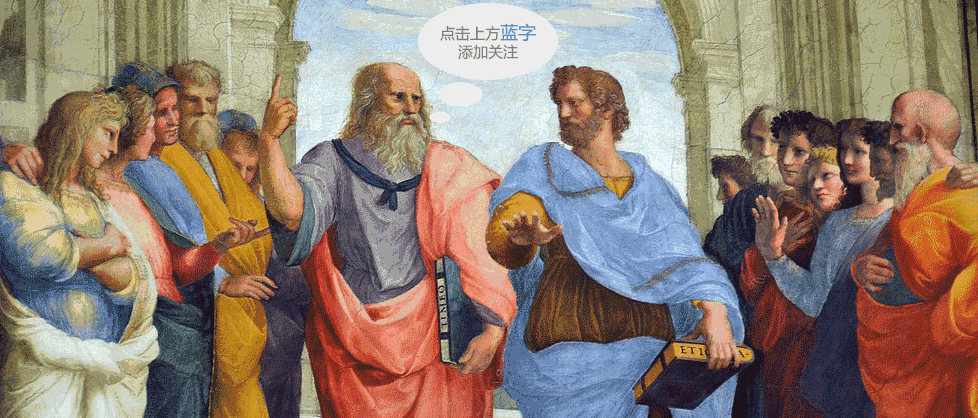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彦门在路上”

摘 要:学校的开学典礼蕴涵一种“交叉的二分对立”结构,这种结构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并充满了区隔的意味。它是社会逻辑在学校中的延伸,或者说是学校在预演着社会的逻辑;它鲜明地标示了尊卑、高低、长幼、主次、大小等权位意识及其实践规范。在“开宗明义”的开学典礼上,这种社会逻辑的强力诉说与实践操演,先入为主地对受教育者进行了一剂“官本位”意识的无痛注射,并在以后历次诸如此类的典礼上不断接种、反复强化,终至潜移默化、影响深远。
关键词:开学典礼;社会逻辑;权位的象征;仪式;教育社会学
开学典礼是每个学校每个学期开学伊始都要举行的活动。顾名思义,“开学”即一学期教学的开始。问题是“开始学习什么?”语、数、外、理、化、生等各门课程自是要学习的,但不是这里要分析的重点,这里要考察的是开学典礼的“社会蕴涵”。这对许多人来说似乎又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这只是一种形式!”,“每学期都这么做!”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据特纳思想,“仪式”(ritual)一词更适用于与社会变迁相联系的宗教行为,而“典礼”(ceremony)一词则同与社会地位有关的宗教行为有着更紧密的联系;仪式是转变性的,典礼则是确认性的。[1]那么,作为学校每学期的开幕曲,开学典礼传达、确认的是什么样的社会观念及价值坐标呢?
细致观察一个开学典礼,不难发现它有一个明显的结构,这一结构可用“交叉的二分对立”(binary oppositions)[2]来排列(如表1所示)。在开学典礼中,表1中所列二元对立体系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种二元对立的结构充满了区隔的意味,它是社会逻辑在学校中的延伸,或者说是学校在预演着社会的逻辑。这个结构包含四套体系。
表1 开学典礼中的交叉二分对立
|
纵向对立
|
横向对立
|
垂直对立
|
内外对立
|
|
过去/现在
|
男生/女生
|
台上/台下
|
上级领导/校领导
|
|
非学生/学生
|
新生/老生
|
主席/侧席
|
上级领导/教师
|
|
小学生/中学生
|
低年级/高年级
|
侧席/次侧席
|
上级领导/学生
|
|
中学生/大学生
|
高个/低个
|
左/右
|
……
|
|
非重点校学生/重点校学生
|
|
校领导/中层领导
|
|
|
……
|
……
|
领导/教师
|
|
|
|
领导、老师/ 学生
|
|
|
|
校服/自由服
|
|
|
|
教师代表/教师
|
|
|
|
学生代表/学生
|
|
|
|
……
|
|
第一套体系是纵向的,区隔的是学生/非学生,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学生。比如,对于一年级的小学生而言,开学典礼预示着“我上学了”,“我已由一名儿童(孩子、宝宝)变成了一名学生”;对于中学生/大学生来讲,开学典礼则象征着“我已不是小学生/中学生了”,“我应当像个中学生/大学生的样子”。总之,“‘成为你所是的人’,这是所有制度行动的施事性巫术背后隐藏着的一条规则”[3]。这种纵向体系,通过强调时间的过渡(例如从“孩子”、“宝宝”到“小学生”、“中学生”以至“大学生”),掩盖了典礼仪式的一个基本影响,即“区分开那些受礼者与那些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不会经历此仪式的人(而不是那些还未受礼的人),也即在那些这一仪式适用的人与其不适用的人之间,建立了永远的区别”[3]。譬如,那些无缘学校或无缘某类(级)学校的人,便被永远排除在了由入围者们参加的各种开学典礼之外。
第二套体系是横向的,表达的是男女有别、新生老生、身材高低、依次递进的二元结构。开学典礼时(往往在操场上或礼堂),往往按照年级、班级、男女、身高等编码站队(落座),呈现出“后浪推前浪”、“新生变老生”、“学弟变学长”的新老更替、依次递进的变动态势。
第三套体系是垂直的,彰显的是官民、尊卑以及长幼、(资格)高低等二元排位。其中,学生代表指的在典礼时(往往有颁奖之类的活动)发言的代表(其他代表亦同)。左/右之所以列入垂直对立,是因为主席右边为大,“无出其右者”即为此意。校服(学生)/自由服(领导、教师)之所以列入垂直对立,是因为校服是符号,“它们也起约束作用”[4],其重要功能是使学生“齐一化”、“群众化”、“匿名化”、“背景化”,这是站在观察者而非穿戴者的立场而奉行的是一种“铲平主义”;而“铲平是为了特殊化”[5],以学生之“背景化”彰显身着自由服的上级(领导、教师)的威严与鲜明。之所以强调是“二元”对立,是因为不同角色往往特别注重与自己邻近(上或下)的角色比较和“较真”,如副书记甘愿坐在书记下座,但对于副校长则要力争上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我们嫉妒那些在时间、空间、年龄或声望方面接近我们的人,……不会嫉妒那些在我们或他人看来,远低于或高于我们的人”[6]。
第四套体系是内外对立,实为第三套体系的变式,惟表明的是被邀请参加典礼的(校外)上级领导与学校领导以及师生的对比而已。
开学典礼中的交叉二元对立结构,鲜明地标示了尊卑、高低、长幼、主次、大小等权位意识及其实践排列。而这些,其实也是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土壤之中的。譬如,传统儒家认为,每个群体内都有长幼亲疏贵贱上下之别,不平等是普遍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荀子·荣辱篇》)。因此,儒家将人分成具有二元对应性质的类:“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也”(《中庸·治国》),是谓天下五项大道(五伦);并规约了每一类的应尽之道(义):所谓 “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顺;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大学·止于至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是谓十义”(《礼运》)。《乐记》亦云:“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又及《荀子·君子篇》:“故尚贤使能,则主尊下安;贵贱有等,则令行而不流;亲疏有分,则施行而不悖;长幼有序,则事业捷成而有所休。”而《礼记》里面讲的十伦(鬼神、君辰、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则几乎把现实的和虚构的关系全囊括了。而且,这些是不可改变的社会秩序,诚如《礼记大传》所说:“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对于国人这种等贵贱的思想,鲁迅曾剖析得入木三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欺凌,但也可以欺凌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地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或虽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了——‘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供神也。故王臣工,工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大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有了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7]
这种等贵贱、别亲疏、重(宗法)结构的思想,甚至还体现在中国的语言上。仅家族的称谓,就数目繁多且层次明晰。如在英文里仅以uncle/aunt了事的称谓,在中国则必分作叔婶、舅父母、姨父母、堂父母、表伯父母、堂伯叔父母、族叔婶、族伯父母等种类;又如兄弟姊妹、堂兄妹、表兄妹、表姊妹等称谓,在英文里也仅以brother, sister, cousin了事;而一个you字,就可区分出你、您、尔、汝等不同形式;再如甥、侄等字,也不像nephew那么简单;就令兄弟之间,亦有嫡(妻所生)庶(妾所生)之分、长幼之别,故在宗法上的权利皆不相同。有学者就此判言,这种“公民名词少,族属名词多”的称谓语言,对于中国整个文化很有象征意味,“中国这样的家族社会绵延到很久很久,走不到公民社会”[8]。
中国人的这种思想,即使行将离开人间,竟或到了阴朝地府也还要保留,不谓不深重。譬若庶人死即为“死”,诸侯死却曰“薨”,天子死则尊为“崩”了,真乃“生”得伟大,“死”得亦光荣!对于家族成员“死”的称呼与祭祀的名称,亦要赫然区分,见表2、表3。
表2 人品及其死时的名称
|
人 品
|
死 名
|
告 丧
|
|
天 子
|
崩
|
登假
|
|
诸 侯
|
薨
|
|
|
大 夫
|
卒
|
|
|
士
|
不禄
|
|
|
庶 人
|
死
|
|
表3 家族成员生、死、祭的名称
|
生 时
|
死 时
|
祭 时
|
|
夫
|
|
皇辟
|
|
妇
|
嫔
|
|
|
父
|
考
|
皇考
|
|
母
|
妣
|
皇妣
|
|
王父(祖父)
|
|
皇祖考
|
|
王母(祖母)
|
|
皇祖妣
|
在这些复杂的称谓背后,蕴涵着中国人(尤其是汉人)对待亲属和社会关系的两个重要原则:一是男女有别,二是长幼有序。[9]这种(传统)社会的逻辑延续至今,并在开学典礼上一仍诉说。尽管现在施行的是新式学校教育,却在内心深处或无意识中遵循着传统社会的逻辑,演练的仍旧是社会上那一套官本位的模式。这就难怪有教授对某重点大学的开学典礼大声激呼和责问:“这样的大学是什么?”,“‘处级’贵过教授?”,“横看竖看,都是衙门”:[10]
某日,某部属重点大学的新生开学典礼在该校大礼堂隆重举行。来自五湖四海的数千名高考胜将鱼贯而入,齐把目光投向主席台那密密麻麻的一片。经大会主持人一一介绍,方知第一排坐的都是校级领导,从书记到校长到各副书记、副校长,还有纪检书记,以校长、书记为中心,从左右两边依次排开,一个也不能少。第二排是各学院的院长,也都如数看齐,最后一排是各学院的教授代表,据说他们还是由校办点将的资深教授。“校领导席”、“院长席”和“教授席”,秩序井然。……我丝毫不怀疑这样的排列并非“独此一家”,不必少见多怪。况且,如果改用别的方案去排,那不是很费劲也很为难吗?……你把第三排与第一排对换吧,那既无法显示校领导的重要性,也容易让某些领导提出质疑:“我们也是教授”(这也是实话,他们个个都是有教授职称的);你把第三排调到第二排吧,院长们也可以反驳说:“我们也是教授”,而且把教授们夹在校长与院长之间,主席台的“层次感”就会遭到破坏,教授们也未必能感到自在。但问题在于,我们不是经常说要“开放”、要“接轨”吗?如果我们把目光稍稍投向那些教育发达国家,在那些国家的学府里,他们会制造那么庞大的主席台,还把教授列入末座吗?他们敢吗?借助于开宗明义的开学典礼与三个等级的递减式排列,把官本位的家底毫无遮饰地裸露无遗,将会给那些兴致勃勃走进学术殿堂的入门者带来什么潜意识的影响?教授、学府、学术的尊严何在?……从现实而言,目前的大学就是一个享有固定行政级别的衙门。
笔者长篇征引上文,并非出于其作者的义愤之情,而是想对之进行社会学的解读。首先,纵然这位教授很气愤,即便他确知“目前的大学就是一个享有固定行政级别的衙门”;但他仍未真正跳出社会逻辑的“钳制”,譬如他提笔就使用了“部署重点大学”的字样,并纳闷“如果把教授们夹在校长与院长之间,主席台的‘层次感’就会遭到破坏,教授们也未必能感到自在”。这说明社会逻辑支配学校程度之强、影响程度之深已到了“很自然”的地步,到了“跳”而不“出”的境地。随手还可以举出类似的事例,譬如:“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决定,著名化学家、博士生导师陈骏教授担任南京大学校长(副部级)”,“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决定,任命易红教授担任东南大学校长(副部级)”[11];“(2006年)8月1日,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赴杭州宣读任免通知:……杨卫接任浙大校长(副部长级)”。凡此种种,与钦差奉旨“封××为××,从四品”的古法何其神似!难怪有评论说,“在公立大学中,从未形成从不具有行政级别或官员身份的名教授、名教育家中选任校长的机制”[12]。
其次,确如该教授所言,教育发达国家至少不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操演大学衙门化的举动,这在“政府官员进高校”以及“招收名人或授予名人学位”方面就可见一斑。在发达国家,虽不乏政府官员进高校或参加学校庆典的现象,但操作的逻辑和标准与中国迥异。譬如,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是原美国财政部长,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离任后也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普通教授。但国外聘请政府官员出任校领导和教授,对其学术背景要进行严格审查,官员职位并不重要,如克林顿就落选哈佛大学校长,而比他职位低的萨默斯却得以当选。又如20世纪80年代,哈佛大学校庆时请当时的总统里根参加,里根便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哈佛大学能够授予自己一个名誉博士学位,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牛气冲天的哈佛大学断然拒绝了权势熏天的总统的并不过分的要求。哈佛大学学术委员会严肃指出:学术标准绝对不能在权势和金钱的面前妥协,他们宁愿总统缺席大会,也不愿开这样一个恶劣的先例。但“与哈佛大学强硬的姿态相比,中国名校的骨头却是软弱的”,它们既“卑躬屈膝”、斯文扫地地向有名、有权或有钱的“明星”敞开大门以让他们如同京剧中的“票友”那样参与“玩票”[13];(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也把“高官执教鞭、官员兼教授”变成了值得夸耀的大喜事,而且,与国外不同的是,一些高校聘请官员做领导或教授,只需“经党委、行政研究,征得领导本人同意”就行了,至于官员教授是否授课,那不是关键问题,重要的是他们有名声,能发挥“优势”。[14]
再次,为什么把教授排列第一或第二排也作难?因为他们会说“我们也是教授”。但关键不在于“我们也是教授”,而在于“我们还是、或者我们首先是校长、是院长”。“校/院长+教授”所以令一般的“寡”教授(尽管“资深”)“自惭形秽”或“感到不自在”,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客观上不排除校长、院长在学术水准上确实不劣于甚至往往还优于教授,其资力、资历、资本确实强于、深于、大于教授;此时的“自惭形秽”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二是主观上也是致命的,乃是“官本位”的思想在作祟,即以行政级别(如校/院长)为“尊贵的头衔”,来凌驾学术职称(如教授);此时的“感到不自在”就有些扭曲变态而难以令人服膺了,这极类拿公鸡与母鸡比下蛋,原本就不是同一逻辑下的东西,偏偏就这样失范地扭结在一起。惟其失范,世人才往往欲“学而优则仕”,学人名片及作者简介才每每要“官衔第一、职称第二”——即令有不屑于此者,亦不得不循此道。说到底,此乃社会逻辑在学校教育中的持续性延演。
自孔丘“耕者,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之“读书做官思想的最早表述”[15]始,“中国人凡受教育者,做官的思想非常发达,自己是那样的希望,社会是那样的期许,直到现在,此风不破”,加以“士与仕之连带为用、不可分离的教育系统,则无怪乎做官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8]。两千年前,在“开学典礼”上就须习唱小雅上的三首诗歌,以学习学做官的初步,所谓“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礼记·学记》)。如今的情状形异实同。而且,上述引文中该教授的义愤及困惑恐怕还不止于现有的烦恼,倘若适逢某日校庆,驾临一批上级官员,恐怕教授们连第三排的座位也得腾出了。这并非耸听之危言,时下“官本位”意识沉渣泛起,已经延长到诸如校庆、院庆乃至各式各样的“庆”上。而“这‘庆’那‘庆’的,说白了,不是借个名目“官庆”,就是找个由头‘庆官’;搞一次庆祝,加深一次‘官本位’的烙印,把‘官本位’的延长线拉长一截。如此而已”[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