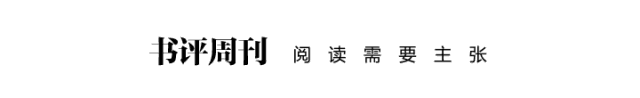
生日那天,我走了好多路,午后到猎德涌,坐在仿佛江南的小石桥边。
河水碧绿,风吹起阵阵涟漪。岸上垂柳冉冉披拂,天空蔚蓝,云海美幻。阳光普照下,城市恍如隔世。
不敢相信活了这么多年,感觉好像活了一天,又好像活了一千年。

《甘州子》
(五代)顾敻
每逢清夜与良晨,
多怅望,足伤神。
云迷水隔意中人,
寂寞绣罗茵。
山枕上,几点泪痕新。
南国也有冬天。每到冬天,我都会变成一个死者,变成遥远的回忆。灰蒙蒙的地平线上,一列看不见的火车隆隆而过,里面坐着一个我。许多天过去了,地球转到另一个方位,我还是没能忘记你,也没有被治愈。遗忘很长,故事太短,才开始就完结了,连彼此的人都未及看清。如罗伯特·勃莱诗中的蚂蚁,冬天的蚂蚁,每个人都带着隐秘的伤口和沉默,继续呼吸,继续活着。我靠词语活着。我通过词语去爱。天真的词语,危险的词语,无辜的词语。有些是火焰,有些是绿荫,有些是露水,有些是利刃。我至少憬悟,我爱的不是一个人,我爱的是爱本身。你并非我生命的全部,没有你我照样活着,也能活得好好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很快乐,可是快乐算得了什么?我来世上绝不是为了快乐。我来是为了爱,我想学会在这个世界去爱,在分离中依然感到爱的完整。五代词绝大多数写爱情,本质上,所有的诗都是情诗。爱情不是爱的唯一方式,却是最强烈、最容易使人忘我的方式。掉进爱河,意味着迷失,而人只有在迷失的时候,才能回到原始的本质,这就像忽然迷路时,世界看上去不再那么坚实,而是变得摇摇晃晃。来看这首词。“每逢清夜与良晨,多怅望,足伤神。”不是每天都想你,更不是每时每刻,你的缺席已成为一种存在,如同背景空间,无需想起,不会忘记。但清夜与良晨,每当这样的时候,世界潮水般退去,或者还没有醒来,你从背景中显现,我们离得很近,听得见彼此的呼吸,好像你就在我的隔壁。可是这里并没有你。现实如同深深的梦境,大雾弥漫,即使晴天,也看不清方向。“云迷水隔意中人”,怅望远方,云迷水隔,不知道他在哪里。云迷,水隔,这些措辞准确地摹写出思念者内心的迷茫。“寂寞绣罗茵”,恋人离去后,最孤独、最怪异的地方,莫过于床。独守空床,的确,承载过两人欢爱的床,顿时变得很空,越来越空。床上铺的锦褥,也许还是旧的,不舍得换,从前鲜艳的绣罗,如今蒙尘寂寞。相信古代有无数这样的女子,现代也依然有,不过现代女子的人生可以自主,至少不会走投无路,古代女子一旦跟了人,那就等于要仰望终生。五代北宋,写女子相思的词,作者都是男人,竟写得如此哀感顽艳,似乎比女子自己更懂她们的心思。当然,文学是想象,是梦的艺术,至于词作者会不会因为懂得所以慈悲,那是另一回事。名叫顾敻的词人,史书记载仅短短几句,我们得知他大约于928年前后在世,做过后蜀太尉,字、里、生卒年均无考。我认为这样很好,免却一切干扰,作者消失,只留下诗。

深夜梦回情脉脉

《归自谣》
(南唐)冯延巳
何处笛?
深夜梦回情脉脉,
竹风檐雨寒窗隔。
离人几岁无消息,
今头白,不眠特地重相忆。
笛声从哪里来?诗以问句开头,总给人以突兀之感,带着讶异,像一个谜。
所有故事都是谜,始于谜,终于谜。生活就像一棵树,枝上挂满许多故事,那些我们不会谈论的、如梦似幻的故事。
笛声来自某处,也来自回忆,来自梦中。深夜笛声,本身就是个故事。被笛声唤醒,脉脉含情,她梦见了什么?诗人没有说,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经验和想象去补充。
她感到一阵寒冷。窗外,竹风檐雨,似有什么在那里徘徊,在那里远去。隔着寒窗,她侧耳倾听,仿佛听见隔世的另一个自己。淹没这个时辰的雨声,使黑夜更黑的雨声,无疑属于过去。
“离人几岁无消息”,读到这句,我们看到故事的轮廓,也是故事的核心。很多时候,没有消息就是消息,没有回复就是回复。她心里明白,但仍在等待,“今头白,不眠特地重相忆。”她等到头白。不是相思令人老,而是等待,漫无尽期的等待,像茫茫大雪,落在她的发上。
特地重相忆,末句言外之意,即她接受了他也许已死的事实,或者她以为自己接受了,决定不再长相忆。而夜梦和笛声,以及竹声檐雨,忽把一切又带回来,梦中他还是从前的样子。
“特地”,这个略显生硬的词,与其说传递出她的努力,不如说传递出她的克制。相思无益,她不再经常想他,就好像他真的死了。深夜梦回,此时此刻,他却分明在这里,她不能再睡,她要用回忆把他留住,哪怕多留半个晚上。

《孤雁儿》
(宋)李清照
藤床纸帐朝眠起,说不尽、无佳思。
沉香断续玉炉寒,伴我情怀如水。
笛声三弄,梅心惊破,多少春情意。
小风疏雨萧萧地,又催下、千行泪。
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
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
李清照晚年这首词,写得散淡,好像坐在时间的外面,看花谢花开,岁序不言。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离合聚散,炎凉恩怨,都只是过眼云烟。
“藤床纸帐朝眠起”,起句平实,似听见窸窸窣窣。藤条编的床,纸糊的帐子,今天的读者也许感觉归真返朴,李易安写的其实是生活条件的简陋。
“说不尽、无佳思。”句式和声音,传达出欲说还休的无聊况味。早晨再次铺开,对于一个寡居的、上了年纪的妇人,还有什么值得期待?新的一天究竟是什么意思?
她仍然活着,活在熟悉的事物中间,与它们朝夕相伴。黑夜是繁复而隐秘的庆典,当她睡去,那些逝者,死别的,生离的,不速而至,出现在梦里,往日笑颜,往日衣履。晨醒,白昼再次展开,现实一望无垠,所谓世界,仿佛连绵不绝的围墙,生老病死永无止境地延续。
沉香断续,玉炉冰冷,夜梦消退之后,清晨像一个淡出的结局。李易安是个诗人,她有诗书,有花木,她仍爱着一切美好的事物,更可以写诗觉照自己。“伴我情怀如水”,水有愁,水有哀,水很安静,似她的情怀。
笛声三弄,她被惊醒。“梅心惊破,多少春情意。”笛声惊破梅心,记忆的闸门骤然打开,多少春情意,涌起在心里。她爱过,生活过,那些日子,就像春天一样烂漫,就像春天一样明迷。
梅花仍在开,故乡何在?小风疏雨,一片萧萧地。国破家亡,流离失所,身边没有一个至亲的人,晨起听见笛声,值此恶劣天气,怎能不伤心流泪。
真正衰老到一定时候,老年就不再是心态问题,而是一个简单的事实。退场就是退场,凄凉就是凄凉。赵明诚算不得神仙眷侣,但易安真是爱他,所以处处理解他,哪怕逃难途中,他独去湖州赴任,临别叮嘱若遭兵乱,则要她与那些祭器礼器共存亡。
赵明诚死了。死,一了百了,真是奢侈!李易安带着他收藏的书卷、金石刻、器皿等,数量惊人,四处辗转,不胜惶恐,最终还是散失几尽。易安性情豁达,如她所言,“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金石录后序》)她是为赵心疼。
她仍爱梅花,见梅花又开,她折了一枝。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可是她该赠给谁?“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人生至此,世界完全陌生,一片虚空。
想起意大利诗人蒙塔莱的诗,《也许一天清晨》,诗中写道:“也许一天清晨,走在干燥透明的空气中/我转身,看见奇迹的发生:/我身后空无一物,只有/虚空在我后面,带着醉汉的惊恐。”
诗人所说的“奇迹”,即他在某天清晨领悟的虚空。在诗的结尾,他说他将寂静地走在从不回首的人们中间,带着他的秘密。这个“秘密”,便是树、房子和山川,犹如聚集在屏幕上,这些幻影想要挽留他,但是太迟了。凡是看见过真相的人,绝不会再回到假相中去了。
瞥见虚空的诗人,从此将彻底不同。他走在人群中,无人认得,他活在世界上,却不属于世界。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三书;编辑:张进;校对: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文末含《新京报·书评周刊》2023合订本广告。

点击“阅读原文”
打开2024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入围书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