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艺谋:1950年4月2日生于陕西西安,中国电影导演,“第五代导演”代表人物之一。
正午:
《长城》在您所有的作品中是什么样的意义?
张艺谋:
这个电影应该这么说,对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这可能是走得最远、最广泛的一次。
我们说中国电影走出去,其实一直在说某种程度的空话和套话。电影节电影是我们认为真正的电影,有情怀有思想有格调,对于全世界电影有作用和各种思考的电影都在电影节,它们笼统被称为艺术片。第五代(导演)起步就是这条路。第五代赶上国家打开了门,在西方的主要电影节摘金夺银,直到至今。如果这条路是中国电影走出去的话,中国电影没有断过的。得奖之后通常在全世界的市场就会有很多人买,它推广就是艺术院线,或者买了之后直接转电视台等等,非常少的利润,但是卖得多,艺术片是这个情况。
如果没有另一种现象,这种情况还是会延续30年或50年。但大家不得不面对的另一种现象就是全世界艺术院线萎缩,好莱坞大片以压倒性的态势“一览众山小”。我们说中国电影走出去,全世界很多电影人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继续走,在审查制度下,能到什么程度就什么程度。但是我自己看,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胜利——宝莱坞除外。
我接《长城》完全是被动的。给到我手里,美国公司是试探,当然中国电影市场到了这个程度了他们愿意试探。我看完剧本,坦率地说是特别典型的爆米花合拍片的类型,我想了很长时间,觉得这个根本就不是我拍的东西。后来我的经纪公司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长城》只有一个价值,就是它有可能在全世界5000家影院上映,是第一部由你来做的一个大片。他提醒我了,我突然发现有一种可能,由中国导演作为创作核心,中国演员、中国故事作为构成,一个合作中美的大片,哎,也许很有意思,如果成功,那《长城》系列拍下来10到15年,完全可以培养出来一个大话题和一个大观众群。某种意义上这是文化走出去、电影走出去的绝佳时机,而且是一个实际的案例,说别的都是空话。
我自己给《长城》定义为是借全球大片传递中国形象,传递价值观,传递文化信息。从这个意义来说它是我电影当中独特的一部。我其实也是看上《长城》的这种功能了:借水行船。
正午:
如果没有美国公司来找您,您也会拍一部这样的电影吗?
张艺谋:
不会,我拍不了,没有这个投资。它是一个工业体系上的东西。受众最广泛的,主流院线的,年轻人最喜欢的类型,一直是我们中国电影的短板。其实这种类型是重工业,是核心竞争力。我们的市场固然很好,越来越好,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像宝莱坞,就是自娱自乐。所以人家七年打造剧本,我一同意,人家很高兴就要开拍,我又延了一年,我一定再改一次,把让我感动的和有意思的东西放进去,这样我才愿意拍这个电影。
正午:
您觉得他们在理解“长城”这个特别明确的文化符号上跟您会有冲突吗?
张艺谋:
人家讲的是商业类型片,老板托马斯是个怪兽迷,所以他就突发奇想长城打怪兽,很有意思。然后怪兽用什么呢?有人给他建议饕餮,也很有意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商业创意,我要改的是什么呢?是慢慢地去讲长城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精神地位,慢慢去讲这个战斗应该什么样子,甚至讲这个饕餮……我给了他一本英文版的《山海经》,我说你看我们这个怪兽,我们不要丢掉贪婪的用意。
这是举一个小例子。我希望突出中国文化的一些信息,就要沟通和调整很多东西,牵一发动全身,许多小调整会牵动整个故事的走向。这就是文化和文化的区别,但是咱们殊途同归,你是想着商业,我是想着载体,有没有可能大家一致呢?都希望它成功。
正午:
《长城》除了是怪兽片,最终它是什么?
张艺谋:
我个人认为是家国情怀。我认为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一代带来的就是家国情怀。
正午:
在这部电影中,有多少您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表达?
张艺谋:
你可以看电影。在这样一个工业化操作的流程下,我尽全力做满我自己。
正午:
我看了主题歌的MV发布,中间有若干镜头,它给我的感觉有点像您导演的奥运会开幕式。
张艺谋:
对电影的评价要看整个电影。看完之后也许你能感觉到我用心良苦,所有人都会感觉到我用心良苦,但是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它的价值,是不是所有人都欣赏?说不定还有板砖砸我,但是我自己希望能有好结果,而且做到这个,其实很艰难,就这么说,以我的江湖地位和韧性和坚持和包容,也是做满了,可能换一个人还会崩溃的。在这个市场上,在咱们的评价标准上和语境上,还会有很多批评的,但是这次我是想明白了,不会再像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那么纠结,我只是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机会,对中国的电影,中国文化的信息传播也是一个机会。
正午:
但这个过程中,您要服从各种商业规则,这个所谓文化的传递可能会有偏差,您有这个担心吗?
张艺谋:
当然。这就是两种文化的碰撞,即便是在这种全球大片的类型化上,也有文化的不同。所以首先要了解规律,顺着规律走,什么叫借水行船,你别上来就修水库改航道,这个事情就太累了,对方也不干。顺应潮流,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做法。
正午:
您担心它最后变成一个两头都不着边的东西吗?
张艺谋:
那要看市场检验了,它首先是一个市场类型的电影,要让市场检验,这个谁也不能预设,我能想到的,我能做到的,我尽量把它全身心地投入,很诚心诚意地去做就完了,结果谁都无法预测,这是第一。第二当然是一个开始,希望成功,成功了以后就会下一部,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好莱坞六大公司会来找王艺谋、李艺谋,更多地开发中国故事,这不是好事情吗?但是这个要交给观众了。我们为什么在中国先发?我们希望中国观众捧场,中国观众捧场了是一个好的开始。
 《长城》工作照。
《长城》工作照。

正午:
对于您个人的作品而言,您把艺术电影和这种专门面向商业的电影分得很清楚吗?
张艺谋:
应该分清楚。电影是要分类型的,对电影的评价也是要分类型的。对商业电影大谈思想深刻性,大谈批判现实主义可能是不对的;对艺术电影大谈赏心悦目,大谈走进大众也是不现实的。电影分类型我觉得是基本,评判标准分类型也是基本,不能一锅烩,没有天才的导演什么都拍得好,也没有天才的作品,什么都面面俱到。我们俗话说的雅俗共赏是很难的,雅要大雅,俗要大俗,那多难啊!那是至高境界,那是我们的追求。一个导演接一个活儿,拍什么类型你先弄清楚这个,这也是为投资负责,为这个产业负责,其实我每次都是比较清楚的。
正午:
您在每拍一部电影之前都会先想清楚这件事吗?
张艺谋:
对。你打算拍这个电影,还不想好你要拍一个什么电影吗?这是第一步就要想好的。比如,你要不要拍一个低成本小制作,但是它可能在文艺上面有点独特性,说得俗一点,有可能让你去得奖,功名利禄帮你挣一把,做吗?可能没人看,可能“一日游(编者注:指院线排片率极低)”,你想好这些以后,自己觉得要拍,你就拍,你拍了以后又抱怨,凭什么不给我排片,凭什么大家不捧场?又开始要求另外的东西,那还是没有分清。我觉得军走军路马走马路,在这一行其实特别清楚。在评判标准上,在欣赏角度上,在制作流程上都要分类型,这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一个成熟的工业体系。
正午:
就您个人而言,每部作品拍之前,您的动机是来自于哪里?
张艺谋:
《长城》让我有动力的就是我想要做的这个事情。
正午:
之前呢?像《十三钗》,以及《英雄》之后的作品。
张艺谋:
那些不是这种全球大片的类型,在原则上,我都是按文艺片拍的,甚至《英雄》,它最早就是一个文艺片。《英雄》我很早把剧本就打磨出来了,结果《卧虎藏龙》大获成功,我都想放弃了,我说李安拍《卧虎藏龙》这么火,我再拍这个,人家觉得我跟风,算了,放几年再说吧。后来江志强找我,他说导演还是拍拍,现在市场好。那好,那就拍,这是文艺片的架构,是我自己喜欢的那点所谓武侠。然后江老板就告诉我,梁朝伟要吗?可以吗?张曼玉要吗?还有李连杰,真的吗?还缺一个配角——甄子丹。这全是他提议的。我说可以吗?江老板说,市场好,《卧虎藏龙》打开了很大的局面。我说很贵的,成本很高——可以呀!就是这样子拍成的,但其实我拍的整个过程是一个艺术片的思考,那个时候不知道成了商业大片的一个开门之作。包括《金陵十三钗》也很简单,那是一个艺术片,不是《长城》这个类型。《长城》很简单,一个打怪兽的,又是这种大公司,它的标签很清晰,你接不接是看你自己了。
正午:
您认为《长城》有可能成为大IP电影,不停地拍下去吗?
张艺谋:
要看成功与否。我希望中国观众捧场,我也希望外国观众捧场,最后有五亿人看了《长城》,知道了中国长城了不起,这是多好的一个事情!我当然希望是这样子的。
正午:
对您个人而言,这是您接下来想做的事情吗?
张艺谋:
我不去想那么远。我是碰到什么拍什么,只看到自己是不是喜欢,当有这个机会找到我的时候,我是经过思考的,我愿意做这样的尝试,这完全就是因势利导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说我从此设定以这个为目标其他啥也不拍,那不是有病吗?天天想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那就是空的。对导演来说,当有一个可能性的时候,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方向进入,有空间就行,就是这样。
正午:
您很早期的作品像《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那其实也是中国电影走出去让世界看到的一种方式。
张艺谋: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这样的事情我们做了三十多年了,也小有建树,但这种类型的空间有限,那有另外一个空间,你要不要尝试?
在全世界除了反恐战争之外,不会有世界大战的情况下,我认为目前步入了消费时代或者娱乐时代,好象大家都在变浅薄,不像30年50年以前,电影探讨那么多内心世界,有那么多的流派,孜孜不倦地开拓——电影当年承担了这样的任务,是非常高端地探讨人内心精神世界的一个方式。发展到今天,可能是电影整体流俗了,不仅仅是中国。又深刻又人文又反思又能批判,而且拍得非常地道,这样的电影全世界每年也就三两部,有时候一部都没有。用电影做前卫性的开拓,前锋性的开拓,思想深度的开拓的时代过去了,那么做没人看,也没人拍,现在是这样。
正午:
您还想拍那样的电影吗?
张艺谋:
想啊,我是那样成长过来的啊,那是我的最高目标。只是现在机会越来越少了。还有,坦率地说,空间也少。在中国的创作环境中,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国情比不过外头,这种题材都是批判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就是深刻,无论是政治、社会、文化,乃至人类本身,这些都是广义的批判现实主义,唯有批判现实主义才深刻。我们特别知道这个,但是批判现实主义在中国极难拍。
正午:
《归来》算是?
张艺谋:
算是,已经很难拍,我认为那是我能做到的最大化。
正午:
《归来》也被批评“避实就虚”。
张艺谋:
那是在中国站着说话不腰疼,我想怎么拍怎么拍,可能吗?不存在,有可能投资都撤了。这方面的空间非常有限。
正午:
如果避开?
张艺谋:
避开就无法那么深刻。
正午:
《路边野餐》您看过吗?
张艺谋:
我听说了,但是没看。中国年轻导演都在尽自己的努力表达自己的认知,这些东西很重要,而且应该是一代一代这样的。我们还是这样的现状,在创作上有很多的限制。做任何事情都应该讲究最大化,但是做不到。
正午:
您更多还是从文学作品中找题材?
张艺谋:
当然,文学作品我认为是母体,全世界也是这样。文学的思考高度和文学的现状可以从电影中看出来。母体要非常有营养,非常百花齐放,导演才能发挥。导演是一个简单的职业,是一个工匠,是用影像讲故事的人。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做好,母体就是剧本,但好剧本的来源太难了,归根到底就是创作性太难了。
正午:
对于一个创作者,尤其是像您这样非常成熟的创作者而言,您会找自己最有感觉的地方去创作吗?
张艺谋:
对,我要给自己一个动力,一个发动机。李安是我的老朋友,他的“120帧”是他的发动机;小刚也是朋友,他的圆(画幅)是他的发动机。导演都要找一个发动机,让自己调动,让自己有激情,成功与否不重要。这就是我们这一行最基本的创作规律。这个发动机不是纯技术,是很直观很感性的一个东西,当然,中间慢慢地它会有一些调整,但是发动机的初衷就是创作的原动力,并不是说我今天想拍一部电影,没有那么简单。刚出道的时候,有许多年轻导演为了扬名,为了站稳江湖地位,有可能先拍一个,我先表现我有这个能耐,这是讨饭碗,这时候是不加选择的。但是成熟一点的导演没有发动机,怎么做呢?其实创作没有任何神秘,没有任何伟大,也没有任何高下之分,每个导演有感兴趣的就来做。
正午:
您会担心有一天找不到发动机了吗?
张艺谋:
不会的,这就是创作,创作就是你永远会有。像童心一样的,你永远会有你的追求,它是无限的,这是一种心灵规律。
正午:
您在拍电影的时候最享受的是什么?
张艺谋:
就是实现我这些目标的过程。很多很多时候是为了整个大局,但是有一场戏你会很欣赏,有一段你会很欣赏,因为你认为你那个初心、那个发动机在这个地方表现得最充足。当然有人有时候跑偏了,特别想表现得很充足,把这个东西刻意放大,这就变成矫情了,变成雕琢了,刻意了。拍一个好电影,我自己认为有三大要素,有运气碰上一个好剧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选对了好演员,演员最重要,TA对人物和故事做最生动的诠释,是TA,不是你。第三个做对了你自己,就是你在这个电影中做的所有的决定没犯大错,全对上了。这三大要素结合起来,旷世大作出来了。但是它是很奇妙的,三个都要碰上。
正午:
像《长城》这样的商业大片,这三部分都在您的把控范围之内吗?
张艺谋:
我不拿这三个套,这三个是最高标准。首先碰上一个好剧本,《长城》是这种类型电影的剧本,不是我的选择,所以首先我不敢说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选对好演员,有可能。第三做对我自己,那是一个太复杂的过程,导演在整个电影的创作过程中要做一万个决定,适合不适合,对和不对,许多这样的问题,都回答对了吗?还有外部的原因,还有力所不及的地方,还有自己要妥协的地方,还有无奈的部分,不是由你来掌控的等等,尤其是像这种大电影就更复杂了。我怎么可以今天回答你,我做对了所有的事情。
正午:
您以往的所有作品中,您觉得最接近这个理想的是哪部作品?
张艺谋:
我自己当然还是大家公认的几部,比如说《秋菊打官司》,比如说《活着》,比如说《大红灯笼高高挂》,比如说《红高粱》等。全世界的好电影,不管类型——商业型、艺术型、个性的、独立制作、大制作都无所谓,但是全世界的好电影它这三个部分都要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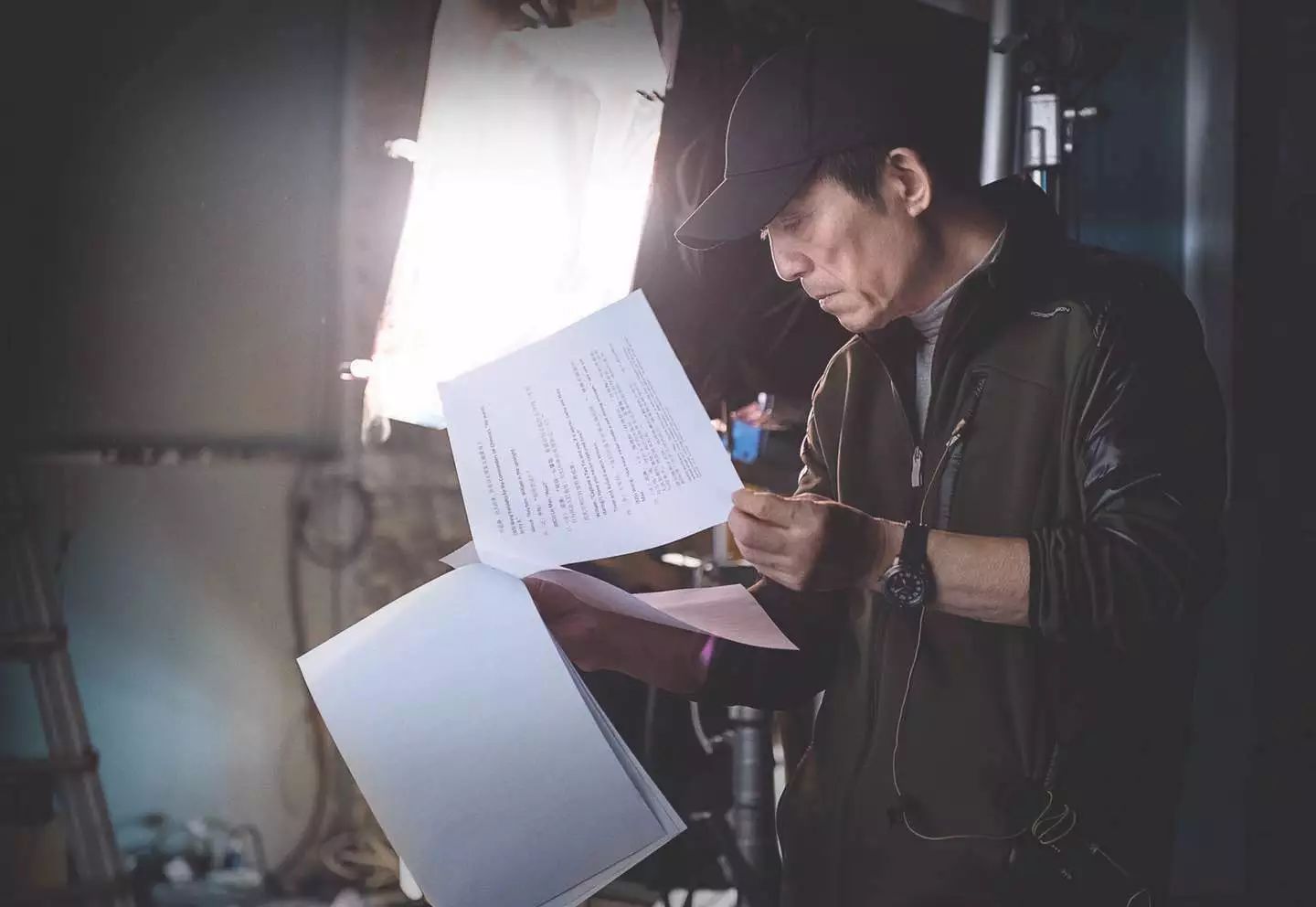
正午:
您认为您是一个“作者电影”型的导演吗(编者注: 作者电影Le cinema d'auteur,指在影片制作的种种环节打上导演个人的主观印记,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影片)?
张艺谋:
你怎么定义作者电影?我认为所有的电影导演都是作者之一,因为导演是用影像讲故事的人,电影就是影像。但是如果必须是编导一体,那不是。
正午:
您并不想做一个完全只考虑自我表达,不考虑其他东西的导演?
张艺谋:
我从来不是那类人,何苦装成那样子?我不是那类人的原因是成长环境和所有方方面面决定的。像欧洲的很多作者根本就不屑你,什么也不出席,你说什么不带理的,他觉得理你都是耻辱。他拍完电影以后到岛上自己想事去了,如此的高傲,那态度很坚决的。我觉得这样的人中其实有很多真的是艺术家。艺术家是什么?极端的个性。根本不能合群,有了合群的想法就不是艺术家。像那么极端的艺术家,我当然不是了。我们的成长环境和教育体系让我们这类人都是集体主义的。也许未来,2000后或者2010后有很多桀骜不驯的个体艺术家,但是我认为这种艺术家最好别做电影,最好去写书写诗画画。电影就是要交给大众的,你要以大众为庸俗的话就没有办法做。受这罪干什么?所以我相信要是那样强调个性和个人抒发的话,那应该是去做作家画家之类,那是非常个人的。
正午:
您在开始做导演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把艺术家当成自己的理想,是吗?
张艺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