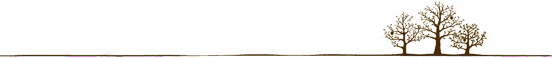

老话说,一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排在首位的为柴火。是呵,若是没有了柴火,哪来的饭热菜香,美味佳肴?

先前,人们日常生活所烧煮用的柴火,多为柴爿、树枝及茅草一类。记得小时候,尽管居住的房子不大,但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硕大的柴仓,里头堆的都是柴火。柴火分为几类,一类是引火用的茅草柴,或是木匠刨木料时产生的刨花;一类为易着火的木柴,称为柴爿;还有一类属于不易着火的硬柴,比如树枝、树根或是藤蔓,其密度厚,虽不易着火,但耐烧。

每天火一升起来,人们想的就是如何节省,通常会将着火的木柴,架在铁锅的中央烧,这样火力集中,无论煮饭烧菜,都能加快速度,节省不少柴料。凡是尚未燃完的木柴,则把它插进灶台的灰塘缸中灭掉,待下次续用。边上还备置有一个炭缸,将成炭的柴火,用火钳挟进缸,一盖,断了氧气,日后也都是上好的燃料。过去的灶台,一般有两眼,分别叫大镬小镬,大的煮饭,小的烧菜,两者中间安有一个铁铸的汤罐,不论哪眼镬升火,汤罐里的水都能够烧热,可用来洗碗、洗脸、烫脚等,这种的节省,或许被现今的人所不屑,但这种节约能源、利用到极致的方法,还是很令人赞叹的。

那时节,每天都有走街串巷挑担进城卖柴的农民,一担好柴,从山上斫下来,又用船载到温州城底,再挑到大街小巷上叫卖,几多的劳累,换来的顶多也只是一二元钱。从我家门前那条小巷走到底,再一个右拐,那里便是瓯江上一个极好的避风港湾,人称东门浦。靠左向的叫浦边,而靠右向的叫浦口,那里面歇了好多从永嘉楠溪或是青田、龙泉来的舴艋船儿,带来的都是山底角的货物,比如香菇、木耳、干笋等等,木柴也是其中的主要货源之一。我父亲是个极其节省的人,每当柴火即将烧完的时节,总会带上我们兄弟几人直接到东门浦去买柴。在这里可以有所选择,一番讨价还价后,总能买到货好价格便宜的柴火,况且还可以扣除运输费,多多少少能省一些小钱。

柴火斤量多少,是用大杆秤称的,若是干燥了,卖的人不合算,因而买过来的柴火一般都比较湿,不能着火,得放在太阳底下晒一段时间。有回,一连下了十几天的雨,我家的柴火断了,可新买的还是湿的,不能着火,而天又不见晴,怎么办?还是父亲有办法,通过关系,从附近一家单位食堂里购买了几天的饭菜票,总算渡过了难关。不过,那几天是我们初吃食堂饭,感到大锅饭好吃,特别香。我有朋友在龙湾,他说,那时在乡村,用柴火更加困难,附近山上的基本被砍光,有时为了斫柴,得跑到好几里外的地宕,为此与人打架是常有的事。
大约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左右,城区居民购物本上岀现了煤球票,并开始有了煤的供应。虽然按户口人数,家家户户都有煤球供应,但那时经常断电,煤球生产供不应求,尤其到了年关,供应更加紧张,什么时候有不确定,煤球一运到店铺,近水楼台先得月,很快就被周边的居民抢光了,待离店铺较远的我们上气不接下气急忙忙赶到时,早就断了货。于是只好整日整夜到煤球店去排队,好在那时家里人口多,上半夜一个,下半夜一个,兄弟姐妹几个轮流去排队,但这种守株待兔的办法,也不一定管用,运气不好,有时一连好几天都没有。最可气的是,待你将箩筐什么的刚刚搬走,运煤球的板车过来了。

煤球和草木料两种柴火相比较,煤球方便了许多,一次升火后,无论煮饭、炒菜、烧水等,都可以连续用上一整天,而且比之价格还要节省一些。尤其明显的是,先前硕大的柴仓不需要了,一下子腾出了许多空间,厨房变得宽敞了。但烧煤球虽说是方便,早上升火很麻烦,首先是不易着火,得用许多引火的东西,然后还要持续不断地用蒲扇使劲扇;其次是在扇的过程中,会有呛人的浓烟和气味叫人受不了。因而一大早,好多人都将家里的炉子搬到宽阔的街上去升火。那时城区的大街小巷,到处是“云雾缭绕”,到处是咳嗽声。

后来有人发明了蜂窝煤,把煤制作成了圆形的蜂窝状,这方法着火容易,火力猛,燃烧久,而且不用天天烧火,实在是方便和经济。这样一来,传统的镬灶成了单眼,厨房的空间又变大了。那时工厂上班不正常,蜂窝煤供应不上,许多燃料店只卖未加工的煤粉。好在温州人会动脑筋,每家都会自制一个做蜂窝煤的工具,先将煤粉拌均匀,加上少许的水和黄泥粉后,装进工具内,使劲地敲打,然后将工具外层往上一提,一个圆形结实的蜂窝煤就出来了。我们这般年纪的人,都干过这活儿,叫“捣煤球”。

再后来有了煤气罐,没有了煤尘,也没有了呛人的气味。如今城里人又用上天然气,不仅清洁,生火就好比开水龙头一样方便自如。想想,这真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我们,连做梦都梦不到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