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理︱袁剑
5月20日,“一带一路的边疆实践:拉铁摩尔、中国与世界”暨《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出版座谈会在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举行。本次座谈会由中央民族大学袁剑和陕西师范大学黄达远召集,北京大学唐晓峰、昝涛,清华大学沈卫荣,中国社会科学院许建英、宋培军,中央民族大学李鸿宾、张海洋、关凯,上海外国语大学杨成,外交学院施展,新疆大学程秀金,陕西师范大学李如东等学者参与现场讨论。讨论的前一部分内容已经以
《拉铁摩尔与“新清史”在中国为何会引发不同的反响?》
为题发表,以下是第二部分的主要讨论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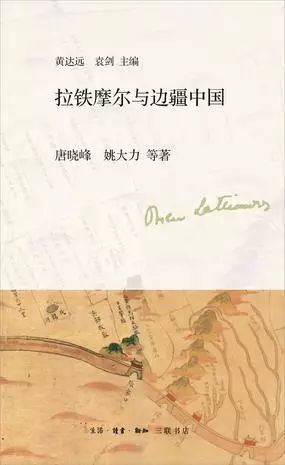
《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
━━━━━
许建英:
整合与差异的共存
━━━━━
从研究边疆这个角度来看,这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是生逢其时。因为我是长期研究新疆的,所以知道拉铁摩尔与新疆研究渊源很深。最早接触到他是在关注近代以来西方(包括日本)对于新疆勘查的相关研究中,接触到他的《亚洲的枢纽》《高地鞑靼》等作品。后来我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访问,见到罗威廉,他也讲了很多关于拉铁摩尔的事情,虽然他本人是研究清代内地问题的,但对拉铁摩尔非常感兴趣,所谈的也非常有启发。我在2006年到英国利兹大学访问,还曾专门听过那里收藏的拉铁摩尔留居期间的录音。
美国的新清史在中国形成这么大的反弹,在我看来,这种反弹是对清末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认知层面差异的体现。我们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一般强调的是整合与统一,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同的面向,即便是清朝政治结构本身也不是单一的结构,期间经历了不同的演变阶段,与此相应地,中国的边疆地区也存在不同的特征,而中国内部的这种复杂多样性在以往我们一百多年的主流叙述中被忽视了。
从历史层面来看,我认为内陆边疆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海疆的影响,不能因为近代的坚船利炮打破了我们国家的传统和优势而放弃对内陆边疆的关注。我们称作“内陆亚洲”的边疆线是我们不能忽视的,而“一带一路”新战略的提出,也是我们非常重大的一种平衡和转换,让我们注重到陆-海双向发展的重要性。
━━━━━
张海洋:
长城线与“长征线”构成中国的新认知
━━━━━
边疆议题实际上是中国问题的折射。我们对边疆议题的关注需要我们从整体的中国视野下来考量。如今我们继承了清朝的疆土,同样也继承了这片疆土上长期以来所具有的社会文化生态,以及广袤的边疆区域,因此,了解和认知中国内部的复杂社会文化生态和边疆区域,依然是我们需要努力的任务。
拉铁摩尔的贡献在于,一方面,他弥合了西方学界当中汉学、蒙古学、藏学等将中国内地与边疆割裂开来的认知框架,从整体上形成对于中国边疆的认知,并在基础上构筑更具整体性的中国认知框架。这是对西方学术框架的超越,也是对原有的中国认知的超越。另一方面,拉铁摩尔对中国边疆区域的重视,也恰恰是当时中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生态的体现。拉铁摩尔所重视和关注的中国内陆边疆地区,既是历史上的长城地带,同时也是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区域,这是长城线与“长征线”的聚合,正是在这里,我们的革命先辈们获得了比国民党领导人更多、更全面的对于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认知,认识到了边疆民族地区在推动全国革命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力量,对此,我们也需要“不忘初心”。在另一方面,拉铁摩尔对中国内陆边疆地区的实地调查和研究也提示我们,从古至今,中国内部都存在着复杂性,不管是在唐代,还是在清代,用单一的内地模式都无法有效地治理边疆地区,在边疆治理方面需要我们有更多的智慧。

拉铁摩尔
━━━━━
关凯:
超越民族与民族主义
━━━━━
边疆的政治性是不言而喻的。赛义德认为,如果我们脱离知识包含的政治隐喻,完全去政治化,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谈问题。
拉铁摩尔给了我们提供了一种反思的可能。在传统的历史话语中,我们往往是轻视游牧社会的,但这是在民族中心论下出现的,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则是民族国家的竞争,它已经超越了民族本身。如果我们在更为一般的历史维度上来思考的话,就会发现,即便是在司马迁的时代,不仅中原地带存在着对游牧的轻视,在当时的世界其他地区也存在对游牧的歧视,我们不能将其跟有目的的书写传统相提并论。长城内的歧视长城外的,西方歧视非西方,甚至西方思想家眼中的亚洲没有历史,这些都需要我们反思。如果还原到拉铁摩尔,他最大的还是在史学方面的贡献,他发现内陆亚洲存在着某种“中央性”,这一区域与周边文明的互动是有各种历史记载的,而以此所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天下体系,他是在这个史观下来进行叙述的。
在拉铁摩尔看来,工业化最终消解了农耕与游牧之间的界限,同时也使长城成为兼容内地与边疆的中心所在,而实际上,在这背后真正支配我们的是历史哲学,是黑格尔。中国总是在反复中前行,中国这一文明受到了来自里里外外的太大压力,拉铁摩尔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视角,也给我们以反思,去更好地认识农业文明的史观,并更好地面对工业文明的新挑战。新清史的研究本质上是一种“乾隆学”,而拉铁摩尔给我们的另一个贡献是,面对这些隐喻性问题,我们能不能超越民族和民族主义,进而构筑起更大的秩序和知识架构。这是因为,当今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的历史叙述,实际上正带来更大的后续影响。
当然,拉铁摩尔理论的负面性也是存在的,那就是对边疆史的过简化叙述,他将一个具有丰富多样性和内在实践的阴山区域简化为一个中心和平面化地带,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
━━━━━
杨成:
世界体系中的平等性问题
━━━━━
很荣幸参加这个讨论会,我不是专门做历史的,只能从国际关系的视角做些观察,谈些浅见。
对我来说,如何从拉铁摩尔的研究中找到中国传统的一些思维方式,是一大要义。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被迫打开国门的中国开始先学器物,再学思想,一直到当下作为过程和结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始终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的深刻影响。而在这过程中,我们对边疆地区和游牧社会的认识,在相当程度上是被忽视的,在华夏性和内亚性相互塑造、相互建构问题上,后者的主体性至少没有被充分意识到,这不仅影响了历史书写,也内在地规制了我们的边疆治理和周边外交的理性、手段和战略内涵。至少从国际问题研究的视角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很长时间内更多只有对大国的外交,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外交。这一倾向在改革开放以来表现更为突出,体量和影响力不大的中小国家在中国外交的整体布局中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关注,这跟我们的战略资源相对有限有一定关联性,但多数情况下可能是战略视野以及大国小国身份并存的实际结构的限制所致。这跟我们当初忽略游牧社会在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建构中的作用有类似逻辑。
正在进入加速推进阶段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传统的天下秩序是有区别的。根据历史学家而非历史哲学家的研究,传统的天下秩序框架内国与国并不是一种对等的关系,自内而外的圈层等级结构构成了这种秩序的核心机制,华夏中心主义是很显而易见的。因此,对我来说,作为方法的拉铁摩尔的相关研究意义尤为重大。他让我们关注到外部世界与中国的相互适应、相互塑造问题,也启示我们当未来的国际秩序因中国的成长而被重新界定的同时,中国自身也被加入这种秩序的进程和结果而定义。换而言之,“一带一路”的推进要避免中国中心论的思维,要意识到至少在近代以来外部世界对我们的塑造作用大多数情况下要大于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影响,“一带一路”提供了修正的机会,但如果以中国中心论取代西方中心论,就有可能滑入新的陷阱。这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
昝涛:
共享历史如何书写和呈现
━━━━━
拉铁摩尔的议题让我回望自己所关注的土耳其议题,共享历史如何书写和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