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着弗拉基米尔,看了一部拍摄七年,创下了俄罗斯电影票房最高纪录的史诗片:《维京·王者之战》。
乍一听这个名字,像一部奇幻片,但它是讲的是弗拉基米尔的故事。中国观众对这个名字或许不熟,但这个人在俄罗斯文化中算得上是家喻户晓,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唐宗宋祖。这么说吧,普京老师的大名,就叫弗拉基米尔。
有趣的是,普京老师本人还很喜欢这部电影,接见了剧组,还二刷。
它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
讲了一个世人觉得很牛逼的男人,一个战斗英雄,内心深处很苦逼的故事。

他是俄罗斯(那时候是叫基辅罗斯)的领袖,从战斗中成长起来,一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内心深处却很痛苦,直到皈依了东正教信仰。
让我感兴趣的,是这种人脆弱的一面。
他是战斗民族公认的英雄,对吧,很容易想象,首先是要能打。这个弗拉基米尔不是太子,又是庶出,本来是被分封到边远地区养老的。后来一路打啊打,还找来维京人一起打。维京海盗大家知道,也很能打,双方有点英雄相惜的意思,就一起打啊打,打到基辅去。一路上几乎战无不胜。看不起他的美女也睡了,继承大位的哥哥也被他给捅了。于是就像李世民一样,顺理成章坐上了大哥的位置,当上了战斗民族的领袖。然后又向外打,打出了国际声誉,还跟拜占庭的皇室联了姻。
这样的故事是不是很燃?
——理论上是会很燃。但这个故事不太一样。
因为这个角色从来没有流露出爽到了的感觉。在别人载歌载舞狂欢的时候,他一脸的忧世伤生,好像在说:「一个月挣一二十亿的人,其实是很难受的。」他在被什么东西裹挟着,身不由己地往前走。他的眼神一直是这样的:

不好意思放错图了,是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

电影里甚至都懒得给一个他登基加冕的镜头,随随便便就北境之王了。坐上王座的那一天,我估计要是有人采访他的感受:「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他会
45
度角望着天空:「也不是……」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
他忧伤地叹一口气:「不知道……」
为什么给人感觉很无辜啊!
你几乎要觉得他是一个受害者了。但是你又知道,这是一个最不无辜的大佬啊。所有杀伐决断都跟他的欲望脱不了干系。要真的什么都不想要,一开始就不要搞事啊!在自己的封地上好好活着不好吗?是谁非要踩着别人的尸体往前走这么远!
他其实很渴望,渴望王位,渴望被爱,渴望征服,但他也很痛苦。
他的欲望是真的,他对欲望的厌恶也是真的。
所以就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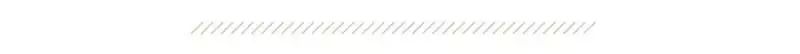
如果抱着看一部爽片的心情看这个电影,你会看到史诗级的大场面,看到恢弘的战争特效,看到波澜壮阔的征服史。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它前半段的情节,比任何
YY
小说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你看着看着就会意识到,这个故事要复杂得多。
这是一个沉闷的男人,沉闷地面对自己两手的血腥。
弗拉基米尔后来皈依了东正教,不但自己受洗,还强制他治下的人民受洗。这是电影的后半部分。前半部分的主线是征战,后半部分的主线则是弗拉基米尔个人的精神冲突和救赎。于是就要谈到一个关键概念:
信仰
。

这可能是故事真正想表达的东西。
信仰这个概念,是中国观众不大熟悉的。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听到前面的人说:不就是一个基督教的宣传片吗?——但信仰的本质,却不完全是宗教。
信仰是一个把自己交出去的过程。
并不是说,因为我做错了什么,所以我特别矫情地想找一个「他」,来原谅自己。而是说:真的是「我」在犯错吗?我的错从哪里开始?我有选择吗?
不妨设想这么一个场景:一个人在玩手机游戏,操作着一个角色。这个玩家在替角色分配技能点,决定他去哪幅地图,经历怎样的冒险。现在的问题是,假如游戏角色具有思考的能力,他以为自己的一切行为,都是出于自己的意志。那他会不会有一天意识到,自己的意志背后,
存在一个更大的力量
呢?
他要怎样才会发现,自己只是一个角色,只是在顺应另一个人的指令?
——这就是弗拉基米尔遇到的问题。
电影里没有明确表达这个问题,但是或多或少地,流露了这个意思。弗拉基米尔的痛苦在于,在他遭遇这个问题之前,他一直相信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人。弗拉基米尔就是操控弗拉基米尔的玩家本人,除此之外还能是谁呢?我就是我自己。
那时候他也有信仰,信仰的是多神教。但他的信仰是工具式的,借着「贿赂」他的神,来获得某些超出人力的力量。他知道,人不能掌控命运,所以他要通过神,掌控那些超出个人掌控的事,譬如战争走向,人心向背。他的神是原始的,蛮荒的,也是工具化的。祭司告诉他,神无所不能,条件是他要给神提供活人作祭品。
这个电影最动人的一段情节,就在于弗拉基米尔试图终止那个祭祀的仪式。但他根本做不到,因为所有人都信神。他徒劳地对抗潮水一样的信众。虽然大权在握,但那一刻他意识到,他的权力只是因为别人相信他。离开这一点,他什么都不是。
这是他第一次努力想改变一点什么,却失败了。他染上了更多鲜血,光荣和罪孽都增加了。他被人崇拜,被人诅咒,被山呼海啸的民众簇拥。
但他只是一个木偶,什么都控制不了。

献祭,是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很多人试图用这种古老的仪式,跟他们心中的神明做交易。我们奉献出去一些东西,请求回报给我们一些额外的恩典。
这样,就对那些无法掌控的事物,获得了一层掌控感。
今天,有人或许会觉得这样的想法很幼稚。但不要忘了,那是一个蛮荒时代,北境的男人们裹着厚厚的毛皮,挥舞刀剑,像熊一样鬼吼着,厮杀来厮杀去……他们并不具备我们那么「科学」的头脑,来理解他们经历的一切。
更何况,今天我们就真的确定,自己没有这样的想法吗?
有人说,中国人已经没有信仰了。这话不对。只能说我们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信仰。要是中国人没有信仰,不相信有别的东西能为我们的生活做主,岂不是个个都成了神?但我们明明又很焦虑,知道生活中有太多我们无法掌握的事情,甚至连孩子在幼儿园里能不能保证基本的安全,我们都没法掌握。所以必定还有比我们更高的力量,在替我们做主。——这就是说,我们也是要信点什么的。虽然未必能指名道姓,说是漫天神佛中的哪位高人,就说是「命」好了。
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对命和各种巫卜之术,开始有些半信半疑了。但心里还是有些不安稳,就要找一点别的东西,占住自己的心。
有人信仰「金钱」之神,相信只要多挣钱,就可以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很不幸,最近两起幼儿园的事,让这个信仰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有人信仰权力之神,相信权比钱更管用。
有人信仰科学,相信一切疑惑都可以在「科学」中得到解答。
有人信仰自律,他们日常的仪式就是自我约束,把尽可能多的时间作为贡品,献祭给学习和工作一类的「正经事儿」,认为这样就能过上好日子。
有人信仰人脉之神,只要朋友遍天下就什么都不怕。
有人信仰成功学之神,相信多花钱,多买课,就可以获得速成的幸福。
有人信仰下一代,希望对孩子善加栽培,实现全家的阶层跃迁。

通过这些信仰,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把一件自己掌控不了的事(命运),转化成自己可以掌控的生活方式(仪式),我们相信,依靠这种看不见的护佑,会有一种力量应许给我们福祉。我们便可以解除焦虑,享受自由,更幸福地活在当下,这本该是信仰的好处。但有时我们过分地狂妄,妄想通过献祭的仪式,征服生活本身。
结果是把一件自己掌控不了的事,转化成掌控不了的更多事。
过去的书上说,有那信佛的老太太,信奉不杀生,以为那样就可以有福报。这本来是让人安心的想法。谁知老太太把它发展到极致,连身上的虱子都得轻轻捉,生怕捏死,捉下来还得小心翼翼地养着,生怕饿死。——后来虱子真的死了,老太太很惊恐,以为自己又在无意中犯下了恶行,必被菩萨降罪云云。
信仰成了束缚。她为信仰的献祭,反而变成对自己的折磨。
今天的年轻人,把浪费时间当做恶行,由此背负了更大的压力,步履维艰,他们也是被信仰束缚了:越焦虑,越拖延,越惊恐。「努力让人进步」这句话,本应是让人安心的教义,现在反而变成了多少拖延者的紧箍咒。
所以信仰不一定给人解脱。我们从当初的信命,到今天的信努力,信计划,信时间管理,信成功学,绕了一圈,还是把「命运牢牢地抓在双手」,也很难说是进步或倒退。但是从心理意义上,我们献祭了更多,是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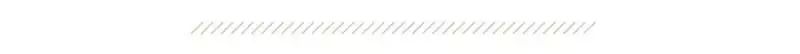
真正的信仰,是放下。
《维京》这部电影的后半部分,探讨的就是这个复杂的主题。它没有用最容易的方式去讨好观众。不是抒发情感,也没有说教人性,更不是像《血战钢锯岭》那样,通过一个外显的「神迹」去印证主角的选择。它只是在呈现一个普通的人,日复一日地提出没有答案的问题,而最终用自己的方式得到了答案。这种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