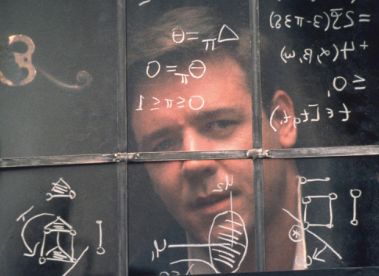
1939年9月,二战爆发,纳粹治下的奥地利局势动荡,一位33岁的维也纳人因为“长得像犹太人”,在当年11月遭到一群纳粹党徒攻击。
年底,接到征兵令的这位维也纳人意识到,必须跑路了。他和妻子踏上了一场长途逃亡,先辗转来到莫斯科,再经西伯利亚铁路横跨欧亚大陆,从日本横滨登上了开往大洋彼岸的轮船。1940年3月,终于抵达旧金山的维也纳人心情大好,写信给自家兄弟:旧金山绝对是我见过的最美城市。
不过这还不是旅程的目的地。稍加整顿后,夫妇二人又经太平洋铁路横跨美国,到达了真正的终点——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一趟旅程横跨两个大陆,值了。
更应该感到“值”的是美国。这位33岁的年轻人,就是在入籍仪式当场指出美国宪法漏洞的著名数学家
哥德尔
。
哥德尔只是当时因战乱移民美国的众多基础科学家之一。
希特勒给罗斯福送上的“大礼”包括但不限于:
爱因斯坦、爱瓦尔德、奥尔、波利亚、德拜、德恩、费勒、费米、冯·诺依曼、弗朗克、佛里德里希、冯卡门、哥德尔、海林格、柯朗、兰德,勒威、纽格堡、诺德海姆、赛格、塔斯基、外尔、魏格纳……
没有这群天才,
盟军破解纳粹密码的进程不会那么快;
美国也可能没法这么快完成曼哈顿计划,投下一锤定音的原子弹。
更深远的影响发生在战后。
40年代,费米设计建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核反应堆芝加哥1号,奠定了日后核电产业的基础;50年代,冯·诺依曼帮助IBM第二任掌门人小沃森完成了第一套存储程序计算机701的开发,开启了美国制霸电子信息技术的辉煌;同一时期,战后从英国移民而来的晶体管共同发明人肖克利创立了仙童半导体,该团队的骨干诺伊斯、摩尔等人后来出走,创立了另一巨头英特尔。
此后,在科技上长于应用而弱于基础的
“二流暴发户”美国一把翻身
。
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成了基础科学的圣殿,全球顶尖人才开始源源不断涌入这个国家——这是美国近80年来高速发展的最大护城河。
大国崛起,必然伴随着基础科学的崛起。
80年轮回,又一个风云变幻、高压弥漫的时刻。
过去数十年,迅猛发展的金融和信息全球化,已使
大型跨国公司及其代表的工业界
日益成为重要的权力实体,站到了新一轮争端的舞台中央。
当地时间 5 月 15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华为加入“出口禁运”实体清单
(即美国企业需要获得特别许可才能向华为出口软硬件产品)
;上周三中国时间深夜,ARM公司也宣布暂停与华为的芯片架构合作。可以预见的是,
为争夺国际地位而拿工业界开刀
的手法将越发频繁。
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热点问题——中国企业在芯片、操作系统等底层技术上到底有多依赖美国?华为“备胎”有多强?开源系统会不会也被“禁运”?
然而,更隐秘而重要的竞争还不在应用面,而在
基础科学面
。
时间仿佛回到了80年前,危难的另一个名词是机会——被“卡脖子”的地球最新“暴发户”,中国,会孕育出一种更重视底层技术和基础科学,以及拥抱、善待顶尖科学人才的新型科技文化吗?
1.任正非的质问

“用物理方法来解决问题已趋近饱和,要重视数学方法的突起。”
——任正非《中国没有创新土壤,不开放就是死亡》
从很多迹象看,中国确实越来越重视基础科学了,尤其重视向来被认为是科学皇后的
数学
。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这一次,发出支持声的最强音来自工业界。
相信很多人都已读完了任正非于5月21日接受媒体采访的2万字实录。74岁的任正非在回答中
27次提及了“数学”
,例举了诸多数学对于华为的重要性:
华为5G标准是源于十多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的一篇数学论文;P30手机的照相功能依赖数学把微弱的信号还原;如今华为终端每三个月换一代,主要是数学家的贡献。
他掷地有声地质问:
我们国家修桥、修路、修房子……已经习惯了只要砸钱就行。但是芯片砸钱不行,得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但是我们有几个人在认真读书?博士论文真知灼见有多少呢?

来源:AP Photo/Vincent Yu
他甚至表示,等自己退休了要找一个好大学,
学数学
。
这不是任正非第一次提及数学的重要性。
2012年,在任正非与内部专家的一次座谈《中国没有创新土壤,不开放就是死亡》中,他提到:
“我认为用物理方法来解决问题已趋近饱和,要重视数学方法的突起。”
2006年以来,华为在俄罗斯和法国这两个传统数学强国建立了数学研究所。今年初,在接受采访时任正非说:这30年,其实我们真正的突破是数学,手机、系统设备是以数学为中心。
按任正非披露的信息,华为现在已有700多名数学家、800多名物理学家、120多名化学家、六七千名基础研究专家。
无独有偶,连向来被视为“拿来主义”大佬的马化腾在上周二被问及贸易争端时也说:“中国已经走到发展前沿,拿来主义的空间越来越少。如果我们不继续在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上下苦功,我们的数字经济就是在沙堆上起高楼,难以为继。”
今年两会前,马化腾还曾发表口头预告:腾讯未来要拿出10亿元建立基金,启动“科学探索奖”,支持数学、物理等基础科学的研究。
更早前的2016年,包括马化腾、李彦宏、丁磊、徐小平在内的中国互联网工业界“大佬”组团捐赠了“未来科学大奖”,单项奖金100万美元,承诺连续捐10年。
当被问起捐款原由时,马化腾说:“这么好的事情怎么能没有我?”他希望让数学、生命科学等基础科学领域成为新的时尚。
在上周六刚刚举行的2019年未来论坛·深圳峰会上,深圳市副市长王立新从城市产业发展的角度提到:
大家从最近的形势也看到基础研究对深圳、对中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过去讲80年代上大学的时候说: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提那句口号,就是:
“学好数理化,打遍天下都不怕”
。
工业界主动示爱数学,看起来朴素直白,背后却经历了充满辛酸泪的九曲十八弯。
要看清“破冰”的来路和去路,或许先要从骄傲的数学讲起。
2.骄傲的数学

“数学家们正把时间浪费在了无意义的‘谜语逗趣’上。”
——牛顿
一群数学博士聚会,常见的调侃是:
“那谁是不是6化了?”
“听说某某6化了?”
“什么?你小子浓眉大眼的,居然也6化了!”
“6化”一梗,源自理工大校MIT,描摹着数学和外部世界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
在MIT,所有课程都以数字编码,6字打头的是如今最炙手可热的计算机。本来学数学的人,学着学着溜去了计算机,是为“6化”。
能“6化”,说明数学作为科学之母,跨入其他学科并不难;但“6化”成为一种调侃,则反映了数学和其他学科间的距离感。
在华为此前建立数学研究中心,并广招数学博士时,也曾遇到过类似的尴尬。
一位快毕业的数学博士在知提乎问:
华为为什么要招数学博士?

一个答案是这样的:

答主认为,华为招的其实是应用数学博士,并非“主流数学”,从论文占比来说,纯数才是数学研究的主流。
这个答案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其中一种极端观点是:
应用数学根本不算数学
。
为什么理论数学界如此急于对外“划清界限”呢?
这是理论派的骄傲,也是理论派的孤独。
美国数学史家莫里斯·克莱因称这种隔绝为
“数学的孤立”
。
别误会,数学并非生而骄傲。一开始,数学家们总热衷于解决现实问题:牛顿是因为渴望算出双星轨迹才发明了微积分;庞加莱是为了解决三体问题才发明了微分方程。
曾几何时,璀璨的文艺复兴(14~16世纪)与激荡的大航海时代(15~17世纪)同时上演。数学在与其他学科和各类现实应用的互动中快速发展——航海需要的天体力学、战争中优化炮弹等武器需要的运动力学纷纷刺激、呼唤着数学的新突破。
牛顿引领的科学计算风潮应运而生,在古希腊数学理性、抽象、脱离于自然的传统上注入了
对现实的强烈关切
,让数学家更关注物理、天文、力学、光学等自然科学和应用中产生的问题,主导了17、18世纪和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数学文化。而数学也因为与应用紧密交融,带来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然而,浪漫的现实主义,却遭遇了漫长岁月里三次数学危机狠狠落下的“锤”:
公元前5世纪,信奉“万物皆数”(整数)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慌了:一位叫希伯斯的人发现了一个腰为1的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长度为根号2)永远无法用最简整数比表示,推翻了毕达哥拉斯的著名理论,引发了第一次数学危机。毕达哥拉斯学派愤怒地把希伯斯抛入大海。直到公元前400年,通过对无理数的定义,第一次危机被解决;
18世纪,微积分蓬勃发展,但人们发现牛顿和莱布尼兹分别创立的微积分理论是不严格的,他们对基本概念“无穷小”的理解是混乱的,微积分的合理性遭遇巨大质疑,第二次数学危机爆发。直到柯西用极限的方法定义了“无穷小”,微积分理论才得以进一步发展完善;
19世纪下半叶,康托尔创立了著名的集合论,其干净漂亮让数学家们开始相信集合论可以成为一切数学的基石。1900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法国著名数学家庞加莱甚至兴高采烈地宣称:“借助集合论概念,我们可以建造整个数学大厦……今天,我们可以说绝对的严格性已经达到了!”
可好景不长。1903年,英国数学家罗素提出著名的“罗素悖论”震惊了数学界:集合论是有漏洞的!第三次数学危机随之爆发。
本意修地基的人,越修却越发现更多的坑。
三次数学危机,让数学家们笃信的数学大厦的严格性一次又一次被撼动、修补、再撼动、再修补,此后,直觉主义、逻辑主义、形式主义和集合论公理化蓬勃发展,被危机吓怕了的数学家深深意识到“攘外必先安内”——四大流派当时的首要任务已不是解决来自物理、天文、光学、航海、炮弹制造等多个实际领域的问题,而是以各自的方式,
试图让数学重回一个逻辑严密的系统。
直到1931年,哥德尔终于给了数学体系致命一击。
哥德尔以一篇《论中的形式不可判定命题及有关系统》论文提出“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真的”和“可证的”从此被区分开来,可证的是真的,但真的不一定可证,换句话说,
世界上不存在既没有矛盾,又完备的数学系统。
这是一记重锤。数学家们终于开始接受确定性的丧失——
数学,并非一个和自然完美对应的真理体系。
咔嚓一下,支撑信念的东西脆裂了。
一种深刻的变化由此蔓延——既然数学并不必然和自然对应,那么用自然中的问题来启发数学研究似乎也并无必要。
此后,
自然、现实应用中涌现的问题,不再是指引数学家方向的明灯。
另一方面,现代高校分科制度的建设、教职评定的各种指标,又进一步强化了数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分离。学界有学界的规则,全职研究者不得不考虑顶级刊物、奖项的口味。
渐渐地,数学和物理、力学、天文学、电磁学等自然科学的深刻羁绊减弱了,数学被看做“形式科学”,和“自然科学”区隔开来;甚至即使在数学的国度内,数学家们也不再相互理解了。
纯数学变得越发骄傲
,失去了牛顿、庞加莱时代的“野蛮”活力
(在后世数学家看来,18世纪的数学过于依赖直觉,缺乏严密性)
。
1947年,冯·诺依曼曾敏锐地察觉了数学家想抛弃其他试验科学的动向:
在距离经验本源很远的地方,或者在多次“抽象”的近亲繁殖之后,一门数学科学就有退化的风险。起初,数学的风格通常是古典的,
一旦它显示出巴洛克式
(以装饰繁复著称)
的迹象,危险信号就发出来了。
——《数学家》
正如一个孤独的孩子是很难自发变开朗的,改变数学的“孤立”,很难靠从内“自爆”,而需要从外敲击。
比如动荡的二战就是一个敲开数学封闭围墙的钥匙。彼时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在“形势所迫”下,成了现代历史上最后一个数学与其他科学紧密互动的殿堂:最杰出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最杰出的数学家哥德尔、开创了计算机科学的冯·诺依曼、人工智能的鼻祖图灵,总能轻松穿过走廊自由交谈,一个世界的智慧启发着另一个世界的方向。
而如今,围墙之外,“6化的世界”又开始急切地敲门了。
3.着急的工业界

“人工智能需要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否则它的发展会有很大困难。“
——丘成桐
在数学世界的另一端,工业界可没那么深沉。
他们的思维方式简单粗暴——
产业发展遇到了瓶颈,亟需更多基础理论支撑。
近年来,从高端制造需要的材料科学,到物流、交通和智慧城市离不开的运筹学,到安全技术所依赖的密码学,再到直接卡住人工智能进展的算法层的思想革新,“硬科技”在工业界的落地,处处呼唤着数学。
去年以来引起中国普通民众关心的半导体产业,正急需数学的贡献。
在芯片设计、制造的繁复流程中,每个微小差别——比如不同的组件尺寸、组件材质、元器件排布等——都可能使芯片性能产生巨大差异,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而数学的引入,则能在仿真和模拟环节代替成本高、耗时长的真实实验,提前预判芯片的效果。
目前,科学家已找到了许多描述半导体特性的数学方程,但是在求得精确解上,数学家仍束手无策,只能借由计算机得到近似解。随着芯片制造难度的升级,工业界急需找到更优的计算方法。
在对新型燃料电池、高端装备、高端制造影响深远的材料科学领域,科学家也在呼唤数学家的跨学科援助。
如离散几何分析极有可能助力对纳米多孔材料的研究,这一材料在研发新型催化剂上有广泛的应用前景,而新型催化剂又有可能攻克氢燃料电池的应用难题,从而带来新一轮的汽车革命。
而如今大热的人工智能领域,数学缺席的瓶颈感格外明显。
业界对过去一年的人工智能有一个评价:
2018年,人工智能的进展就是没有进展。
《浪潮之巅》作者、硅谷风险投资人吴军有一个判断:
“人工智能技术20年内不会有大突破,因为今天的人工智能已经用光了40年来所积累的技术红利。”
这要追溯到神经网络、深度学习方法的缘起。上世纪70年代,计算机科学家就开始研究神经网络在推进人工智能上的可行性。
在
《甲小姐对话特伦斯》
一文中我们曾提到,当时,人工智能开山鼻祖之一马文·明斯基认为神经网络有数学上的局限性,在他的权威震慑下,神经网络在此后近40年里一直无缘主流。
2012年之后,主流快速翻转,深度学习在“大算力+大数据”加持下获得神速进展,功能主义取代理论体系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尚方宝剑,但花开遍地后,却遇到了能力进一步提升的关卡。
关卡背后的深层原因是,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是对以逻辑、规则为基础的“建制派”的颠覆:好处是在结合大数据之后效果立竿见影;坏处则是深度学习成了一个人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黑匣子”,效果显著,却
缺乏数学理论支持
。
到2016年,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赛事ImageNet中的神经网络层数已达到了1207层,工程思维一度盖过科学思维,但要想进一步发挥作用,没有底层理论支撑很难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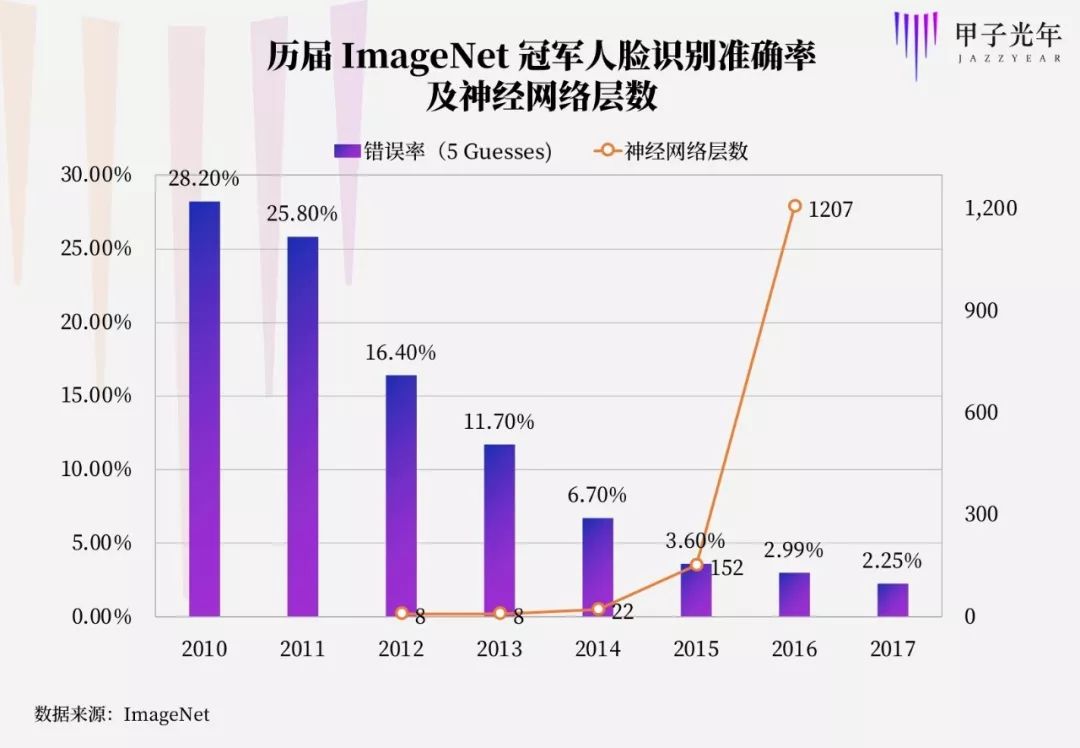
在2017年的中国计算机大会(CNCC 2017)上,首位华人菲尔兹得主、哈佛大学终身教授
丘成桐曾从数学家的角度发出提醒:
人工智能需要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否则它的发展会有很大困难。
如今,中国工业界对攀登人工智能高地踌躇满志,在应用领域也是“形势一片大好”,诞生了诸多知名的业界公司,但却面临着丘成桐提及的“基础不牢”的隐忧。
上周五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张钹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目前仍长于跟随,不擅拓荒:
我们的从众心理很严重,比如在人工智能领域,
深度学习很热,发表论文的作者中几乎70%是华人
,但是其他非热门领域,包括
不确定性推理、知识表示等几乎没有华人作者
。这就是从众扎堆,不愿意去探索“无人区”。
当被问及瓶颈该如何突围时,张钹院士给出了两个方向:“一是数学,二是脑科学。”
何时可以迎来突围?
院士的回答,真诚中有一点无奈:
“很难预计,我们也很着急。”
4.知其所以然

“数学的核心是解决‘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的问题。”
——华为技术战略部部长朱广平
数学究竟能为工业带来什么?
任正非在采访中提到,F22隐形飞机的隐形原理是五十年代俄罗斯数学家发明的。而华为在2008年推出的传奇技术方案SingleRAN,更是数学支撑工业应用的一个经典范例。
对华为的客户,即网络运营商们来说,SingleRAN解决了一个刚需:在2G、3G、4G和不断到来的通信网络迭代中,提供同时运营多制式网络的能力,从而让运营商以更低成本平滑进入4G时代。
这一方案迅速引领业界风潮,到2010年底,华为已在全球部署了80个SingleRAN网络。《经济学人》的一篇报道提到,拉美运营商AméricaMóvil在部署了华为的SingleRAN之后,
基站功耗降低了50%,设备数量减少了70%
。
SingleRAN的革新性,
离不开背后复杂的数学算法
。
2006年,陆家嘴软件园,华为上海研究所903实验室里,射频领域首席专家,华为Fellow吕劲松向多载波技术这一业界难题发起挑战,这是SingleRAN的起点。
在1年半的研发过程中,华为俄罗斯研究所的算法专家鼎力相助——
当年华为之所以在莫斯科建俄罗斯研发中心,正是看中了俄罗斯作为传统数学强国的深厚底蕴
。
不仅提前布局基础数学研究,华为还通过长年投入,趟完了从基础数学到工程化落地的各种坑。吕劲松在开发多载波技术时,曾在生产线上待了6个月,从库房到物料,到贴片机,清查了各环节可能影响质量的所有细节,保证了SingleRAN的质量。
正是对基础研究的持续投入和超强的工程能力,为华为建立了作为设备商的技术壁垒。借助SingleRAN,此前通信设备业务收入排名全球第四的华为力压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在4G普及的2014年,一跃登上世界头把交椅。
5G时代,数学又帮华为进一步获得了制定标准的先机。
去年7月26日,华为深圳总部红毯铺地,欢迎一个神秘来宾,他并非政要商要,而是土耳其毕尔肯大学教授Erdal Arikan。
当天的活动是为了感谢这位非华为编制的研究者。
2010年,已投入5G研发两年的华为发现了Arikan在2008年提出的Polar Code
(极化码)理论
。
相比Arikan的导师Robert G. Gallager
(香农的学生)
在1963年提出的信道编码技术LDPC码,Polar Code有理论上的优势,但从工程学的角度来说不成熟。
华为顶着风险,陆续围绕Polar Code投入了数千人的研发资源,把Arikan的论文变成了一系列专利和技术,并使之在2016年底成为5G控制信道编码方案——
这是中国厂商第一次掌握了国际移动通信标准制定的话语权
。
在去年那场感谢Arikan教授的活动中,任正非说:“我们要加强基础研究的投资,希望用于基础研究费用从每年总研发费用150-200亿美金中划出更多的一块来,例如20%-30%,
这样每年有30-40亿美金左右作为基础研究投入。
”
这也是为什么,在如今华为遭遇危机后,任正非仍能自信地表态:“华为的5G是绝对不会受影响,在5G技术方面,别的国家两三年内肯定追不上华为。”
2016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拓扑绝缘体,也是数学和科学、工业界碰撞的成果。
拓扑学本是数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几何体在连续形变中的不变性质。2007年发现的拓扑绝缘体,是将诞生已100多年的拓扑学引入凝聚态物理的成果之一。
拓扑绝缘体被认为是继石墨烯之后的“next big thing”,它内部绝缘,表面导电,特性神奇,在半导体行业极有应用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