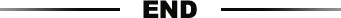一
上初中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收音机里收听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我迅速记住了高考落榜回乡青年高加林和纯朴善良的刘巧珍,他们的形象深深地刻印在我年幼的心灵里。小说开篇的那句话我一直记得非常清楚: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在你年轻的时候。
没想到,几年以后,我也像高加林一样踏上了回乡的路。
二
1989年的高考对我来说是空洞和虚无的,因为那是一场没有真正考试的高考。也就是说,我虽然也是一名高中毕业生,但并没有看过真正的高考试卷,也记不起当年的高考作文是什么。
因为我没资格,我没有通过预考这一关。
那时由于高等院校少,招生名额有限,国家把高考分为预考和正式考试两个阶段,在预考阶段先把绝大多数升学无望的学生像垃圾一样清理掉,然后再在剩下的少数人中选拔。
听到预考没过的消息,我感到很丢人,睡在家里的小木板床上几天也不出门,我害怕碰见别人,他们每次的询问就像是鸡喙啄了一下我的心,后来,我干脆就不出门了,连家人也不想见,只把自己锁定在那一米多宽的小床上。
妈妈心疼我,一天三顿把摊得油汪汪黄亮亮的鸡蛋饼端给我吃,平时沉默寡言的父亲每天都要在我的床边坐一会儿,有时劝我再复读一年吧,不然我回来能干什么呢,有时什么也不说,只在那里枯坐一会,但他每次都是连抽几支用我废本子卷的老烟叶,呛人的烟味搅不活凝固的空气,父亲的存在让我心里感到堵得慌,这时我就盼着父亲会被老烟叶呛得猛烈地咳嗽一声,然后跑到外面去吐痰。
父亲的劝说并没能让我回心转意,念了许多年书,我也实在是念够了,想想再去回堂复读,那些依然生疏的题目就像已经被嚼过而没消化的米饭一样,让我再去吃,我只想吐,再也不愿接受。
三
儿子没有跳出农门,就要像他们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地生活,父母在沉默中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我的执拗掐灭了他们的最后一点希望。
他们接下来就为我的生计发愁,一到五更头,他们睡的柴笆和柴席就被左右翻身压得吱吱响起来,然后就听到他们在东头房里咕咕叽叽地讲话。他们讨论的重点就是我要摊到河工了。
乡下人都是穷苦人,穷苦人都是又势利又现实的人。在我的成绩没出来之前,他们对我还是另眼看待的,因为我还存在着跃出农门的可能,如果我跃出了农门,他们就会高看我一眼,如果我重新又跌回到土疙瘩里,他们顾不上同情我,立即就会把他们所受的苦分给我一份,让我和他们平等,而不会因为我细皮嫩肉,因为我是本家的小辈而照顾我。况且我们那个小村庄还是一个有着四大姓的杂姓庄。
那年的深秋,我真的就摊上了让人胆颤心惊的河工。上河工也就是扒河,是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苏北地方乃至全国各地农村冬春的一项重要农事。那时候,每到冬闲时节,乡村就要在大广播里反复发动群众大搞水利工程,为明年和今后的农业生产做好准备,有的河道每年都会疏浚一次,也有的几年一次,根据需要,还会从平地用人海战术硬扒出一条大河。那时候的河,基本就是这样靠千千万万人一锹一锹车推人担干出来的。
扒河工是一个苦活,要一锹一锹地把湿重的泥土上到独轮车上,然后沿着斜坡向岸上推,那就像推着一座山啊,向上推,车辙深陷在松软的土地,推不动,又不能向后退,一退就人仰车翻。扒河工时,男人们都会想,狗日的,自己连平时用鞭使唤的老黄牛都不如。当时,许多人拼命地学习想跳出龙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摆脱扒河工的命运。
那时,家附近的小河工都是按人头分的,出公社的大河工都是按男劳力分的,也就是说庄上凡是达到年龄的男劳力(学生除外)必须要去。我刚毕业那年摊到的就是大河工,虽然我才放下书本,但庄上就有人开始从背后撬我去上河工。
让我上河工的消息像是化不开的雾霭笼罩在我家的用黄土垒起的小院里,母亲无心做饭,我睡在床上头脑里一片空白,父亲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着老烟叶,最后,父亲趁着夜色的掩护拎了一小篮子鸡蛋跑到队长家和队长商量,队长虽然和我家不一姓,但和我家沾亲带故,最后队长不知是看在鸡蛋的面子上还是亲戚的面子上,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那就是出钱买工。但那时早已分田到户,队长已经没有绝对的权威,他的话并没有被一呼百应,最后我还是没有逃过扒河工的一劫。
我至今都记得那天上河工的情景,一大早,队长不知从哪儿找来了两辆小四轮拖拉机,车上装着木棒、铁锹、手推车、麦草,面、白菜等东西,还有几十名庄上成年的男丁,每个人的手里都握着大队发的彩旗,今人血脉喷张。但这只是别的感受,我记得我当时爬上车子的一刹那,心里就像是被押上刑场一样难受。
扒河工是一个苦活,要一锹一锹地把湿重的泥土上到独轮车上,然后沿着斜坡向岸上推,那就像推着一座山啊,向上推,车辙深陷在松软的土地,推不动,又不能向后退,一退就人仰车翻。扒河工时,男人们都会想,狗日的,自己连平时用鞭使唤的老黄牛都不如。当时,许多人拼命地学习想跳出龙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摆脱扒河工的命运。
随着河底的加深,慢慢地河道两边就形成了90度的垂直坡,抬筐已不适应了,一人推车一人拉牵也更艰难了,有时,一人在后奋力向上推那装满淤泥的独轮车,要二三个人帮忙奋力地向上拉,才能勉强地将一车土推到河堰上。
我当时是和父亲分在一起,父亲舍不得让我推小车,只是叫我用绳子在他前面拉,我体深深地体会到了父亲的辛苦和对我的无言的爱,就在前面把身体倾斜成了45度,拼命地拉,肩上的绳索深深地勒进了我的皮肉里,手上的血泡都破了,握在手心的是钻心的痛。
到了初冬,寒风刺人,但是工地上的人们身穿单衣仍汗流浃背。每到收工吃饭时,我们就到附近村庄代伙的农户家吃饭,吃的大多是我们平时很难吃到的白菜烧豆腐和肥猪肉煮粉丝,我的饭量大增,每顿都吃两大碗米饭。
吃过饭后,工友们有的抽烟,有的在地上画一个棋盘下棋,有的讲古,而我总是爱躺在稻草铺就的地铺上,累得一动也不想动,像一个遍体磷伤的战士,落寞地想着自己微茫的心思。
那是我唯一的一次扒河工,刻骨铭心。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扒河逐浙由人工转向了机械化,河工也就浙浙淡出了我的生活,我才彻底摆脱了弄河工的恶梦。
四
虽然我没跳出农门,但在土地里折腾了半辈子的父母却不愿再让我沾上泥土,他们想找关系走门为我谋得一份风不打头雨不打脸的工作,但是这对于完全是在土地里刨食的父母来说,是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有一次妈妈回娘家之后。我记得那次妈妈是愁眉苦脸回去的,回来后却是满面春风,她还没跨进家门就喊着父亲的名字,然后告诉父亲,她有个叔伯哥哥以前是个当兵的,参加过打越南的自卫还击战,后来提了干,现在转业了,在县政府上班。
于是,父母就把我的未来寄托在这位从没见过面的但却是唯一在外当官的亲戚身上。他们决定第二天早上就去找这位亲戚。可是再近的亲戚,也是去求人办事的,空着手肯定是不行的。父母琢磨来琢磨去,觉得家里能够拿得出手的让人有点稀罕的东西只有当地的特产小油果花生。于是,父母就带上了一蛇皮口袋精心挑选的小油果花生,临走时又觉得不够,临时从鸡圈里逮了两只小公鸡。
具体见面过程不详。只听妈妈回来说,她的这位兄弟虽然是个当官的,眼眶一点也不大,大姐大姐叫得亲热热的,还拉他们到饭店里吃了一顿。
后来,我的这位远房亲戚还真的给我在乡政府谋了一份差事,那就是到乡政府里的棉办上班。所谓棉办就是棉花办公室,是一个临时性的机构,成员是由从农村抽来的棉花技术员和像我这样的闲杂人员组成的。说白了,这个机构就像是一块肉,有肉在,我们这些人就可以像苍蝇一样围上去,肉没了,我们也就会一哄而散。
棉办的工作除了偶尔向棉农传授一些病虫害防治的知识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罚款。那时,田地已经承包到户多年,按理说,农民可以想种什么就种什么,他们是自由的。可是,当时乡政府的领导人为了自己的政绩,非要搞什么棉花特色区,也就是要强制农民种棉花。我们这些人干的事就是每天早上到乡政府点名,然后骑着车子下村,拿着卷尺到各家地头挨家挨户地丈量,不足的就要按规定罚款。然后中午到村干部家吃喝,下午喝得晕乎乎的早早就打道回府。村民们看到我们来了,都在背地里叫我们"黑狗队"和"二黄"。
作为一个农民子弟,我对这样的工作是不适应的,我想逃离。于是,我就利用业余时间写稿。我上学时就爱好文学,是学校春晖文学社的社长,曾经有文章发表,也因此造成偏科没有考上大学。
很快,我的通讯报道稿就在当地报纸发表了,一篇接着一篇,每篇里面我都刻意突出了"党委书记某某某"字样,公社书记看了很高兴,在早会上把我表扬了一番后,当即就把我调到了党委办公室从事通讯报道工作。
我的到来让一个人感到不悦,那就原来的通讯报道员老黄。老黄四十多岁,干这个工作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我从小就是在农村小喇叭里听他的"四季歌"式的新闻长大的。说实话,我对老黄那些千遍一律味同嚼蜡的新闻从心底里是瞧不起的,这也有可能是我当时年少气盛吧。
自从我到了党委办公室后,老黄整天板着脸,和我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他原来是坐在进门的最后一张办公桌上,我来了以后,他立即搬到了前面,让我坐到了后面。他领的稿纸从来不给我用,都说是自己买的。不仅如此,他在投稿上还骑在我头上,比如说同一件事他投给了县广播站和县报,然后他就不让我投了,说他是这些单位的特约通讯员,意思就是说,我垄断了。
但是,真正的才华他是压抑不住的。他不让我写他那些鸡零狗碎的"豆腐块",我就写登在县报一版二版头条的长文章,另外,我的新闻特写还登上了《新华日报》和《农民日报》。可以肯定,如果我在乡里干下去,肯定会把老黄的饭碗撅掉了。然而,我并没在乡政府干多长时间,不久我就萌生退意。
有一次,我到县里去参加县优秀新闻工作者表彰会,见到了许多平时只见其名未见其人的各个乡镇的通讯员。他们大都是和老黄差不多的年纪,在这行里干了二十多年,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土记者。但是他们至今仍然拿着二三十元微薄的没有保障的工资,可有可无地在乡政府里存在的。因为是农村户口,他们就是干得再好永远也无法转正,然后沿着秘书--副乡长的仕途上升。我就是在这里再干上二十年,也是和他们一样的结局。
于是,1994年,我在父母的一片反对声中,带着新婚的妻子到淮安打工去了。打工最终改变了我的生活。这是后话。
五
高中毕业第二年,我就遇上了一名像巧珍一样的姑娘。
自从我不上学回到农村务农以后,父母第一件事就是操心为我找工作,第二件事就是操心为我找对象,父母一出门就要求我和他们一起去,他们和人讲话时,无论谈什么话题,最后都会回归到我找对象的问题上,结语都是"有相巧的请你帮忙说啊"。
我出门时,父母都让我在白的确良小褂的口袋里插上一块五一包的罗曼蒂克香烟,见到人就散一散,活套一点,才会有人愿意给我介绍对象。
其实,在找对象这件事情上,我当时内心还是有点抗拒的。因为在上学的时候,己经有一位姑娘走进了我的心里。
当年,我是一个土里吧唧的农村臭小子,我暗恋上了我的一位初中女同学,她是教师子女,她的父母在附近的一所小学教书,她穿着洋气,连发型都是时新的紧跟着城里的潮流,就连她骑的自行车都很别致,是那种高龙头弯车把的,有别于普通女生骑的笨重的二八杠自行车。她生下来就有了有别于我们这些乡下孩子但的高贵的血统,她是定量户口,我是修地球人所专有的农业户口。
我虽然爱慕她的这些所有的特质,但这并不是我喑恋她的理由。我暗恋她,是因为她的作文好,我的作文也好,我们俩的作文经常被语文老师拿在课堂上作范文读,每次我的作文被读过后,作文本都是由坐在第一排的她转身扔给我,或者是下位子送给我,每次看到她扑闪扑闪的眼晴像蝴蝶一样飞过来,我就羞怯地低下了头,而事后,我会偷偷地贪婪嗅一嗅我的作文本子,希望捕捉到她身上的芳香。通过作文本子,我的心与她有了初次的链接。
后来,初中毕业后,我仍在原校就读,她到了县城读高中。我们开始了长达三年的通信,高中毕业后,她上了大学,而我走向了农村,我们就像两条来自不同地方的河流,在某地交集了一下,然后又各自流向远方。自始自终,我都没敢吐出那个字。
回到农村后,我不能忘记她,就把我对她的思念以及我们曾经的往事写成文章投给了家乡的媒体《涟水报》,文章发表了,我非常兴奋,我发誓写遍家乡的所有媒体,我希望她能看到我的文章,后来,我又写了几篇这样的文章先后在《淮安电视报》、《江苏工人报》和《服务导报》上发表。
但是这些文章并没能帮我找回"失联"的她,不知她看到过我的文章没有。我虽然知道由于我没考上大学,我们之间有着天然的城乡之间的鸿沟无法逾越,但我心里还是有点放不下。
但是父母并不知道我的想法,他们不停地为我说媳妇积攒着钱,父亲一到逢集就推一口袋粮食到街上去卖。每次回来,父亲就把那些大小不一的钞票理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小心翼翼地揣进家里的那个旧被胎里,那个不起眼的旧被胎就是我们家里的保险箱。
不仅如此,父母还为我说媳妇积攒着人缘。父母老实,对人热诚,从不做伤人脑筋的事,和老少三代都能处得来。因此我们家虽然不富裕,但因为人性好,再加上我是个有点文化的回乡青年,前来说亲事的人纷至沓来。
六
我对其中一个叫做小红桃的姑娘动了心。这位姑娘身材修长而结实,宽松的粗布衣衫掩饰不住她的秀美,单眼皮,瓜子脸,马尾辫,白皙的脸上时常飘着两朵红云,令我难忘。
她完全符合我在心中预定的择偶标准,个子高一点,白肤白一点。因为这两个标准是我的缺陷,我想与她互补一下。
说实话,当时我还怕她看不上我呢。当时我们是在街上供销社门口相亲的,双方在人来人往的赶集人的掩护下匆匆地看了一眼,然后媒人就把她拉到一边去问同不同意。农村人做事就是这么干脆,同意就同意,不同意就不同意。我站在一旁,内心很忐忑,把头转向别处,不敢往她们望。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媒人就眉开眼笑地跑来报信说,女方没意见。
从此,我们就开始了交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农村还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我们无法联系,于是一逢集我们就不约而同地去赶集,希望在街上遇到对方。事实证明,这种约会的方式也蛮灵验的,我们总是在想见对方的时候就能如愿见到对方。
在接触中我了解到,她只念到小学毕业就辍学了,原因是她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三个人都念念不起,还有就是她的妈妈体弱多病,干不了什么农活,需要她顶上去。
有一次我问她喜不喜欢看书,她说不喜欢看,她说她喜欢听流行歌曲,喜欢听小虎队的歌。我听后有点失落,仿佛自己的青春自已的梦想就这样被人轻轻地提走了,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散文《相亲》,发表在团中央主办的《农村青年》杂志上。
文章发表后,我的教书的姑姑委婉地提醒我说,你这样写就不怕你对象生气啊。经过小姑的提醒,我也觉得有点对不起她,就在一次见面时试探着把这件事告诉了她,并且我提出要把文章拿给她看一看。谁知她竟然朝我一笑,满不在乎地说,我不看哦,只要你和我好就行,你想怎么写都行,我拖你的后腿。
交往了大半年后,我们的感情渐深,每次逢集见面时都不忍分手,她把我送到家门口我再把她送到家门囗。父母也认为到了瓜熟蒂落该摘果子的时候了,就提出要结婚带人。
没想到,她妈妈提出的条件却把我们逼到了分手的岸边。她的妈妈提出要一万八千八的彩礼,少一分钱也不行。这在当时可是个天文数字,父母省吃俭用很长时间家里也就聚了几千元钱,与这个数字相差太远,就是借也借不了这么多啊。
父母买了条罗曼蒂克烟给媒人,请煤人前往周旋,可几次都没有结果。媒人回话说,她妈说了,她家指望这个钱把家里的土墙瓦房翻盖成砖砌大瓦房,留以后给儿子说媳妇呢。
那时候她家里也穷,屋里除了人之外,没有什么象样的东西。她妈妈常年不做事,也许是体弱,也许是好吃懒做,常年就像一个摆设一样,地里所有的农活都依靠她和她那终日像老黄牛一样的父亲。她的父亲一天三顿饭都端给她的妈妈。她的妈妈是一个怪人,从不和家人坐在一桌子吃饭,她吃饭就像怕见人似的,总是一个人躲在床头吃。她吃的也都和别人不一样,她吃的大都是猪蹄爪汤煮饼或者是鸡蛋面之类的一般人很难吃到的好饭。
她妈妈还是一个阴冷的人,常年不笑,坐在哪里就懒得动,就像一个抱窝鸡一样,但她却长着鹰隼一样的三角眼睛,整天冷冷地扫瞄着,控制着这个家的走向。
七
她家提出要天价的彩礼后,父母的天空愁云骤起,父亲又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着老烟叶,他们也没了主意,问我怎么办,我不吱声,父母知道我舍不得,他们就四面八方地去借钱,无奈,家里的亲戚基本都是和父母一样在土里刨食的人,根本拿不出多少钱借给别人,父母跑了一大圈只借到了几千元钱,离彩礼钱的数字相差太远。
为此,她也与她的妈妈吵闹过,以不吃饭不干活来抗争过,但都无济于事。她的妈妈看我们家迟迟拿不出彩礼,对她也看得更紧了,不许她上街,更不许她到我们家去。于是,她就让她最小的弟弟到街上供销社门口去找我,约我到她家附近的一块玉米地里见面。
我如约前往。我们躺在玉米地旁边的一块花生地上,她向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那就是先怀孕后结婚,这样生米煮成了熟饭,她的妈妈就不会再要那么多的钱礼了。
她的想法胆大得让我有些吃惊,要知道,那时的人还没有现在这么开放,这样做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弄不好就会身败名裂。
那一天,我们躺在如绣了绿色花朵的地毯一样的花生藤上,我的心她的心都被染成了绿色,我们被绿色融化了,我们与绿色融为了一体。
后来,我们又多次在玉米地里约会,但是一段时间后,我们的计谋并没得逞,她并没有怀孕。
但是她的妈妈等不及了,她妈妈看到我们家再也榨不出更多油水了,就又把她说给了村上一个专门杀猪卖肉的杀猪屠的儿子,老子杀猪,儿子卖肉,家中很有钱,没费劲就把彩礼捧来了。她妈妈剩热打铁,迅速为她定下了结婚的日期。
我与她最后一次见面还是在那块玉米地里,其时,每一棵玉米都像一个威武的士兵,把玉米地站成一个绿色的海洋,有的玉米的棒槌上已经开始抽出晶莹色的胡须了。她流着泪对我说,我们做不了夫妻,你就做我的哥吧。我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我把头深深地埋进她的怀里,她的怀里飘着田野的芬芳。
我知道,今生今世,我再也遇不到这样好的女人了。
责编:笑笑
本文版权归属有故事的人,转载请与后台联系
阅读更多故事,请关注有故事的人,ID:ifeng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