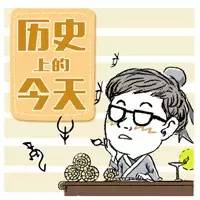当我们谈及自由意志时,往往将其与自主的抉择、自由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第一重探问在于:为什么惩罚会与自由意志相关涉?惩罚首先是一种对于行为结果的再审视,它基于对行为的判断,在这个层面上惩罚需要对自由意志进行界定,并据此来衡量个人的道德责任。这也正是我们在现实语境中经常会遭遇的问题:对于犯罪分子的量刑多少。自由意志导向个体的行为,也说明了个人担负道德责任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根据判断个体行为的恰切与否、过失与否,我们也能追溯至意志的原貌。但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要将惩罚作为应对错误行为的有效手段,而不是借助于其他的方式,诸如言语的劝说或教育?我想,一般来说我们实施惩罚的初衷是在于,我们相信惩罚可以对犯错误者及潜在的犯错误者的意志产生一种有用的因果影响,用以避免他堕入更大程度的恶。我们希望将罪犯判刑,用强制手段限制其行为自由,使其不能够继续作恶,也通过惩罚来追究罪犯在行为上的道德责任。惩罚本身意指着更深层次的道德判断与道德责任。用一种不甚确切的方式来表述,已犯下的罪行等于一种见证或证据,它表明了犯罪者本身是一个可能怎样的人并具有怎样的倾向,提供了一个大前提,而这种大前提在多数情况中会指向一个恶的结果。
而当我们从另一个极端切入,将惩罚和决定论立场两者并置时,自由意志的重要性反而在这个独特的截面上得到了印证。在决定论的理论框架下,人采取一切行为都早已被因果性地预先决定了,在这种前提下,犯罪更像是一种角色行为。设想一下,如果我的行为早在宇宙大爆炸时便已被决定了,我犯罪抑或不犯罪,杀烧抢掠抑或遵纪守法都早已被决定,我就像是一个尽责且专业的演员,单纯按照早已敲定的剧本演绎生活,那么我本身就不应当背负道德责任,因为任何的决定与行为实质上都与“我”无涉,我没有理由成为这些决定与行为的承担者。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我的行为所导致的结果对我进行惩罚绝对不是正确的,惩罚亦根本无意义,惩罚与否都无法改变我继续作恶或停止作恶的预定行为,也无法改变事情变化发展的走向。在决定论的预设下惩罚失去了其被赋予的价值内涵。因此,在决定论的理论立场预设中,惩罚是完全不必要的。我们能够断言说,道德责任内在地要求非决定论。这也恰恰映射了惩罚与自由意志之间不可割裂的关系:惩罚能够在自由意志的基质上发挥效力,自由意志的存有与否也能借此得以证明。
现实基点:公众对于惩罚的认知
惩罚和自由意志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通过一个哲学实验来厘清。Shaun Nichols曾就大众对于自由意志的看法进行实验哲学研究 ,不同于传统式的思辨性论述,这个实验着重探究人们对自由意志的知觉以及自由意志和惩罚两者的关系。在实验中,他们向一组被试者描述了一个决定论的世界:每个事件或决定的发生都完全是由之前的事件所导致的,每一事件或决定都严格遵循因果律发生 ,并随即询问被试者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有道德责任是否可能?被试者都倾向于认为不可能负道德责任。这当然是一个抽象层面的问题,但也同时证实了通常人们是否认决定论的,抑或说否认不存在自由意志的断言。而另一组的实验结果却大相径庭,在该组中,研究者向被试者描述了一个具体的案件,一名男子杀害了他的家人,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被试者知道在这个假设的决定论世界中每一行为和事件都是被决定的,人们仍然倾向于认为这名男子需要对他自身的行为负有完全的道德责任。同一个预设的理论背景下,大众却对抽象情境和具体情境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判断,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具体的情境会更多地触发人的情绪反应,并进而使人倾向于惩罚肇事者。另一个相似实验的结果有力支撑了这个解释,实验表明,同样是在决定论的世界中,相比较于引发弱情绪的情境【emotionally bland (low-affect) transgression】,被试者在引发强情绪的情境中【emotionally upset (high-affect) transgression】更倾向于认为肇事者负有道德责任。
这个实验所关涉的,更多的是一种普遍的,同时亦是直觉性的自由意志观念。但同时也映射了一种受到普遍认同的惩罚观念。
即便是面对海耶斯和科米萨耶夫斯基这样两名穷凶极恶的罪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当公众了解到脑瘤抑或其他神经性疾病是导致他们犯罪行为的诱因时,可能会陡生“理解之同情”,道德的天平也会迅速改变倾向,从原本的深恶痛绝转变为同情宽恕。
行为是否是有意识地进行的,这一点对于惩罚的判定具有基准式的作用。有意识的行为并不仅仅是说人在那个瞬间知晓自己正在做什么,也同时要求人对行为的道德本质有所体认,要求人在意愿层面对可能的行为结果做出回应。这同时也牵涉到是否有意作恶的问题,苏格拉底认为“无人有意作恶”,有了善知便有善行,恶行是无知的结果,将人的灵魂置于善的导向之下,但在现实中,我们依然倾向于将行为意愿进行善恶二分的价值定性。一个人有意作恶,可能表征为一种作恶的必然性,抑或行为动机的不合道德性,归根结底,可以说这种恶扎根于他的意欲中,从意志或念头的萌生到行为的落实、行为的结果,这种恶一以贯之。对于有意作恶的行为,人们倾向于认为惩罚必要,借由惩罚的手段来改变作恶者的意志。无意作恶的行为包括过失、情绪冲动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似乎并非是被意志所主导的,更多的是被外在于人的客观因果所影响,意志本身并不浸润在恶之中,因而人们倾向于说可以减轻惩罚,或者不需通过惩罚来纠正意志。
但是这种关于自由意志的经验性直觉一定是正确的吗?在我们拥有自由意志的前提之下,自由意志本身也是一种具有固定属性的东西吗,为什么瞬间做出的决定就可以被撇离出自由意志的畴域呢?
惩罚的有效性
惩罚所指向的是罪责,而在上述所说的现实情境中,罪责似乎不再是一种纯质的东西,而是一种混合物——其中混杂着两类:自己造成的影响和命运造成的影响,自己造成的影响指的是自身的犯罪动机、犯罪意愿等,而命运造成的影响更多关涉着外界因素或外部原因,诸如犯罪者从小生活的环境状况、犯罪者的生理官能、疾病状态等等。前者与自由意志的存有直接相关,后者则倾向于从外部世界寻找行为之原因,这种因果原则实际上要求我们跳脱出惯常的第一人称视角,跳出日常生活而以第三人称的上帝视角来看待我们的处境,意志被要求从生理性或者自然性的层面进行充分的解释。
概括说来,大众的惯常思维可以概括为一个简单的公式:【理想的惩罚=自己造成的影响=行为的全部影响-命运造成的影响】,这个世俗性公式面临着最为直接的质疑:最理想的惩罚就是仔细甄别行为诱因中的意志成分和因果成分吗?它切实具有现实效用吗?如果不是,那又应该如何界定惩罚。
当我们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审视,功利主义代表边沁就认为,所有的惩罚都是损害,所有惩罚本身都是恶。“根据功利原理,如果它应当被允许,那只是因为它有可能排除某种更大的恶。” 这似乎是说惩罚并不必须,而仅仅是在避免更大恶的层面上被需要。边沁同时提出了不应当施加惩罚的四种情况,其中包括(1)惩罚无理由,即不存在要防止的损害,为总的来说无害;(2)惩罚必定无效,即不可能起到防止损害的作用;(3)惩罚无益,或者说代价太高,即惩罚会造成的损害将大于它防止的损害;(4)惩罚无必要,即损害不需惩罚便可加以防止或自己停止,亦即以较小的代价便可防止或停止。就边沁的视域来说,惩罚应当与道德约束力、宗教约束力区别开来。可以说,惩罚本身对于行为的意志作用是有效的。这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情感层面的威慑,我倾向于认同自由意志也具有功利性的趋利避害属性,惩罚作为一种损害能让意志充分考量行为后果并趋向于采取避免惩罚的行为;其次是矫正,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谈到“矫正的公正”,他指出法律只考虑行为所造成的伤害,把做错事的好人和坏人两者看成是平等的,如果一方打了人,另一方挨了打,或者一方杀了人,另一方被杀了,做这个行为同承受这个行为这两者之间就不平等,法官就要通过剥夺行为者的得来使他受损失。 惩罚能够作为一种矫正来实现平等的维护。亚里士多德同时给予我们另一重启示,做错事的好人与坏人是平等的,那么推演到自由意志,是否意味着无论自由意志自身属性的善恶,当其所致使的行为结果是糟糕的,自由意志本身应受到同等的谴责?
可以说,惩罚基于某种道德判断。诚如弗兰克林所指出的,人们当下广泛称为“道德判断”的那种判断,主要建立在一个奇怪的基础上,“这个基础把人们对不幸结果的愤怒、同情和报复,与对行动者的观点的尊重、社会效用以及人的个性、他治和自治的价值混合起来。” 形成这种判断的原因混杂着情感冲动与经验价值,这在一些情况中甚至不能与理性相兼容。“惩罚”的概念敦促我们进行明晰的判断,并尽可能找寻到判断的根由:如果人拥有自由意志,那么究竟在什么情况下一个人方才称得上是按照自由意志行动的?又是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说他的自由意志受到了损害——是在他被五花大绑受到外力约束无法动弹的时候?还是当他精神失常胡作非为时?又或者当他无法按照自己的愿望来控制自己的欲望时?这个问题同样可以压缩为:自由意志的作用是体现在行使调用还是合理控制上?就我看来,自由意志不是境况性的,也不是时隐时现的,而是贯穿于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瞬间。这些看似自由意志受到损害的情况,其实是意志初衷与现实结果相悖离的情况。那么此时也许会有人站在决定论的对立面提出疑问:“他是不是当且仅当自己的意志是行为的无因之因时是自由的?” 自由意志并非是一个被寄放在我们身上待发现的零部件,它不可目见,也没有触碰式的开关控制,但它和行为之间的存有的因果关系是显然的,意志自由并不体现在意志与行为的全然一致性上。正如Honderich所指出的,“一个行动是被引起的”这个事实在三个方面与某种意义上的“责任”是相容的:(1)法律上的严格责任;(2)对惩罚进行回应的责任;(3)来自于非强迫的意图的责任。
一个情节语境中的惩罚透视
康德强调:惩罚在任何情况下,必须只是由于一个人已经犯下一种罪行才加之于他。 没有任何理由对一个尚未犯罪的人进行惩罚,即使我们知道他很快将会犯罪。
我们可以在一个情节语境中对这个问题进行纵深讨论。在一部最近热播的韩剧中有这样的情节设定:女主角能够通过梦境来预知未来将发生的事件,例如即将发生杀人案且被杀者正是身为检察官的男主角,借由梦境的蛛丝马迹,甚至可以大略推断出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这种设定似乎暗合了决定论的观念,一切因果性都注定了该事件的发生。女主角已然预知到结果,但她在意愿上并不期许这样的事件,因而她力图要改变时间轴上的“因”,改变事件的进程轨迹。在此,人的意志似乎开始介入。女主角没有清楚看清杀人犯的面容,但终而排查到有可能有杀人动机和倾向的男子A,男子A在男主角受理的案件中蒙受冤屈经受舆论暴力,心生怨愤,因而女主角对男子A进行开解和劝慰,并通过媒体渠道向公众证明男子A的清白,消除了男子A心中的怨恨与复仇意欲。我们可以设想,纵使女主角清楚地知道了杀人犯是谁,她能够在杀人事件发生之前就对杀人犯进行指控和惩罚吗?当然不可以,这既不符合逻辑,也没有任何现实依据。因为对于杀人犯而言,杀人的意图和动机并不会在绝对意义上导向杀人行为,也不构成杀人的充足理由。女主角显然是一个非决定论观点持有者,她相信通过梦境中呈现的未来并不是100%确凿的,未来不是仅有一种可能,而是有改变的空间和余地。她在用意志介入时从事件的结果溯源至原因,在因果性上改变事件的走向似乎又依循着决定论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女主角是一个相容论者,决定论和自由意志之间并非是一种强烈对撞的尖锐冲突,她的行为是能够被我们的经验或思维惯性所能理解和接纳的。
相容论视角下的惩罚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已经简略地论证了惩罚概念与决定论之间的冲突性,决定论是一种直接而简单的阐释方式,它同时以一种环环相扣的因果链条延展,具有很强的逻辑力和说服性。但就我看来,决定论所临遇的最大挑战并非来自“自由意志”的概念,而是人生的无意义性。从过去到当下再到未来,我无需对他人负责的同时也丧失了对自我负责的机会。无论这条时间轴线多少次地前进倒退甚至重写,我的人生都像是一部拍摄完成的影片,仅仅在一段进度条上来来回回。那么“我”的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似乎等同于虚空的假象。自我变成了因果的产物,变成了一个拥有确定性的空躯壳。
但是,我们如此鲜活地处在当下,我所经验到的每一个抉择都如此真实,所经历的犹疑徘徊也如此真切,要在决定论的理论下抽离我们自主生活的能力,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
只有确认了自由意志的存有位置,我们方才会进一步讨论惩罚的必要性。当我们受自由意志支配时,亦是同时被抛入了时时刻刻的不确定性之中。任何抉择的主体“我”承载着完整的逻辑线索,从【实施行为的意志】到【行为本身】,再到【行为的结果】,自我都在经历抉择,“我”成为整条因果链的构筑者。
惩罚的概念同时亦在相容论的立场上被广泛讨论,霍布斯和布拉姆霍尔关于自由意志问题的论辩是一个具有良好视域的切口,在双方观点的交互中,矛盾得以呈露,我们也能更好地看到惩罚这个概念在不同立场角度所经受的变化和挑战。
布拉姆霍尔捍卫自由意志的存在,并借由捍卫自由意志的必然性来证明奖赏、惩罚的合理性。在自由意志与责任的关系方面,布拉姆霍尔认为,“为行为负责、因而应受赏还是应受罚的必要条件,是一个人的行为由自由意志所引起。”
但是霍布斯秉持相反的立场,他认为“与行为的赏罚分配相关联的,是此行为到底是遵守了道德律或民法,还是违反了道德律或民法”,赏罚是依据道德律或法律所订立的标准,《圣经》中诸多赏罚的例证并不能在支持或推翻布拉姆霍尔观点上发挥作用。
而布拉姆霍尔所临对的问题在于,如果每个行为都由先前的时间所决定而成为必然发生的,那么禁止人们行为的律法就会丧失其合理性的根基而分崩离析。一切的劝诫都丧失了意义,惩罚自身也会站不住脚。
霍布斯试图将法律框限在了决定论的畴域中,并把法律制作一种强制的规约力量。霍布斯忽略的一点在于,在他自认为成功地抹除了惩罚必要性的同时,他是不是也将法律的必要性一并消解了?霍布斯当然会针对这种质疑进行辩解,他认为,“人因此并非因其出自自我选择的偷窃行为而受死或受罚,而是因其有害于和有悖于人们的保全而受死或受罚”,但我认为这样论证法律的必要性并不充分有效,换句话说,似乎只要将法律概念置换为惩罚概念,这种论述依然能够成立。在霍布斯硬生生将法律和惩罚置于不甚相关的两极时,他同时也面临着为法律寻找根基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