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总结
文章介绍了社会学会社筹备推出的新栏目“读者来信”,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分享对社会学思考和困惑的平台。文章引用了读者“丹可”关于田野调查的困惑,并呼吁读者通过特定渠道投稿交流。内容包括对质性研究中尴尬情况的处理、对真实与谎言的取舍、研究的意义与联系等问题的思考。
关键观点总结
关键观点1: 新栏目“读者来信”的目的
通过文字建立精神情感连接,打造互动、分享、启发的公共知识平台,回应读者对社会学的思考和困惑。
关键观点2: 读者“丹可”的困惑
涵盖了田野调查中研究者面临的道德选择困难、如何取得调查对象信任、研究是否真正反映社会学规律等问题。
关键观点3: 投稿交流和邀请
面向读者开放投稿交流,内容可以是学习、研究或生活中的所思所想所感,不必符合学术规范和门槛。
正文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正在筹备推出全新的原创栏目
“读者来信”
。这是一次面向长期以来支持社會學會社的朋友们的特别邀请。我们希望通过文字,与大家建立更紧密的精神和情感连接,打造一个互动、分享、相互启发的公共知识平台。

在平日学习课程或阅读理论专著时,作为读者的你,是否常常有困惑与不解,想要一吐为快?面对布迪厄等理论家令人“头秃”的著作,是否会觉得明明“每个字都认识”,但知识却如何都“进不了脑子”?这究竟是作为读者的我没有认真读所致,还是那些学者本就在故弄玄虚,亦或是能真正触动我内心的那位社会学家还未与我相遇?
在学界已有的议程设置下,作为初学者的你,是否常常质疑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议题的价值?是否也曾被迫选择自己不感兴趣但容易发表的题目,而将真正感兴趣的题目默默藏在心里?即使千辛万苦做完了调研,文章能否发表?是否需要绞尽脑汁地套用理论概念,以求满足学界的学术规范和审美口味?
在田野调查与日常生活中,作为调研者的你,是否面临着“道德选择的困难”?如何才能取得调查对象的信任?我到底要不要给ta送礼?这件事能不能写?可不可以录音,录音应不应该告知对方,告知对方如果被拒绝了怎么办?
更进一步地,我所做的研究是我心目中的“社会学”吗?惯常使用数据分析的朋友,每日对着电脑爬取各种数据,却不知能否从中找到用以分析社会运行的规律。田野研究者或许也面临类似的困境:调研过程中鲜活、真实的人与人互动过程被处理为一个个理论概念进行命题分析,社会学的味道有了,但离“人”却好像越来越远了。当那些真正打动我们的故事和瞬间以“实证”的名义被裁剪、被丢进垃圾桶,留下来的“客观”之物能否支撑起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理论想象?
“读者来信”
栏目旨在为各位读者朋友提供一个“可以说说对社会学的心里话”的平台。你是谁、有着怎样的title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作为一个人类个体,在学习社会学的过程中,是怎样认真、用力地思考——这些思考无需符合所谓的学术规范和门槛,只要你想说、说的是你关于社会学的心里话,就足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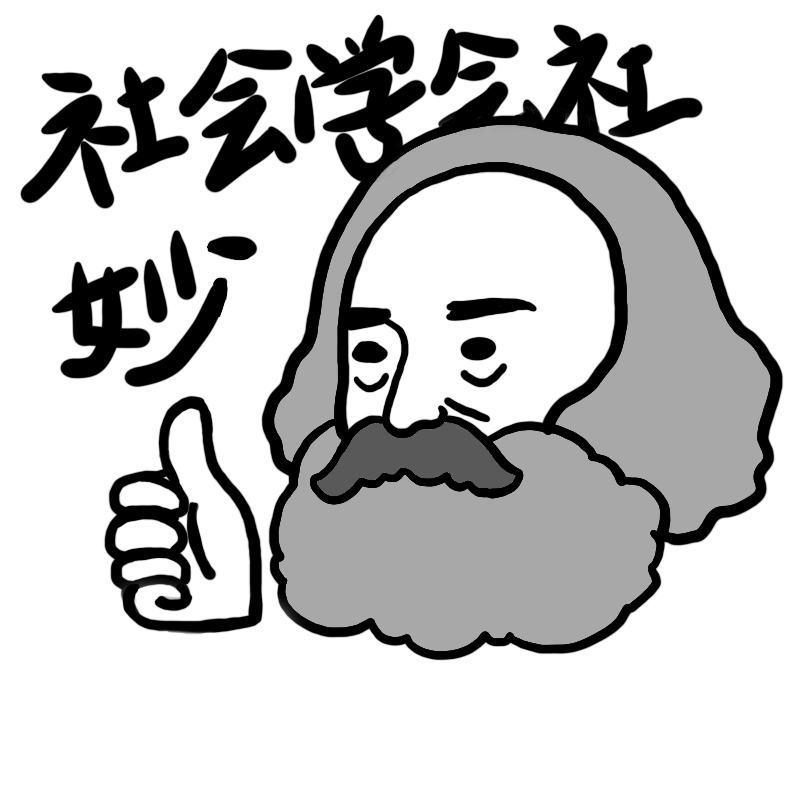
作为引言,本期推送也摘录了一位读者朋友对于田野调查的困惑与思考,希望借此激发读者朋友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我们相信,好的问题是最重要的,而好的答案则不一定来自书本。很多时候,真正触动我们的答案,或许正是跟我们有同样困惑的朋友的体悟。
以下是这位读者朋友分享的调研困惑:
你是否曾试图在田野调查时,为自己的调研和访谈找到合理的“借口”?
当我们把这些伟光正的说辞强赋给当下的研究时,是否会对受访者在访谈中的叙述产生影响?当我们虚构出一个并不存在的“导师课题项目”时,本质上仍然是为自己的研究寻求一个更高层次的合法性背书,而这是否体现了研究者试图在研究情境中实现权力不平等的翻转从而以高位者的姿态引导研究的进行?
——《质性研究中的“尴尬”——基于田野工作中的个人困惑》
当受访者流露真情时,你是否会感到无所适从,不知如何给予情绪上的支持?
面对受访者的真情流露,我没有提供任何情绪上的安慰或支撑,只是用沉默来化解他内心如浪涌般翻滚的辛酸回忆,在他平复情绪之后继续访谈,这算得上是共情式理解吗?当研究者的提问导致被研究者情绪失控时,研究者该如何处理这种情绪上的尴尬?
——《质性研究中的“尴尬”——基于田野工作中的个人困惑》
在社会调查中,你是否也曾在观察到的“真实”和受访者的“谎言”之间难以取舍?
面对这样的“谎言”,我应该选择相信谁吗?还是我应该思考,为什么受访者在访谈中向我隐瞒其真实的生存状况?进一步而言,为什么我会在得到前后矛盾的信息之后“自然而然”地选择了相信后者,这是否体现了我在研究中的某种价值立场或对被研究者的某种预设?
——《质性研究中的“尴尬”——基于田野工作中的个人困惑》
调研结束后,你是否会怀疑自己的研究能否实现预想的现实意义?
我深知自己的研究不过是完成毕业论文的任务,甚至连能否发表都要打一个问号。即使万幸之中能够发表,但人微言轻,只会被少部分有着相同旨趣的研究者看到……研究最大的“意义”,可能就是在寻求发表后作为一项学术成果,也可能成为我拿到一份奖学金的关键筹码,但我该如何面对我的报告人曾幻想的那个无障碍蓝图?我在结束研究之后该以何种姿态与他们联络?或者说,我还需要同他们联系吗?
——《质性研究中的“尴尬”——基于田野工作中的个人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