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德国优才计划
(
ToGermany
)获授权转载
在中国有这样一位老人,
他一生跨越了晚清、北洋、
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代,
堪称“四朝元老”,
跨经济、语言、文化三个领域。
他是中国著名经济学、语言文字学家,
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订者,
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
是仅有的,
曾和爱因斯坦会面的几位中国人之一,
再过几天他就要112岁了,
男性中少有的高寿,
现在他依然思维敏捷,
口齿清晰,红光满面,
绝对的中国国宝级老人。
他就是周有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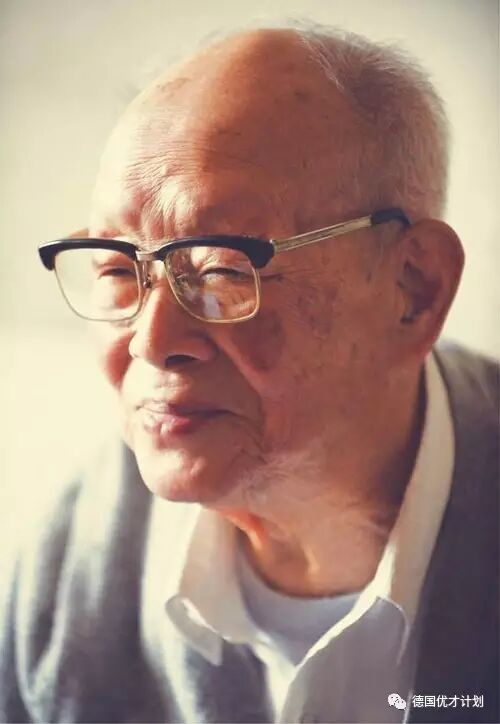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
1906年1月13日,
出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
一个贫穷破落的家庭。
青果巷是一条著名的弄堂,
除了周有光,
这里还曾走出两位中国语言学大家:
赵元任和瞿秋白。
一巷三杰,令人称奇!
1918年,他考入常州中学,
当时白话文不允许进入课堂,
有一位老师思想很新,
经常在课外宣传白话文,
令周有光对语言产生了兴趣。
那时常州中学的课本,
基本都是英文的。
等到他走出中学时,
已经有了很高的英语水平。
1923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
主修经济学。
1925年,再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

他年轻时的命运并不顺利,
甚至可以说是错位的……
大学毕业后,外语流利的他,
本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当外交官,
而他却偏偏选择再出国留学,
由于当时家境拮据,他只能选择日本。
因仰慕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
他离开原本就读的东京大学,
转考入京都大学,
结果还未拜师,河上肇就已被捕入狱。
从日本学成归国后,
他边在光华大学教书,边在银行工作。
不久后,日本侵华战争就爆发了,
他不得不带着全家四处逃亡。
1945年,抗战胜利,
他回到新华银行任职,
去了美国的华尔街上班,
终于过上了舒适、安稳的日子。
后来,他被银行又派往欧洲工作,
在那里,他发现欧洲人对字母学很重视,
于是买了许多字母学的书自学。
1949年,在国外生活优越的他,
却毅然选择了回国。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体会不到,
我们当时的感受……
我们都认为中国有希望……
学经济那么多年,我想中国当时,
最缺乏的也是经济建设,
于是立志回国搞经济。”
回国后,他继续在银行上班,
并兼职在复旦大学教经济学。
本可以领取上海最高工资的他,
却赶上了工资改革,薪水大减,
一百块只能拿到二十块,
但他却对回国的选择毫无怨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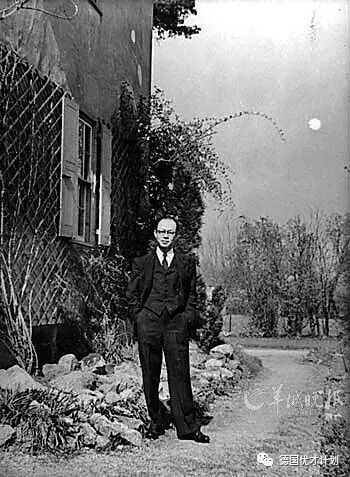
他知识渊博,什么都懂,
大家都叫他周百科,
他的百科全书里,
玩的最好的是语言学。
他一直对语言有着浓厚的兴趣,
大学期间,
就曾积极参加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
还发表、出版过一些关于,
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论文和书籍。
受到了语言学界的重视。
1955年10月,
周恩来总理在看到他写的书籍后,
亲自点名让他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
之后他又被文字改革委员会力邀,
希望周有光能够加入其中。
他有些犹豫:
“我搞语言是业余的,搞着玩呢”。
但文字改革委员会,
却坚持请求他加入。

后来,
周恩来总理都亲自打电话给他。
周有光因此决定北上,
从此开始了新的人生。
“就这样,我离开了经济学界,
到了语文学界。”
而正因为改行,
他幸运地躲过了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
同时期的上海,
一批经济学家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他的领导和学生在那个时期,
很多人受迫害而选择了自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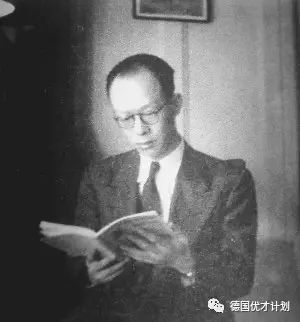
50岁前,
学的是经济学,
从事的是金融业;
50岁后,
在知天命之年,
却重新出发,研究语言学。
但半路出家的他,
却毫不畏惧,
以一种朴素的精神专研其中。
他主持和拟定了《汉语拼音方案》,
主导和建立了汉语拼音系统。
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
成为了全中国小学生的必修课程,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拼音方案,
因此,他被称之为中国的“汉语拼音之父”。
他还出版了《汉字改革概论》、
《世界文字发展史》、
《比较文字学初探》等20余种著作,
以及三百多篇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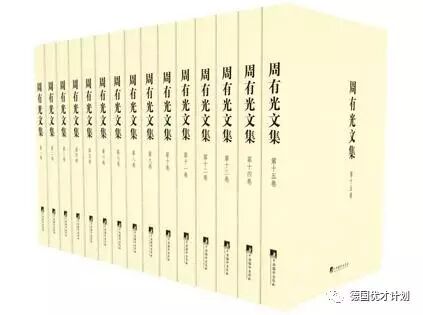
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
在华沙召开文献技术会议。
周有光在会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
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
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三年后,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
认定汉语拼音方案,
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
他为汉语拼音从中国标准走向世界标准,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没有他,
就没有我们中国人现在的汉语拼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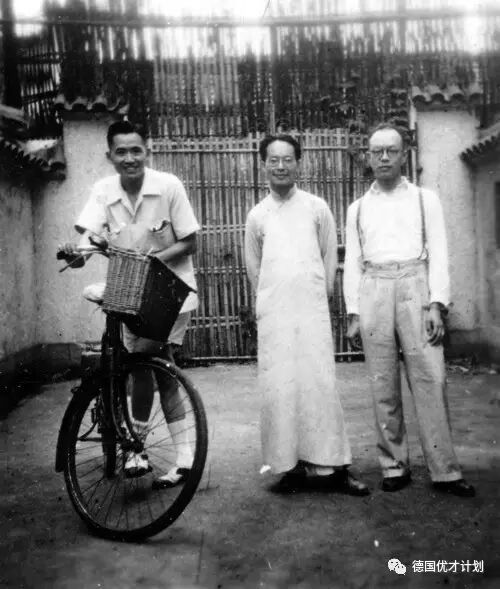
左三:周有光
他虽是语言学大家,
生活中他却从不说甜言蜜语,
也不写含情脉脉的文字。
但是他却有着一段,
比温情的文字,更令人动容的爱情。
1933年,
他和赫赫有名的张允和举行了婚礼。


张允和出身于名门望族,
合肥张家四姐妹:
元和、允和、兆和、充和,
在中国乃至国外都赫赫有名。
张允和是“九如巷的张二小姐”,
叶圣陶曾说:
“谁娶了九如巷的姑娘,
谁就会幸福一辈子。”

张允和读中学的时候,
是周有光妹妹的同学兼好友,
因住得很近,放假了经常一起玩。

后来张允和考入上海的中国公学,
那时周有光正在上海的光华大学读书,
此时的张允和已亭亭玉立,清新脱俗。
同在一座城市,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
再相遇时,他便一见钟情了。

有一天,他从怀中小心翼翼地取出了,
英文版小说《罗密欧与朱丽叶》,
他把书签夹在书中,
待她翻到夹着书签的那页,
一句“我要在你的一吻中来洗清我的罪恶”
让她的心荡起了层层涟漪,
她在心里嘀咕,
“这人真坏,以为我不懂”。
他也有些难为情,
但他还是鼓起勇气牵起了她的手,
虽然最后,她没有允许为他‘洗净了罪恶’,
可是当她的第一只手被他抓住的时候,
她就把心交给了他……

不久后,周有光却犹豫了起来,
他写信给她说:
“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
而她却回信说:
“幸福不是你给的,
而是我们两人一起创造的。”

他们两人的性格和爱好其是截然不同的,
张允和活泼率性,说话直接。
周有光安静沉稳,温文尔雅。
张允和喜欢清茶,
周有光偏爱咖啡,
张允和极喜欢中国古典音乐,
周有光却偏偏喜爱西洋音乐。

但就是这样两个人,
竟如涓涓细流般,
相濡以沫,携手度过了,
余下的70年的光阴。
他们似乎水火不相容,却实则很互补。
两人举案齐眉,琴瑟和鸣。
“结了婚,她听中国音乐我去参加,
我听西洋音乐她也去参加。”
只要是对方喜欢的事情,
他们彼此都会陪伴左右,
成双入对,恩爱无比。

张允和是兄弟姐妹中最早结婚的。
有朋友开玩笑说她犯规抢在了前头,
她就瞪着周有光说:
“可不是,不要脸,那么早结婚。”
一旁的他哈哈大笑,说:
“张允和这个女子最聪明,
可她干的最蠢的事就是嫁给了周有光。”
的确张允和与周有光在一起,
经历了动荡的一生。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时,
她跟着周有光全家四处逃亡,
逃难期间,他们的女儿因病不幸夭折。
抗日战争结束,到了新中国,
虽然躲过了反右运动,
但周有光却没能躲过文革,
文革时,他被群众揪出来批斗,
张允和毫不犹豫地就冲过去保护他。
他身体不好,被下放到干校,
她不畏权势,坚持给他寄药。
无论相隔多远,他们的心始终在一块。
恩爱如初,患难与共。

到了晚年,
他们俩蜗居在一个小房子里,
书房仅仅只有9平方米。
书桌前两椅一几,
古代夫妇“举案齐眉”,
如今人们很少有案了,
他们就发明了“举杯齐眉”。
每天到了约定时间,
他们就不疾不徐地并坐。
“我们两个上午喝茶、下午喝咖啡,
都要碰碰杯子,叫举杯齐眉。

周有光说:
“这个小动作好像是在玩儿,
其实有大道理,什么大道理呢?
就是说夫妇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敬。
要敬重对方。”
多情人不老,
多情到老,人更好!

张允和86岁才开始学电脑,
每当遇到问题时,
只要她一跺脚,撒下娇,
周有光就马上放下手头的事情,
乐悠悠颤巍巍地从书房里出来,
耐心地教她。
有一次,她想给大姐张元和写信,
“亲爱的大姐……”
没想到“爱”字一直打不出来,
她着急了,娇滴滴地喊道:
“周有光,这个‘爱’字打不了,
我爱不了了怎么办啊。”

他们都十分地乐观、豁达。
张允和的口头禅是‘我快乐极了’,
而周有光对于艰辛的下放岁月,
总是一笑而过。
他还说那几年,为他打开了视野呢!
还时不时地会说起一些趣事:
“天上飞来一群大雁,
黑压压如同一片乌云。
飞到我们头上的时候,
只听到一位大雁领导同志一声怪叫,
大家集体大便,
有如骤雨,倾盆而下,
准确地落在集会的‘五七战士’头上。”
腌了整个会场,
唯独他戴顶大高帽子幸免于鸟粪。
苦难的经历,就这样被他诙谐的一笔带过了。

到了晚年,
他常对着自己的光脑袋说:
“我的头发还没有长出来呢!”
当他91岁的时候,
有人问他多少岁了,
他幽默地回答,我今年11岁。
张允和则在一旁补充道:
“他自己认为,
人活到80岁,已算“尽数”,
后面的应从零开始计算。
我也不过是二八年华。”
这两夫妻,
真是一对快乐的老顽童!

2002年8月,
张允和因心脏病突发离开人世。
他默默坐在床前,望着她宁静的脸,
一直握着她的手不肯放开。

一向豁达的他,
这一次却怎么也无法释怀,
就像天塌了一样:
他说:
“允和的去世,
对我是晴天霹雳。
我们结婚70年了,
从来没想过,会有一天,
我们二人之中会少了一人。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
曾使我一时透不过气来。”


至爱已去,
独留他在人间空思念。
从前出双入对,
而今,只剩他一人寂寞的背影。
他常常坐在书桌上对着窗外发呆,
魂牵梦萦,望眼欲穿,
到了晚上,就直接蜷缩在沙发上入睡。
后来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才从张允和的离去痛苦中走了出来……

如今的他,
马上就要进入112岁高龄了,
他依旧面色红润,鹤发童颜,
甚至逆生长,长出了黑发!
他笑称自己是“被上帝遗忘的人。”

百岁的年纪,
还能思维敏捷的人实在少有,
但周有光算一个。
著名诗人聂绀弩曾写诗来称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