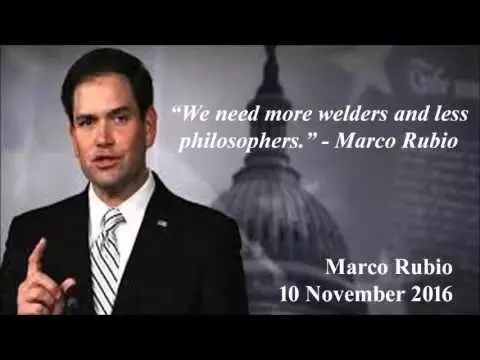
(图片来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xl5wD6U6fU 截图。
编者注:
需要更正的是,截图中显示的日期应为2015年11月10日。)
黄远帆
丨
主要研究元哲学、认识论,致力搭建学院经院哲学与外界的交流桥梁。
美国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在2015年的一次共和党辩论会上宣称,社会需要更多的焊接工,更少的哲学家。
可以说,卢比奥的论断蕴含了一种对哲学的偏见。通俗而言,就是认为哲学没有用,哲学不能用来果腹,哲学不能用来漂洋过海,哲学不能用来焊接,那么哲学到底有什么用?我还很清楚记得当年考上研究生去向上司提交辞呈时的情景。当上司得知我要去学哲学时,既惊讶又担心地感慨:「学哲学将来能干什么呀!」哲学无用论是人文无用论的一个典型。而另一方面,我们发现不太有人会去质疑自然科学是否有用。这背后隐藏着文学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张力。
1959年5月,斯诺(C. P. Snow)于剑桥大学作了「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讲演。这次报告中,文学文化与科学文化的断裂被彰显了出来。自此之后,这方面的讨论不绝如缕。有趣的是,斯诺在报告中批评当时重文学轻科学的风气。然而在当下的社会,天平显然是偏向科学文化的。
人文学者显然不会满意当下的这种论调。哲学家纳斯邦(Martha Nussbaum)为普特南(Hilary Putnam)所撰悼文标题便是醒目的「为哲学而辩」。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主张人文学科的重心在于「人的养成」,人文的薰陶可以涵养心智,活泼性情。也有学者指出,哲学的作用是为了给人提供一种理解方式(维根斯坦式的思路)。还有些哲学家甚至承认哲学就应该是无用的。比如冯友兰说:「哲学对现实问题并不试图去具体解决。举例来说,哲学不能帮助人长生不老,也不能帮助人发财致富。」英国形上学研究者芒福德(Stephen Mumford)提到过,有时形上学的问题更像是稚童的提问。长大后,我们似乎不太会继续追问诸如「什么是圆」或「时间是否流逝」这样的问题。就「什么是圆」这样一个问题,形上学学者可以给出一个极其繁细的说法。但普通人会说,这又有什么用呢?芒福德最后承认形上学也许真的没有什么用。但他仍然强调我们不应仅通过工具价值来衡量事物。他认为形上学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的内在价值。
英国哲学家梅勒(D. H. Mellor)对这个问题有过更为值得借鉴的思考。本文尝试重新勾勒梅勒的想法,透过梅勒的视角,来回答哲学是否有用这个问题。

(图片来源:http://people.ds.cam.ac.uk/dhm11/)
能力之知
为何我们会觉得科学比较有用?一个拍脑袋的答案:因为科学为我们提供了各种技术。电脑科学为我们提供了人工智慧的技术,医学为我们提供了治疗顽疾的技术。据我所知,现在美式橄榄球头盔的设计都有着很强的科学支持。首先,有必要简要澄清一下「技术」这个概念。英语日常语言中,「technology」,「know-how」,「skill」,「ability」等都是同属于一个家族的语词。即:技术往往与能力、技能这些概念相互勾连。比如,在美剧《闪电侠》(The Flash)中,威尔斯(Wells)说过这样一句话:「Well, let me take that technology, let me take that know-how into ensuring that your son actually does have a future.」我们选择「know-how」来切入问题。近年来,学院哲学对「know-how」的讨论络绎不绝。对「know-how」的哲学考察,可以追溯到牛津学者赖尔(Gibert Ryle)的工作。赖尔提醒我们注意有两类不可互相还原的知识,命题性的知识(know-that)与能力之知(know-how)。大致来说,这对区分类似于我们平日所说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对立。比如,哲学家提供的关于真理的理论就是典型的理论知识,而焊接工的技术则是典型的实践知识。
基本上,我们认为这两类知识不能互相还原。比如,一个坦克设计专家,即便他对坦克内部每一个细小零件的作用都瞭若指掌,也并不意味着他会驾驶坦克。同样的,一个玩耍杂技的行家,他未必知道这些杂耍背后蕴藏的物理知识。虽然两者有种类差异,但现实中,两者往往相互依赖。对科学知识(know-that)的求索需要科学方法与技术(know-how)的支援。而一个医生要施展医术(know-how),也势必要了解病人的一些情况(know-that)。梅勒指出,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依赖不限于科学。比如,对色彩知识(know-that)的掌握会影响绘画的技能(know-how)。而对于作画的物件(know-that)的选择又离不开经年累月所习得的色彩感知力(know-how)。鉴于此,可以说「know-how」与「know-that」的区分不仅适用科学,也适用人文。海德格尔曾指明,希腊语词「techne」(相当于know-how)不仅指涉工匠的技术,也指涉艺术才能。既然所有的学科都蕴含了「know-that」与「know-how」的区分。那么,我们不能仅仅诉诸科学能够提供「know-how」(技术)来判定科学更为有用。
工具价值与内在价值
另一种理解有用性的方式是通过「手段」与「目的」这组概念。说一个事物有用往往是因为它能够作为达到某个目的的手段。那麽,只有当技术(know-how)可以作为手段的时候,它的有用性才会得以体现。只有当科学知识能够转化为应用技术时,科学的有用性才会得到彰显。但是,人文知识也能充当手段,比如,写小说是为了被阅读。既然如此,在何种意义上,我们还能坚持说科学更有用?一种回答是:科学提供的技术是人类所有需求的基础,也就是说科学提供的「know-how」更为有用。
梅勒认为下这个论断为时尚早。判断某物是否有用应该立足它作为手段如何服务它的目的。因为我们知道用途也有好坏之分。用途的价值取决于手段所指向的目的。有句老话叫:「好钢用在刀刃上」。如果用一块好钢来垫桌角,虽然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我们可能更倾向于说这块钢没有物尽其用。又如,用一把刀来砍柴,可以说刀发挥了它应有的价值。但如果用刀来伤人,那么显然只是发挥了负面的价值。因此,当我们判断一样事物是否有用时,应该着眼于它作为手段所服务的目的。印刷技术为了书的出版服务,那麽可以说印刷技术作为手段,它的价值取决于最终出版物的价值。
哲学中会大致区分两类价值:工具价值(instrumental value)与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内在价值指事物本身的价值,而某物的工具性价值须要通过它如何服务于另一个目的来体现。现实生活中,这两类价值往往糅合于一处。比如,我去买一块巧克力。巧克力的工具价值体现在它是满足我味觉享受(或食欲)的手段。但在两块价格相同而包装不同的巧克力之间,我会愿意选择包装较为精緻的巧克力。甚至,有些人会更在意于巧克力的外观(内在价值),从而可以忽略它的口感(工具价值)。
梅勒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价值衡量概念:「净值」(net value)。当一个事物作为手段时,它的价值应当通过计算工具价值与内在价值互相抵消影响后的正负值来衡量。这样的话,有时一个手段的价值可能是正值,有时则可能是负值。比如,我有一件NBA篮球球衣,这件球衣尺码太大,我无法穿着它打球,那么这件球衣的工具价值对我来说是消极的。但另一方面,这件球衣却是我锺爱球员的球衣,我视如珍宝。那么于我而言,它的内在价值的正值可能就会弥补其工具价值的负值。
再如,当我们评价建筑物的价值净值时,它设计审美体现的内在价值可以抵消它在实用性层面瑕疵的负面工具价值。当然,也存在工具价值弥补内在价值的情况。一个可能有些争议的例子:枪决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排除他之后行凶作恶的可能性(工具价值),这也许能够一定程度平衡杀害生命本身这个具有负值的内在价值,从而使得淨值能够成为正值。2016年上映的美剧《善地》(The Good Place)中有一个有意思的设置。在这部剧集的世界裡,所有人的生平所作所为都会被计分(被计分者并不知情)。有些言行会被记为正分,比如帮助邻居搬家可能会加十分,救助难民可能会加二十分。而另一些言行可能会扣分,比如陷害他人可能会扣十五分,偷盗可能会扣二十分。在离开人世后,你的下一站去处取决于你在人世间的分数。得到较高分值的人可以升入善地,而分值不理想的人,则会堕入恶土。如果引入梅勒的淨值概念,也许可以使这部剧集中的计分设定更为合理。
为哲学而辩
那么,在什麽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哲学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呢?我尝试运用梅勒的三点理由来为哲学辩护。
首先,是否有用并不是价值评价的唯一途径。很多时候,我们更关切某事物的内在价值。
比如,伦勃朗(Rembrandt)的《夜巡》,罗丹(Rodin)的《思想者》,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的《天鹅湖》,卡夫卡(Kafka)的《审判》,等等。我们欣赏、看重的是这些作品的内在价值(审美意义上的格调)。那么哲学作品自然也是如此。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斯多德的《形上学》,笛卡尔的《第一沉思录》,哪一部不是举世欣赏的杰作?这些作品的内在价值是不容质疑的。
其次,如前文所提,我们应该通过「净值」来评价一个手段的价值,而衡量淨值则既须考量工具价值,又要考虑内在价值。甚至,我们可以设想一些内在价值完全取代工具价值的情况。
比如,一架早期型号的飞机,如今可能已经无法再正常运行了。但它代表了当时的设计理念,因此被放入了博物馆。那么,它的内在价值完全超越了它的工具价值。如果我们完全剥离一个有用东西的有用性,它仍旧有价值的话,这意味着它的净值并不完全取决于它是否有用。就哲学而言,即便许多思力深刻的作品未必有着很高的工具价值(显然我们不能用哲学作品来治疗疾病,毕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作为治疗是一种隐喻),但在净值层面,哲学作品的分值则是有可能会高出一些科学知识的。
最后,我们说过,事物的工具价值应当立足于它所服务目的的内在价值。
同样是建造一栋楼宇,如果是用来作为医院的话,那麽它的价值是积极的。而如果用来作为虐待囚犯的场所,那么它的价值是消极的。那么,如果要比较科学与人文之间哪个更有用,则应该立足于他们各自所服务的目的。从这个角度而言,较之科学,人文学科并不处于劣势。历史上,人文思想的传播和发展,带动了诸多社会运动。比如,启蒙运动开启了人类理性之门,它影响了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得益于启蒙运动,黑奴被废止了,女性地位也得到了提高。再如,辛格(Peter Singer)等哲学家对动物权利的讨论引起了人们对动物保护的关注。这样的例子不一而足。鉴于上述三个理由,我们可以说哲学无用论的论断并不经得起仔细推敲。哲学工作者应当得到世人的尊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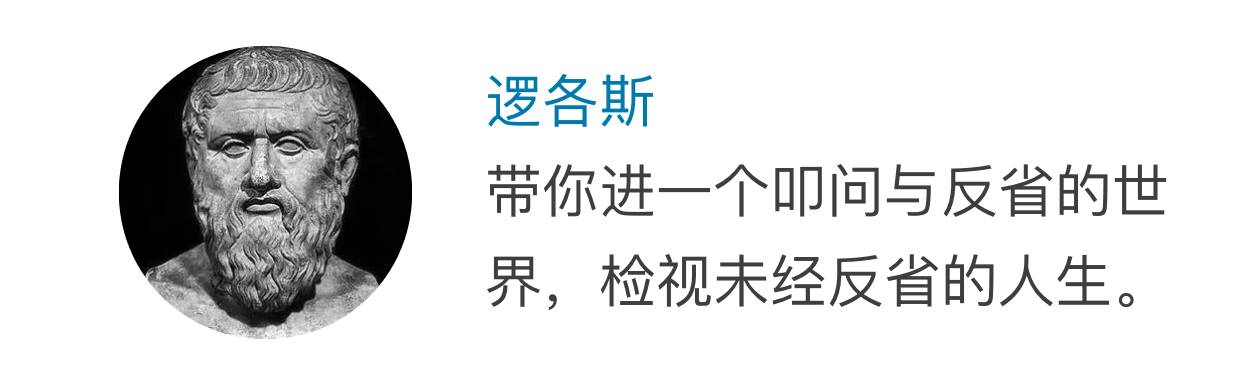
[email protected]
微思客重视版权保护,本文正体字版首发于微思客传媒香港合作方“香港01哲学网站”,经授权以简体字版转载。如需转载,请务必联系”香港01哲学“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