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诺贝尔文学奖当做狂欢当做赌博当做营销事件甚至当做大众教育,很可能都是错误的打开方式。我感到只有少数真正的热爱文学的人,等待这一天就像等待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等待一个未知女人的婚礼,能够幸运地把一位新的从未阅读过的作家,郑重地带到他们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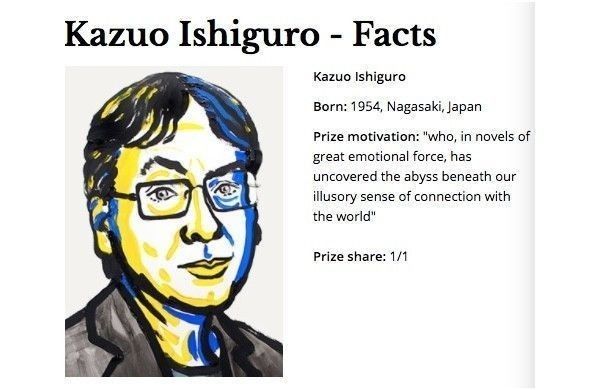
▲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 ( Kazuo Ishiguro ) 摘得 2017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为:“他以巨大的情感力量,揭示了隐藏在幻觉中的,我们与真实世界相连的暗河。”(图/诺贝尔奖官网)

每年当所有媒体都绞尽脑汁等待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的这一段时间,你不知道我们有多希望自己可以视而不见。一来所有凑热闹的行为都是可疑的,二来阅读范围有限,我们并不认为自己可以站在高处来点评国际文学。事实上文学甚至整个艺术领域的评选本质上也都是可疑的,文学和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应该挑战权力秩序,而不是成为它——尽管反对本身也是权力并且盛产权力,这也是很难去评论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原因。
今年恰逢国庆和中秋假期,感觉半个中国都要出国了,当我们提前准备足够的内容,关上办公室里所有的电脑和灯的时候,原本放心地以为今年又可以蒙混过去了。一定会有足够的声音,不需要谁再多说什么。
结果很意外,瑞典文学院今年似乎重回旧轨,没有试图在时代变迁、地缘政治/文学的最新情况下矫正自己的“正确”,而是选择了一位早就获得文学圈和读者共同认可的作家,也是一位来自主流英语国家的作家,石黑一雄。

▲石黑一雄
他是我们熟悉的作家。他也是在中文世界有着良好的翻译和阅读基础的作家,也有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这次好像可以尽量排除一些场外因素来谈谈文学。(加上单位领导的要求)我们好像必须发言了。
主编吴琦应知乎之邀,简单谈了谈他对石黑一雄的阅读感受。略作修改和补充,也发在这里。不是什么严肃的评论,完全是一个正从火热的工作中逃离的读者在异域的旅途中胡乱写就的信,有他的心得和疑惑,也有任何生活和文学历程本身的敏感和仓皇。
读者能够遇到作者,这本身就是偶然的,但我们常常感到偶然常常不足够解释这一切——从这个角度我们理解了所有的文学评选、评论和推荐的机制本质上都是试图在澄清这种偶然性,因为越是偶然,我们就越倾向于相信背后的必然性,并且期望自己有一天能否捕获它。正是在这种相信当中,读者和作者猛然地相遇,而文学像大鱼一样穿行而过,狡猾地脱身,获得了真实的生命。
石黑一雄是我钟爱的作家,也是花了一段时间来追踪的作家。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他最吸引我的文学特质来自早期的几部作品,包括处女作《远山淡影》(1982)和很受读者欢迎并改编成电影的《长日留痕》(1989),就像颁奖词中着重提出的“幻觉”、“与真实世界相连接的深渊”,都指向了他对记忆的持续挖掘和细腻展示,回忆与回忆者之间的关系,回忆与社会历史的共振,这些复杂的问题在他稳健的叙事中不断深入,成为一个母题,也始终是他的文学起点。

▲《长日留痕》电影剧照
最特别的一点是,即便我们带着移民作家的有色眼镜来观察他,也不太能在他的作品中发现这种身份的痕迹或者焦虑,这是他下笔比较高级的地方。他很少直接书写那种异域、他者的经验,换句话说他很少直接书写自己。比如他写一个老旧的英国管家的情感与记忆,或者战争中的一对母女,看起来都和他自己的生命体验没有直接关系,完全满足不了一般读者对于作者的窥私欲,但仔细联系到他个人的历程,联系到他所经历的二战以来的社会变迁,本质上又是血肉相连的。人类是怎样来记忆的?我们的尊严和正义要被变化冲刷到哪里去?这些都是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重大问题。他的书其实一直在对此予以回应。
但历史和现实的流动性,被他幻化成了更本质的文学语言,更简单地说,被他文学化了。只剩一些残骸,遗留在故事中,在故事的结构和节奏中,在故事的氛围中。我们可以读到那种隐晦的恐怖、克己复礼的保守、既焦灼又温柔的叩问,其实都在秘密地暗示,这位作家的日本、英国气息。但隐晦得几乎只是一种猜测。这在国族认同变得空前激烈的今天,是很不起眼的品格。他似乎不想暴露或者过分利用自己的现实位置,并且证明了这并不会剥夺一个作家在写作上所占据的位置。因此,作家本人身上的谜团,故事中的氤氲之气,在我看来成了他身上最迷人的部分,与他稳健从容的节奏、缓慢延宕的语言互为表里,成为一个自足的创造者。也让他很难被一两个标签所定义和概括。这也是为什么所谓的“移民作家”从没有真正阻断他和读者之间更广泛的联系,而是让他在被封神之前,就不再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名字。
反而我并不觉得他其他几本实验或变身转型之作有特别的新意,比如2015年的《被掩埋的巨人》、或是再早一点的《别让我走》(2005)、《无可慰藉》(1995),都有中文译本。叙事的重力、速率都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准,但主题和故事上愈发抽象化、隐喻化,很多故事都完全在想象、寓言、传奇甚至科幻中行走。不知道是他的写作策略和自我要求必然地使他在形式上离现实太远,还是他写作起点处的那种动机离现实越来越近,但给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是,原本最吸引我的那种虚实之间的距离感、穿梭感和伸展性,突然变得太容易琢磨。


▲小说《别让我走》被改编为日剧和电影
他身为严肃作家的身份,身为世界公民的认同,逐渐从幽暗的背景深处走向了前台。他开始更加直接讨论遗忘,处理和解,来写克隆以及人性的黑暗未来,甚至是以英国为例介入历史叙述中去,这些都是被一般认为是诺贝尔文学奖最喜欢的命题,甚至与和平奖雷同。这一切都让他变得更可见了。当然,我想作家本身一定有更详细的对于这种变化的解释。但这种变化本身值得关注,因为其中必定包含溢出文学审美的部分,至少需要我们重新调整早年对他的审美习惯,与此同时,它又如此准确地呼应了我们的世界潮流与社会心理在结构上发生的变化,这本身也不是文学能够解答的问题,而只是它抛出的问题罢了。
当然,最想说的对于一个奖项的过分关注甚至陷入赌博,始终是一件错乱的极其不符合文学精神的书,任何对此事投入过度热情的作者与读者,都应该面壁。文学本身应该是一件不断冲突边界、冲击既有认知的事情。这一次很遗憾诺奖没有把一个更崭新的面孔介绍给读者,但幸运的是中文读者很早就有机会认识石黑老师了。

单读出品,转载请至后台询问
无条件欢迎分享转发至朋友圈
欢迎关注单读海外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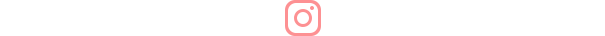
instagram owmagazine

facebook OWmagaz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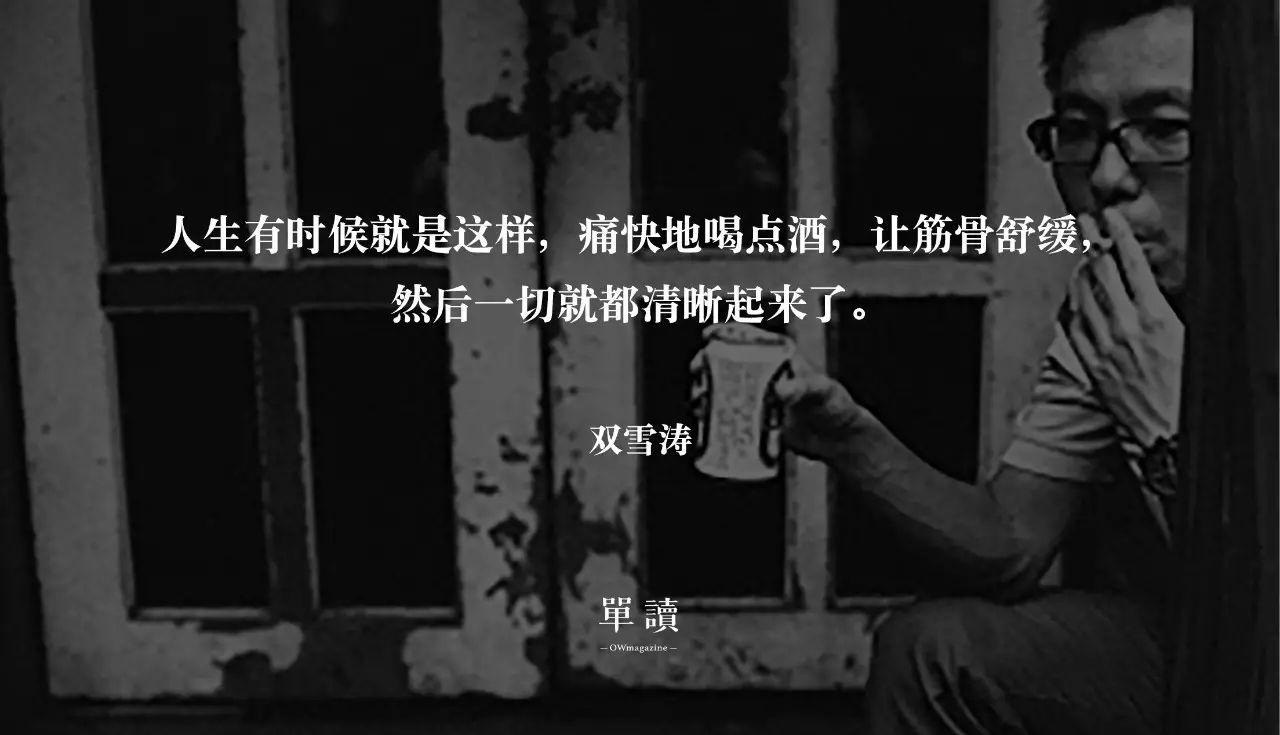
识别图中二维码,购买全新上市的《单读15:我们的黄金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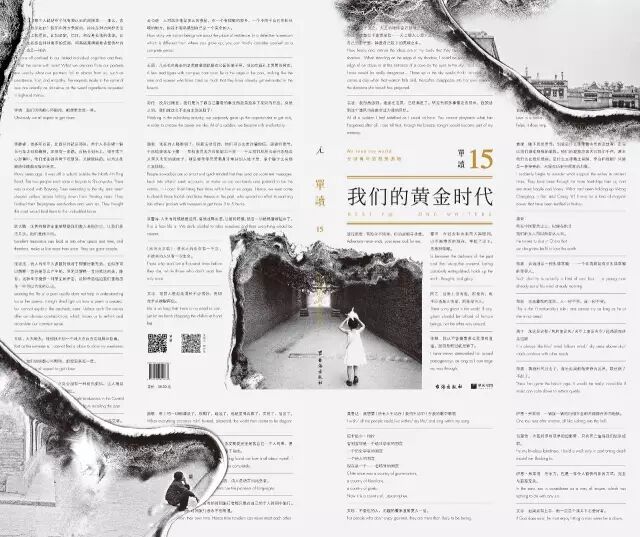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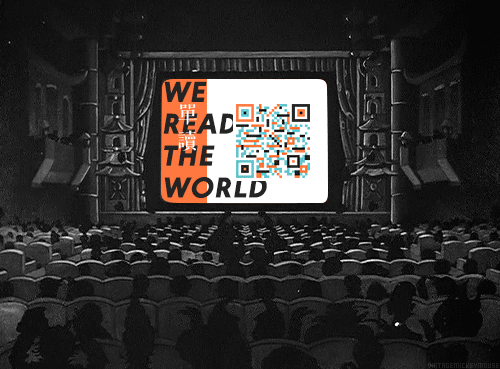
▼▼我发觉我开始留意她的衣服,以及她看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