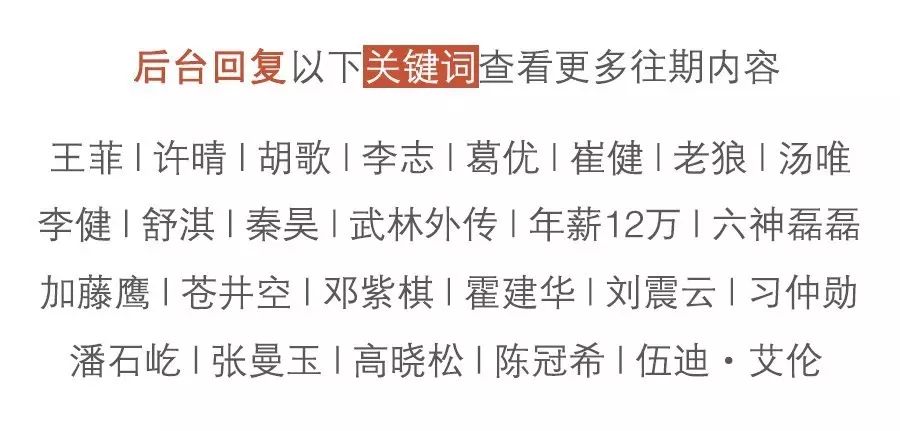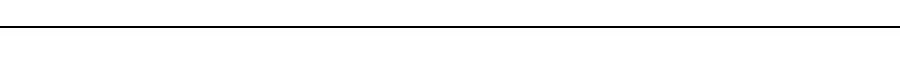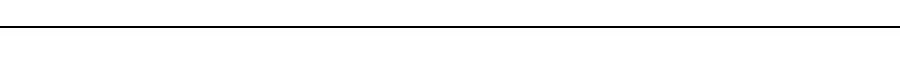2015年接受《博客天下》采访时,有了一定知名度的赵雷说更喜欢早年那种不为人知的状态,那让他感到放松、舒适,不被世界绑架。
文 ✎ 徐雯
赵雷的摩托车比他早出生一年。
白色机身,皮座上全是裂痕,黄色的棉絮飞在外面。这是赵雷在2010年花了1700元买的,骑着它呼啦啦行驶在北京的二环路上,他觉得自由。
这个出生于1986年的歌手挺复古。
他有一台铁质的红色小手风琴,花了六七十块钱在地摊上淘来的。在《赵小雷》和《吉姆餐厅》两张专辑里,只要用到手风琴,他就拿出来,让陈旧但迷醉的音乐元素长到旋律里。

他依然住在鼓楼附近的胡同里。五百多平米的四合院挤了二十多个人,上厕所得往外走一百米,因为潮湿,早上起床经常有蜈蚣趴在地上。赵雷非常享受这种生活:和大家住在一个院子里,在同一个晾衣杆上晾衣服,每天给自己做饭,过得简单纯粹。
“没有人认识我,特别舒服。”这是他所向往的状态,“独处的,淡淡的”。
2003年,17岁的赵雷开始在北京的地下通道唱歌。
此后12年的大多数时间,他都在陌生的人群里出没,酒吧里、街道上。仰着头时,脖子上的青筋常常因激动而毕露;情深处闭上眼,睫毛也跟着情绪微微颤动。
他唱“北方的村庄里住着一个南方的姑娘,她总是喜欢穿着带花的裙子站在路旁”,他唱“青春口袋里的第一支香烟,情窦初开的我,从不敢和你说”,他唱“我没有擦去争吵的橡皮,只有一直画着孤独的笔,那夜空的月夜不再亮,只有个忧郁的孩子在唱,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东南西北地唱,山高路远地唱,在民谣的世界里撕开一道朴素又诗意的口子。
几年前他也上过一些电视节目。
2010年,正好在长沙演出,他抱着玩票的心态参加《快乐男声》,靠着一些自己原创的歌曲站在舞台上和耳熟能详的流行音乐火拼,止步于20强。
2013年,他又接到《中国好歌曲》的邀请。一首《画》深受评委刘欢赏识,被他称为“神来之笔”。赵雷不是很爱炫耀这一点,有人撺掇他再去其他节目露脸,他都觉得自己“不喜欢,上不了”。

▵赵雷参加《中国好歌曲》
以前的赵雷经常在酒吧唱,一两百人的场子最后挤了一千来人,歌迷就这样一点点积攒起来。在电视上露脸之后,他开始逐渐被人认出来,比如在健身房跑步时,比如刚一脚踏出胡同口的老厕所时,比如骑着摩托车拐在北京的老胡同里时。最初,他很不适应这种“出名”,甚至讨厌别人上来问“你是赵雷吗”,现在他觉得不能刻意推拒这份自然的结果,更不能欺骗别人。
也有歌迷找到他的住处,给他送土特产,或者在万圣节装扮一番到院子里吓他,他却淡定地掏出手机:“别动,今天万圣节,我给你照一张。”一些歌迷甚至和他成了朋友,大家一起风轻云淡地聊天。
尽管有一帮忠实的粉丝追随,赵雷也没觉得自己有多出名,更不觉得自己是明星。“不适应那种状态,我如果真觉得自己是明星了,估计就不敢出去了。”
2015年一整年,赵雷都在“收”着唱歌。他谢绝了二十多场商演,这比他今年参加的数量还要多。11月,随着音乐市场的逐渐扩大,赵雷和乐队从Live House搬进了剧场。在越来越多的唱作歌手登上北京工人体育馆、工人体育场的2015年,这不算新闻。
在粉丝群中,有一句话广为流传:“赵雷不红,天理难容。”
他却并不喜欢这种被人捧着的感觉。处在一个被人所知的环境,他觉得逃脱不了别人的描述,比如“你的歌有多好,我多么喜欢你,你的歌怎么改变过我的生活”。
“说心里话,这些我已经听得太多了,我希望别人在不认识我的状态下去认识我。他们知道你是做音乐的,会很刻意地对你,没法自然地接触你。”赵雷喜欢让自我沉浸在不为人所知的快感里,这让他放松、舒适,不被世界绑架。
他甚至给经纪人发自己粘了胡子的照片,说以后要改头换面回到Live House里去唱歌—他企图抛弃名字、面孔以及随之附着的各种标签,回到本真的、只通过音乐来和外界沟通的年代。
“我喜欢别人不认识我。”他说。
“我需要这种陌生的环境去打开自己。总在认识我们的环境里唱歌,有时候就是一场刻意去做的表演”
赵雷有一个美妙的畅想:带上自己的小阵容乐队,装扮一下,去酒吧里唱新歌,不认识的酒吧老板会想“新歌手,我不能给你周六的时间”,也不会说你留下来喝酒;没有歌迷认识你,也不会有人专程买票来听,台下有人喜欢就继续听,不喜欢就转头走,甚至可以砸瓶子发泄;你可以唱10首歌,也可以唱5首,唱开心了为止。
“我需要这种陌生的环境去打开自己。”赵雷说,“演唱会,你需要对此负责,两个小时得把大家喜欢的歌都唱一遍。总在认识我们的环境里唱歌,有时候就是一场刻意去做的表演。”
2012年,赵雷组织过一场不刻意的表演。他和浩子、小猛、冠奇、旭东5个音乐人做了一次“十个轮子上的民谣之路”的全国巡演。他们每人骑着一辆摩托车,从成都出发到上海,又南下深圳,“公里表上写得特别清楚,4500公里”。
“摩托车不是像汽车把你包起来,它跟大自然比较亲近,(你)可以亲身地感受大自然的风,大自然的雨。虽然有时候很冷,也很痛苦,不过你还是会觉得它跟汽车有不同的乐趣。夜里,我们开到山谷里,停在半山腰,下面是悬崖,把摩托车的大灯全部关掉,你就像在一个拉着帘子的屋子里,伸手不见五指。再一开灯,又照出了十公里以外,又看到了前面的风景,下面的山谷、小森林,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叫声,特别不一样。”
有时候骑着犯困,一个小急弯就摔出去了,他爬起来拍着脑门儿:“我怎么睡着了呢?”
要不就是行驶在漆黑的隧道里,和同伴的车一滑,倒在一块儿,赶紧爬起来和后面的汽车招手示意。要知道,那个隧道因为这样的事故死过三十几个人,好在他们“最后只丢了两瓶矿泉水”。
当然,也有一些温馨的时刻。
比如到了乡间的小村落,当地的乡民就问:“你们从哪儿来啊?”
“从北京过来。”
“啊,北京人就长这样啊。”
“……”
“你们为什么要走这么远啊?”
“因为喜欢骑行的感觉。”
路上几个大老爷儿们吃饭,点了六菜一汤,经常一抢而空。吃完一大盆米饭还不够,甩手就是:“再来一盆!”
“感觉特别爽!”赵雷说。
他太迷恋这种在路上青春飞扬的感觉了。
2006年,青藏铁路刚刚开通,20岁的赵雷就攥着借来的700块钱,一路青春呼啸着从北京赶到拉萨。他的朋友、民谣歌手、主持人大冰用“无闲事挂心头,故而日日都算是好时节”来描述那时候的光景。
“特别自由。那时候住在仙足岛那儿的民居别墅里,冬天,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光着屁股在院子里晒太阳,没钱了就去朋友那儿蹭吃蹭喝。大家都穷,有一个《拉萨日报》的记者,我们都靠他,交了房租还剩两三百,每天把钱给我分配。比如20块钱的话,4块钱坐车,2块钱买萝卜西红柿,还留点钱买泡面。有一次实在没钱了,就买一大堆土豆,拿回家全煮熟了然后蘸盐吃。仙足岛那儿还有一片纯沙子的沙滩,好多人就一块儿在沙子上踢球。”赵雷说。
他在酒吧里、马路上唱歌,大晚上去吃回族人烤的羊蹄,吃完黏糊糊的,就用西藏的咸茶去涮手。
大冰称那时候的赵雷是拉萨的街头明星。“每天他一开唱,成堆的阿佳(对跟自己年龄相仿的藏族女性的尊称)和普木(小女孩)脸蛋红扑扑地冲上来围绕着他听。他脾气倔,刺猬一只,只肯唱自己想唱的歌,谁点歌都不好使。”大冰在书里回忆。
后来赵雷去了丽江。
彼时,那里还没有被商业和游客占领。纳西族的民居卧躺于玉龙雪山脚下,阳光丰沛,鲜花葱郁。丽江有火塘酒吧,屋子中间的坑里点着柴火,人们就在噼里啪啦的火光里倾诉衷肠。“那时我们没日没夜地唱,那时我们醉倒在石桥上。”赵雷在歌里唱,“一路昂头的青春,数不尽夜的星辰……”
那段时间,一些知名导演和演员经常去听赵雷唱歌。喝了丽江的梅子酒,再一听到赵雷的歌声,经常悲喜交加。“临走的时候,他们还要给我钱,因为我经常还没怎么唱,他们就哭了。”

时隔多年,赵雷还是会想起当时的场景以及那种自在、独立、纯粹的状态。他经常梦到自己站在丽江古城的院子里,醒来会问自己:怎么就回来了,应该在那儿待着啊。后来带着父亲去丽江,却忍不住感叹物是人非了。9月23日,赵雷在微博上公布了自己的新歌《再也不会去丽江》。“音乐响起,有些东西就会断。”他说。
如同一场告别。
赵雷说,他想回到一个纯粹的环境中去做音乐,做一个思想干净的人。
2011年,赵雷发行了个人第一张唱片《赵小雷》。十首歌,十个故事,有买不起车房的穷小子,有在远方的姐姐和天堂的妈妈,有在理想和现实面前倍感无奈的青年。
在同名歌曲《赵小雷》里,他唱道:“赵小雷他是个什么东西/你知不知道他们都在背后说道你/你还是那样仰着脸叼着烟/一身的流气没人爱理会你……”
做这张唱片的时候,赵雷借了60万元钱,20万做唱片,其余的买设备,在胡同里开了个15平方米的小工作室。那时候他没有生活保障,身体上孤独、精神上孤独,感觉各种坏的事情都赶在身上了,“咬着牙往前走,可是心里还是觉得特别难受”。
但赵雷狠了心要做一张自己的唱片。“必须要让别人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要做什么样的音乐。”
出唱片前得先编曲。赵雷是一个龙头,不完成这个环节,别人没法出谱子,下次没法排练。他就一个人在小屋里扛,觉得特别孤独。“谁能帮帮我啊?不是没有人帮我,而是没有人能说到我心里去、能帮得上我。”陷在旋律里,麻木得没辙了,他就找朋友来听,画画的、摄影师,甚至邻居,谁都行。
“专业的人跟你讲的就是钱,你要给钱我才帮你听。这是一个金钱社会,前提是钱。因为别人付出了,理所应当的,这个也都能理解,但我没有那么多钱,只能凭感觉去做第一张唱片。所以我一直惦记着那些帮助过我的人。”
“特别孤独,把音乐做成的过程。这两年好多了,很多人愿意帮你,因为他们知道你的作品,你的方向。”
这几年,不仅是赵雷,所有的中国民谣歌手似乎都迎来了一个饱满鲜活的市场。年轻人们愿意从一个音乐节迁徙到另一个音乐节,也愿意花几百块钱去给一名喜欢的民谣歌手捧场。曾经一度被贴上“小众”标签的创作音乐人终于要同市场赤膊相见。
“民谣是最接近流行乐的风格,它能融入大众市场,是正常的。但民谣也不是一把吉他,一个简单的编曲,从曲调到曲风都有很多的讲究。
“我所理解的民谣精神,首先就是,它来源于你的生活,细节都能被唱进去。比如前两天我写了个歌词:‘从商店出来的时候就一直看着你,直到你走过了绿灯,直到我望不到你,好像你就和我住在一个巷子里,我们只是隔着几个门牌号而已。’就像这样,没有很夸张的东西,或许就是民谣。其实我不是一个音乐底蕴多么深厚的人,我只是肤浅地认为,民谣是这样的。至于我一直在做的东西是什么,我不希望被限定,我觉得好听就行。”

2014年,在发行自己的第二张专辑《吉姆餐厅》之后,赵雷开始自我反思,觉得应该要做点不同的东西了,“你不能总是孤独,总是无助,总是天天和你的爱人吵架,你的生活总是窘迫,不能总这样,我需要一些新的生活”。
这几乎是民谣或者摇滚歌手在摸爬滚打很多年之后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
近些年,赵雷最推崇的歌手许巍也从早期的苦闷和孤独走向了豁然与温暖,有人指责这种和解是妥协,但赵雷认为许巍现在很难写出波动性那么强烈的歌是非常对的:“他现在就是这样的状态,把幸福感表达出来,并没有说我继续孤独或者怎么样。”
之后赵雷去了一趟美国,去听那里的音乐人歌唱,去看那里的人在怎样生活。他一直想要找到最自然最舒适的状态。
“郑智化有一句歌词,叫只有远离人群才能找到你自己,一点都没错。”赵雷说,“我现在特别特别幸福,会有一些小插曲,但没有把整个大局破坏。”
最近几年,他打算把这种自由、随意的状态维持下去,不把名利当真,“玩玩还行”。他说以后或许会有更现实的活法,那现在就把该做的都做了,如果未来老天有缘分赐给他一些名利的东西,他也不会拒绝,但坚决不会为了名利去争争斗斗。
文 ✎ 徐雯
图 ❏ 尹夕远
▼小号
五年前购于二手市场,赵雷叫它“老古董”,买完后,赵雷兴奋地在家吹了两天。“吹得特难听,驴叫一样,腮帮子特疼。”

▼便携式音箱
赵雷每天晚上睡觉前都用它来听钢琴曲助眠,去外地参加音乐节,也会随身带着。

▼节拍器
朋友从英国带回来的礼物,它是赵雷最常用的练琴工具。

▼专辑
赵雷一共发行了两张专辑,2011年的《赵小雷》和2014年的《吉姆餐厅》。做《赵小雷》时,他借了60万在胡同里开了个15平米的小工作室。
那时候的赵雷没有生活保障,身体孤独、精神孤独,觉得各种坏的事情都赶在自己身上,但总算还憋着一股子劲儿,“必须要让别人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要做什么样的音乐。”

▼纯金刺猬挂件
赵雷觉得自己像只刺猬,这后来也成为歌迷眼里,他的形象标志,“能够相互温暖但彼此无法妥协”。

▼墨镜
赵雷拥有的墨镜里使用率最高的一副,被摔过一次,镜片碎了,赵雷又花钱请人修好。他说自己有旧物情结,一个袋子也会留很久。

▼帽子
赵雷有很多顶帽子,但唯独这一个,戴了三年多。“就在一个打折店买的,我特别喜欢,可能更适合我的脑型。”

▼钥匙
赵雷在过去的六七年里换过很多扇的门、很多把的锁,但钥匙链始终没换过,于是这把钥匙链上拴了一大串“无用”的钥匙。

▼长颈鹿
在胡同里捡的。采访当天,赵雷在家里翻找各种有意思的、有意义的物品,突然间,他意识到,这个自己从没在意过这个小玩意,已经默默跟在身边很多年,“无论桌子怎么换,乐器、设备怎么换,它始终在。”

▼运动鞋
赵雷喜欢跑步,这双鞋陪他跑了很多个“十公里”。“它带动着我的脚,和路是最亲密的关系。”天气好时,他会从雍和宫跑到天安门,再从天安门跑回鼓楼附近的家。

▼拳击手套
拳击是赵雷一大爱好,他在香港买了这副手套,上面还沾过之前对手的血迹。“这么多年做音乐,生活比较单调,所以想刺激一下已经沉静的神经。”赵雷现在依然频繁地练拳,几乎每天要打一个半小时。

▼手风琴
又一件从旧货市场淘来的“老古董”。赵雷原本以为手风琴差不多都得好几百,但这个琴只花了他66块,琴的声音出现在了《吉姆餐厅》和《小屋》里。“可能有一些音会不准,但我比较喜欢它的那种醇厚音色。”

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