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征订正在进行,恭请读者朋友到当地邮局订阅。
邮发代号1-201
张磊夫教授 (1936-),原名勒夫·德·克里斯匹格尼(Rafe de Crespigny),是当代澳大利亚史学界研究中国东汉及魏晋史的先驱。他以年鉴学派的方法解析了东汉末年的社会“结构”(笔者按,年鉴学派的方法在此意指20世纪中叶法国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的史学研究方法。作为结构主义史学(Structural History)的分支,年鉴学派认为人类的行为是被人类所生活的自然及社会环境所界定的。基于此前提,年鉴学派的方法论将政治、地理、经济等环境因素定义为“结构”(Structure)或“结构因素”(Structural Factor)。他们通过分析这些“结构”或“结构因素”去理解历史事件。),包括地理、人口与经济。基于此,张磊夫教授将三国时代看作“结构”的产物,从而进行了独到的研究。
张磊夫现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终身讲座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园行馆荣誉成员。他著作等身,代表作包括:《北方边境:东汉的政与策》(1984)(Northern Frontier: The Policies and Strategy of the Later Han Empire)、《南方的将军》(1990)(Generals ofthe South)、《东汉与三国人物志:前23年到220年》(2007)(A Bibl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Later Han to the Three Kingdoms23BC-220AD)、《国之枭雄:曹操传》(2010)(Imperial Warlord: A Biography of Cao Cao)、《洛阳大火:一部东汉史 前23年到220年》(2017)(Fire overLuoyang: A History of the Later Han Dynasty 23BC-220AD)。其中,《国之枭雄》已与中国读者见面。
笔者负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期间,分别于2019年9月和10月拜访张磊夫教授,受《中华读书报》委托对他进行专访,以就教于各方学友。
张磊夫
徐缅
(以下简称“徐”):张磊夫教授您好!能够受《中华读书报》委托采访您是我的荣幸。您的著作《国之枭雄:曹操传》在中国有大量的忠实读者,他们非常期待此次采访,也非常期待您的另一著作——《南方的将军》中文版的早日问世。您的读者们对您的学术经历很感兴趣。请问您从何时开始决定研究三国史?这一决定背后有什么非凡的故事吗?
张磊夫
(以下简称“张”):没什么非凡的故事。我早年在剑桥大学攻读了一个三年制历史学位,主攻欧洲史及英国史。毕业后回到澳大利亚。当时,我高中的拉丁文老师刚刚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前身堪培拉大学院担任教授。我写信给他,说我对年轻的堪培拉市很感兴趣,也想继续深造。他觉得我已无需多学拉丁文,并推荐我申请学院的汉语奖学金。与此同时,战后的联邦政府刚刚开始对亚洲萌生兴趣。澳大利亚一向更重视与欧洲和英联邦的纽带,但对日战争的胜利让政府认识到学习中文兴许于国家有所助益。我申请的奖学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设立的。于是,我开始师从一位很好的学者,汉斯·别伦施坦因(Hans Bielenstein)(笔者按,汉斯·别伦施坦因(Hans Bielenstein)是《汉代官僚制度》(The Bureaucracy of Han Times)一书的作者)。别伦施坦因先生后来去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他是一位研究光武中兴的专家且极具影响力。在他门下我阅读了《三国演义》并爱上了这本书。这是一段有趣的求学经历。我最终掌握了阅读古代史料的汉语的能力,它使我能够探索那一段历史。
徐
:那么,您为何选择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留校任教呢?
张
:为了感念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奖学金。还有,澳国立在我留校时方兴未艾。它是所年轻的大学并在很多方面令人兴奋。堪培拉虽是座小城,却是联邦政府的心脏。我当时认为留在堪培拉比返回我故乡阿德莱德和去往大都市墨尔本更有趣。因为一切是新的,到处是新的机遇。
徐
:请问您认为自己是一位历史学家还是一位汉学家?您认为这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张
:我是历史学家,不是汉学家。在剑桥,我被训练为一个英国史及欧洲史方面的专家。我接受的是纯粹的历史学训练。可以说,我是一个碰巧懂得中文的西方历史学家。汉学是一门专注于个别对象的学问。比如对中国诗歌、散文和文化现象的研究。与之相反,我的史学研究倾向于将一个时代总结为一段系统的历史,而非许多个别的现象。当然,汉学是一门有价值的、合理的学问。但我个人认为汉学过于碎片化。例如,许多汉学家对曹操有自己的看法,但没有一个汉学家写过一本曹操的传记。相比之下,研究欧洲史时,历史学家们的敲门砖往往就是人物传记。因为西方历史学家总是把一个时代看作一个完整的体系而非许多个别的现象。而这正是西方汉学缺乏的。
徐
:的确。在阅读了您的《洛阳大火》后,我发现您对三国时代有极其系统的看法。这集中体现于您对东汉地理、人口及经济等“结构”的关注。由此我认为您的研究方法论属于结构主义史学的年鉴学派分支。对于我的看法,您是否赞同?
张
:我认为你是对的。实际上,学界常批评我过于结构主义,我觉得这很中肯。例如,在写作《洛阳大火》时,我根据东汉皇帝的继位顺序安排章节,这是个很年鉴学派的方式。我选择这一方式有我的道理。因为每一位皇帝的统治都伴随着不同的危机,如皇位继承、外戚专权等。每种危机都产生于不同的“结构”,不同的“结构”标志着不同的时代。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不断重复的危机,如财政短缺、北方边患等。它们反映了不断延续的“结构”。总而言之,我确实是个结构主义者。在中国读者眼中,我可能显得特别结构主义。
徐
:如果年鉴学派的方法论是您的方法,您为何选择它?它为何适合于研究三国时代的历史?
张
:记得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吴国的。当时我发现人们都在谈论魏国和蜀国,对吴国的深入研究是缺席的。当我开始研究吴国史后,一些大问题显现了出来:为什么吴国会诞生?为什么东汉会分裂为三个国家?为了回答它们,我的论文起初有些尴尬。它用一整章讨论了南中国起源于史前时代的历史背景,我为此甚至寻求了人类学家的帮助。这被一位史学界的朋友诟病为画蛇添足。然而,基于这一章,我提出了一个子问题,为什么南中国得以发展?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又回到了大问题上,为什么汉朝会分裂?为什么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会陷入混乱并分裂为三个国家?这么一来,我意识到,要想研究吴国的诞生,研究汉朝的社会结构及其缺陷是必须的。我发现吴国得以发展是因为大量人口的南迁,这让南方有足够的人口抵抗北方的政权。如我在《洛阳大火》中所述,光武中兴时北方政府尚且能够轻松地征收南方的赋税。然而,在曹操的时代,曹操却做不到。这里的原因恰恰在于人口这一结构因素的此消彼长。在我写作《南方的将军》时,我其实又回到了我博士论文的主要问题上。因而,我的中心论点认为,若要吴国诞生,汉朝必须崩溃,而汉朝的崩溃在根本上是其“结构”的崩溃。
徐
:诸葛孔明曾将中国历史的常态概括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观点在以一种循环史观看待中国历史:中国的历史进程是一个从大一统到分裂,再从分裂回到大一统的循环过程。这一观点在中国史学界有深远的影响并促使中国人以循环史观看待自己的历史。那么,在您研究中国历史时,您采纳的是一种循环史观还是与之相反的线性史观?
张
:线性史观。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国从分裂走向秦汉时代400年的大一统。之后,汉朝衰亡,中国走向魏晋南北朝400年的分裂。这似乎符合了上述的循环史观。然而,从宋朝开始,宋被元继承,元被明继承,明又被清继承。这些王朝之间没有显著且持久的分裂时代。1911年到1949年的中国虽然也是分裂的,但这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实在是沧海一粟。诸葛的观点在当时的确有先见之明。但是,我不认为中国史是这样的。
徐
:在《洛阳大火》和《国之枭雄》中,您总是将三国时代和欧洲史中相似的事件进行比较。比如,您将汉灵帝和路易十五治下的卖官鬻爵进行比较。由此,您认为比较历史学是否适合研究三国史?
张
:首先,我们都是人类。我们通常对相似的问题采取相似的对策。以中国长城为例,它本质上是一条前沿防线。通过研究罗马人在不列颠和日耳曼的长城,我们能加深对中国长城的认识。我们能认识到长城不是一座简单的墙,而是一条“警戒线”。游牧民族能够在马背上快速移动。但中国和罗马的军队以步兵为主。对中国人和罗马人来说,要防范的是游牧民族快速的入侵和快速的撤退。长城的存在意味着农业民族的守军可以快速向后方报告游牧入侵者的数量,从而使后方快速召集精兵。如果游牧入侵者被精兵打败,他们将很难撤回长城以外。因为长城以内在此时会成为屠杀游牧民族的猎场。只要长城被妥善维护,游牧民族将不敢入侵。所以,我想说的是,中国和罗马对相似的北部威胁采取了相似的回应方式。他们在发明这种回应方式时并无沟通。
然而,比较三国史和欧洲史也有些许困难之处。比如,三国时代的社会组织能力比后世的欧洲强大很多。在1415年英法大战中的阿金库特,英国军队只有5000人,法国军队只有15000 到20000人。如果曹操和刘备看到阿金库特,他们会觉得这是个笑话。因为他们的军队都至少有十万之众。还有,欧洲的地理比中国要分裂得多,欧洲和中国的军事科技差距也很大。罗马人只有短剑标枪,阿金库特的英国人还在用长弓。但三国时代的中国已经有弩机了。这些都是比较历史学会遇到的困难。
徐
:在中国,我们有枭雄、奸雄和英雄的概念。枭雄意味着猫头鹰一般的,借强者之力达到目的的人物。奸雄意味着富于智谋但缺乏道德的人物。英雄意味着通过勇气和能力赢得荣耀的人物。中国人认为刘备是枭雄,曹操是奸雄,孙权是英雄。您在多大程度上同意这一看法?
张
:我不同意。我认为孙权是中国军阀里的特例。因为他不是一个成功的将领,他从未靠自己的勇气和能力赢得一场战争。他向来依赖将领。他的父亲,孙坚,是个真正的勇士。他的兄长,孙策,是江南地区伟大的征服者。要推英雄,我认为孙策才是真英雄。很遗憾他25岁英年早逝。当然,孙权的长处在于治国理政,这也是杰出的成就。总之,我不认为孙权是英雄。至于曹操,我认为他兼具了枭雄、奸雄和英雄的优点。尽管我这么看可能有些偏颇。曹操能上阵杀敌,这在他所属的阶层中很少见。比如,袁绍从未上阵杀敌。曹操是个有勇有谋的人,也懂得治国理政。魏国在实际上取代了汉帝国的政治结构,并且运作了起来。曹操的确很狡诈,但他决不只是个狡诈的奸雄。至于刘备,他显然很有领袖魅力。他能够让人们追随并效忠于他。但是你永远不能够相信他。吕布、曹操和刘璋都曾犯下相信刘备的错误。刘备才是真正的奸雄。还有一个能算作真英雄的人物是关羽。他是中国的战神。但因为傲慢,他在荆州败给了吕蒙。然而,我认为关羽是个虚构的人物,因为他太理想主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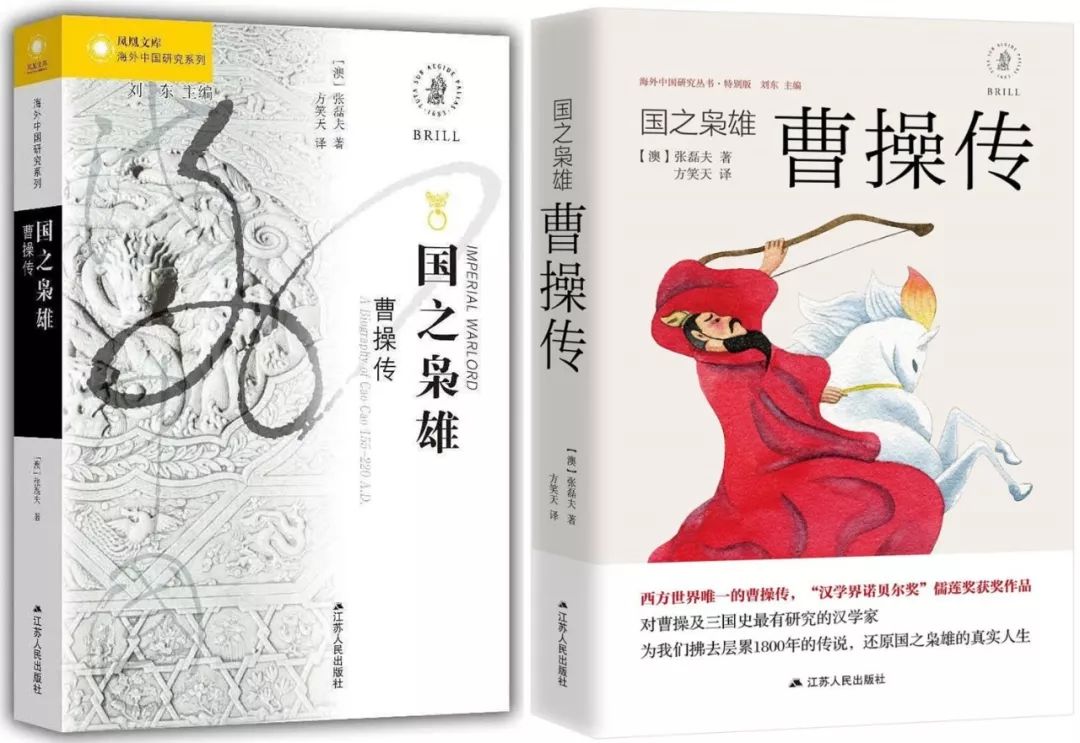
《国之枭雄:
曹操传》书影,平装本(左)和特别版(右)
徐
:结合您在《国之枭雄》中的观点,您认为刘备背信弃义,对他不太欣赏。然而,中国人长期以来认为刘备是一个富于美德的领袖。那么,您认为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认为?为什么背信弃义的刘备能被认作汉室正统的保护者?
张
:首先,刘备绝不是一位富于美德的领袖。他总是声称他很忠诚,但他却背叛了自己的堂兄刘璋。他也声称自己忠于汉室。但曹操仅仅称自己为魏王,而刘备封自己为大汉天子。其实,在他自封天子的时候汉献帝还在位,大汉帝国也没有终结。刘备被认为是汉室正统的保护者是始于南宋。南宋失去了中国的核心地带,他们需要证明自己是中国合法的统治者。相似地,刘备偏居的四川也不是中国的核心地带。刘备自称天子的故事成了南宋的好借口,因为这个故事让南宋政权显得合法。
徐
:您对西方学界对三国史的研究现状怎么看?您如何评价它的优劣及发展趋势?
张
:我认为,令人尴尬的是,除了我对东汉的研究,西方对3世纪的中国没有任何好的研究。我发现到目前为止,西方没有关于魏晋的、完整的史学研究。大多数研究都是关于文学和哲学的碎片化研究。西方也没有对当时中国的文化和社会风貌作透彻讨论。我认为我们很需要完整的三国史。我不会去做这件事,关于魏国和吴国我已经尽我全力。但完整三国史的缺席确是很大的缺憾。西方对南北朝的研究也有问题。我们已有南北朝通史。比如,哈佛出版的陆威仪(Mark Edward Louis)的《分裂的帝国:南北朝》(China Between Empires)。这是本好书,但过于大而化之,它试图用一本书探讨南北朝400年的历史。西方也有一些对洛阳城和南朝政治结构的研究,但它们都太碎片化。魏晋南北朝对生活其中的中国人来说是一段艰难的时期,对于研究它的西方人来说也一样艰难。当然,西方学界对汉唐明清四朝的研究还是令人满意的。总之,我们还有许多要做的。
徐
:基于上述现状,您对西方学界针对三国史的研究方法如何看待?有哪些不足和困难?
张
:中国有许多关于三国的史料,但它们在西方从未被翻译,甚至从未被阅读。在我看来,任何一个想研究中国的西方人都需要了解相关的中文资料,但这很难。我读硕士的时候翻译了《资治通鉴》中从黄巾之乱到汉朝灭亡的部分。但是,我每天只能翻译两页。这意味着,只要我想使用任何汉语资料,我需要费力地阅读甚至翻译全文。很可能,我是英语世界里唯一一个读过《后汉书》全文两遍的人。一边看正文,一边看注释。我仍然觉得这是件有趣的事,但阅读中国史料对于西方人确实很困难。
徐
: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研究三国史对于当代西方社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启示?
张
:辉格文学(Whig Literature)里有句名言,“当众神想摧毁一个人,他们会先让他疯狂。(Whom the gods wish to destroy, they first make him mad.)” 我们时常感觉,这个世界很疯狂。在汉朝,宦官在政治结构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尽管他们没有实权且只是大人物的附庸。在现代西方,政治惊人地相似。在澳洲国会,领袖们总是被许多没有实权的傀儡政客狂热追随,政党好像黑帮一般运行。可以说,澳洲所有的政党里都有这种趋势。还有,如果动荡的三国时代对澳洲外交有什么忠告,那就是:永远不要相信你的盟友们。
徐
:感谢您参与此次采访,您从西方史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了我们中国人都熟知的三国史,真可谓“西洋镜里鉴三国”。作为历史学家,您关于历史和现实的远见卓识令人钦佩。
张
:谢谢,我非常享受这次采访。
▶
2019年10月17日下午,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园行馆(University House of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作者单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历史系)
本文为中华读书报原创作品,如需转载请留言。欢迎转发到您的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