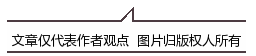北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天下士子云集汴京。他们到此不是为了一尝“开封菜”的滋味,而是为了博取鱼跃龙门的良机——通过礼部进士科考试而成为天子眼前的“菜”。
这场风云际会的考试,注定是北宋政坛和文坛上一次彪炳千秋的盛会!因为考官是欧阳修、梅尧臣......考生有苏轼、苏洵、曾巩、章敦......文坛新老巨匠、政坛前后宰辅“群英荟萃”。

此次科考的试题也颇为独特——竟然是一道有关“法学”命题的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该题出自《尚书·大禹谟》伪孔安国的注文:“刑疑付轻,赏疑从众,忠厚之至”。北宋朝廷开科取士能以此为题,也可见当朝统治者的重法之意!
时年21岁的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便在此次应试中高中榜眼,一举成为北宋政界、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苏轼这篇命题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一经出世,便伴生了许多让人津津乐道的文坛佳话。
如主考欧阳修误以为此文是其弟子曾巩所作,为避嫌将其降为第二名,却“误伤”了本该是状元的苏轼;又如苏轼在文中杜撰尧与皋陶商议刑罚的典故,却向欧阳修解释是出自《三国志.孔融传》中的“想当然耳”;还有欧阳修那句“点赞”到极致的评卷感言——“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或许是由于幕后“花絮”颇多,反倒让人忽略了文章本身。 本文虽是苏轼临场应试而作,却不失为论证赏罚宽严之道的上佳之作,从中亦可窥见苏轼青年时代的“法学思想”。
此文之大意有三:
一是论证为何应当“赏疑从与,罚疑从去”。
上古圣君以忠厚德行对待百姓,赏善并“歌咏嗟叹”、勉励良善之人善始善终,罚恶但同情劝解、帮助作恶之人弃恶自新。
在尧当政时,执法官皋陶准备处决一个犯人,皋陶三次言杀、尧却接连三次赦免,所以天下人畏惧皋陶执法的坚决而喜爱尧用刑的宽大。
四方诸侯建议“鲧可用”,尧原本认为鲧违抗命令、残害族人而不可用,后来又应允“试之”。为何尧不同意皋陶杀人的主张,却应允诸侯用鲧的建议呢?
因为《尚书》中有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可赏可不赏而赏之,只是过于仁慈,但不失为君子!可罚可不罚而罚之,却是有违道义,已成残忍之人!故仁慈可以不过份拘泥于边界,而道义的底线丝毫不容跨越。
二是阐述如何“赏罚”才为“忠厚之至”。
“古赏者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因为,赏以爵禄、刑之刀锯的范围,都非常有限。天下善行不可能逐一赏赐,爵禄也不足以用来劝勉所有人向善;天下恶行也不可能一一惩罚,刀锯也不足以惩罚所有作恶之人。
故此,赏罚有疑时,按照“仁”的宗旨去处置,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效仿君子长者之道,这便是忠厚到了极点。
三是指明实现“忠厚”之道的基本法则。
君子制止祸乱其实别无他法,也不过是控制个人喜怒,使其不失仁厚罢了。《春秋》的大义原则也是立法贵在严厉而处罚贵在从宽,按照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这也是忠厚到了极点。
此文区区六百余字,却饱含着极其深奥的“法哲学”思想,诸如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法的惩罚与教育作用、法本身的功能限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等现代法学理念都可从中看到思想的“火花”,其文采、内涵均可视之为古代“法学论文”的经典之作。

然而,此时年仅21岁的苏轼,毕竟还只是一位满怀激情、求取功名的热血青年,与那位历尽世事沧桑、宦海沉浮的“东坡居士”还相距甚远。
《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虽有法的思维,但仍旧以“仁”为核心。文中所指封建统治者“刑赏忠厚之至”的实践标准也始终以“仁”为标杆,这恐怕与柏拉图所期望的“哲学王”并无多大差距。这篇过于理想化的雄文,难以成为经世致用的良策,苏轼终其一生也未将文中的理想化为现实。
笔者自问各项才能均无法望东坡先生之项背,但对此文有关“法学思想”之不足略有所感,斗胆言之!其弊有三:
苏轼主张“慎罚”而“厚赏”便是仁德,孰不知“赏罚”本是一体。公权力执“赏罚”二柄,对于社会成员任何一方的权利义务授予与剥夺,都会影响到彼此对应的利益格局和社会关系。
在实现分配正义时,整体资源的“蛋糕”有限,于此处多予一块,于彼处则少得一块.
在实现矫正正义时,既有利益状态必须调整,于此处宽纵一分,于彼处则受损一分。
“赏罚”宛如一个硬币的两面,“赏东”可能等于“罚西”,而“罚南”也可能等于“赏北”。
“赏与罚”均是双刃之剑,个中权衡之道并不是“赏疑从与、罚疑从去”这一句话所能涵盖。更何况苏轼也在文中指出,“刑赏”之功本就不能及于世间一切善恶,再执行有失偏颇的“慎罚厚赏”之策,岂能解决芸芸众生中千奇百怪的世事纷争!
特别是在当今之世,社会联系日趋紧密,社会冲突错综复杂,更不能依赖单纯的“慎罚厚赏”之法来化解社会问题。诸如当前许多备受关注的刑事案件以及背后隐含的社会问题,也不是片面地“慎罚厚赏”便能解决。

此文两个典故不仅在真实性上有问题,在证明力上也不足以佐证其论点,反倒证明了尧之“赏罚”乃一断于情、而非一断于法!
1.陶(素来贤名、身边之神兽一直被视为公正的图腾)三次言杀之人、必有其罪,而尧三次言赦的缘由却不得而之。
如尧对判定此人死罪有疑问,何不言明何疑之有、让皋陶去查明事实再依法而定?
如果事实不清不应处死、皋陶还三次言杀,便是皋陶滥杀罪不当死之人,后人只会觉得皋陶残暴、又怎会赞扬皋陶的严明?
如果罪证确凿且其罪当诛、执法官还一再坚持,便是尧放纵该当死罪之人,后人只会认为尧枉法、又岂能推崇尧的仁德?
苏轼说此事最终让“天下人畏惧皋陶执法的坚决而喜爱尧用刑的宽大”,这其中的矛盾实在让人费解!至少,我们弄不清楚文中的“罚疑从去”,其“疑”究竟是疑于事、是疑于情、还是疑于法?
2.鲧(到舜当政时系遭放逐的“四凶”之一)曾有违抗命令、残害族人的过错,四方诸侯向尧举荐了鲧,而尧明知鲧是“带病提拔”,仍答应“试之”,尧确有“赏疑从与”的胸襟。
但其赏是碍于四方诸侯的“情面”,还是看重鲧的某些优点?
尧让曾有过错的鲧感受到了仁德,但是否会让奉公守法却不能被“试以重任”的其他部众感到不公?
自古文人都以吏治为国家治理之本,此举似乎不仅难以褒扬,反而还有滥施仁德之嫌。
因此,尧之行事重情而乱法,或偶有贤明之举,终难免个人的意识局限甚至恣意妄为,不能成为万世效仿之楷模。
苏轼认为“君子制止祸乱其实别无他法,也不过是控制个人喜怒,使其不失仁厚罢了”,但控制个人喜怒,在具体案件中公正赏罚,说来容易做来难!人之喜怒本就无常,案件情况千差万别,赏罚尺度也难以平衡。 故尔,公平公正的社会不能仅靠“哲学王”的道德自律来营造,还是需要靠制度设计、靠法治构建作为基础。
笔者在此依旧联想到最近的一些热点案件,记得我国有位知名刑法学家曾提出一个刑法学“专业槽”的概念,
笔者深为赞同,刑法学乃至一切法律学科、甚至所有司法案件都有一个“专业槽”,都不是任何人都可随意过来“啄把米”的。司法需要监督,司法也需要尊重、需要信任,这应成为全社会朝法治目标迈进的基本共识。因为,尊重和信任司法,也是在尊重和信任法律,更是尊重和信任我们共同生活的“最高契约”。
司法也不是苏轼所言“立法贵在严厉而处罚贵在从宽”这样简单。司法从来都不会过于“理想主义”,办案要严格依法、伸张正义,但不期望每一起案件都人人点赞、彪炳史册!司法更不会崇尚“浪漫主义”,办案要勇于担当、造福社会,但不奢望通过审理某一起案件便能解决所有相关的社会问题!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便是法律人对“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最佳注解!

北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黄州,他在《答李之仪书》中曾说自己年轻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因科考而作了些“妄论厉害,搀说得失”的文章。以苏轼之风骨,此言应是真心表达其反思应试之作的意愿。仅此自省之心,便是无数文坛大师所不能企及!
北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从海南遇赦北返的苏轼写下了“总结人生”的千古名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在这个让他更真切地感受到“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时候,不再“老夫聊发少年狂”的东坡居士,不知将会如何评鉴当年“赏疑从与、罚疑从去”的“法学思想”?心中又会萌生何种境界更高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呢?
(立足司法实务,关注焦点难点,客观理性思索,共享法律人生。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法术仁心”公众号)

转载声明:本文转载自「法术仁心」,搜索「法术仁心」即可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