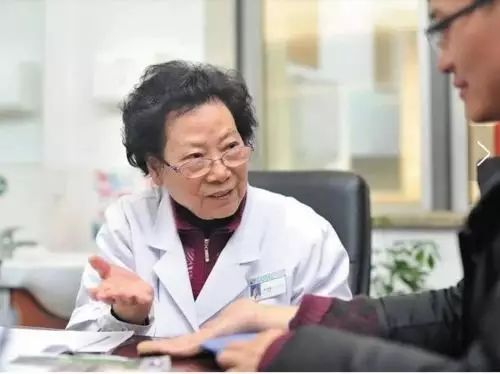2020年的6部华语电影,以及一点感想
文|梅雪风
作者简介:男性。资深媒体人,数码产品发烧友,长跑及太极爱好者。曾任《看电影·午夜场》创刊主编。
似乎是和贯穿全年的疫情适应,整个2020年度的华语院线电影也乏善可陈。
《一秒钟》应该是2020年最有历史厚度的一部电影,当然这是相对于2020的院线电影而言,在张艺谋自己的作品序列里,它就显得单薄了。
在电影形态上,它与张艺谋之前的《归来》有着某种程度的呼应关系。
《归来》讲的是丧失记忆,而《一秒钟》讲的是要记住,哪怕只有一秒钟。
《归来》的底子里是极其冷酷的,它不只是讲的是WG中人人相残的惨剧,更讲了这种惨剧并不一定会因为WG的结束而结束。
《一秒钟》的骨子里却是温柔的,这种温柔在于,在那个连父子都要划清界限的冷酷时代中,两个陌生人却互相为了对方牺牲了自己的利益。
对于劳改犯来说,为小女孩出人头地,同时将胶片交给小女孩,意味着他要冒着胶片被女孩偷走,看不到他女儿出现的那一秒钟电影的风险。
对于小女孩来说,她还回了那盘胶片,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她和弟弟仍将受到那群小流氓的长久欺辱。
劳改犯父亲为了看到在电影前播放的新闻简报中女儿的身影,煞费苦心
但也正是在这部分,
影片缺失了它最重要的东西,也就是人性里的善和自私的对决。
那种自私越显得名正言顺,无可指责,那种善良也才会百转千回,惊心动魄。
只有当这种两难选择被推到极致的时候,人内心的丰富和温柔,才能够得以最有力和最可信的方式展开。
从这个角度来说,劳改犯把胶片交给小女孩,故事才真正开始,因为这时劳改犯已不是陌生人,而是有着悲伤过往且帮助过自己的大叔。在完成大叔心愿和自己的利益之间,她该如何选择?
同理,劳改犯从没有见过女孩真正被欺负的惨状,但如果他见过,如果当他面临在小女孩的安危与自己对女儿那点虚幻的念想之间必须做一个选择时,他又会如何选择?
影片主创在这里,非常自觉地降低了戏剧的强度,它完全回避了人物在这时的内心煎熬。但没有这种灵魂黑夜似的试炼,无论小女孩还是劳改犯的选择都过于顺滑,那影片本来想表现的人性之光也就无从谈起。
没有绝望,就没有希望,没有冷酷,温柔也就无从显现。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影片最后胶片被沙漠掩埋也就不够动人,因为劳改犯已经看到了自己的女儿在银幕上,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那放映员所送给他的那一格胶片,实际上只是一个礼物甚至是一个彩蛋。这是达到目的后的小遗憾。
如果劳改犯到最后没有在银幕上看到自己的女儿,而放映员送给他的唯一一格胶片也被丢弃,那影片的力度将会增大几个数量级。
但张艺谋这一次似乎不想那么戏剧化,虽然是在高度戏剧化的情节设定之下,他也不想过于残酷——劳改犯的女儿死于想摆脱父亲影响、努力挣表现的现场,也就是女儿其实是因父亲而死,这一故事已足够残酷。
他在温情与残酷之间摇摆不定,于是电影中时代的残酷与人物的善良,都显得一厢情愿,面目模糊。
导演让劳改犯愿望成真,看到女儿的影像,但这种温柔恰恰削弱了影片的力度
同样是历史题材,张艺谋选择的是以小见大的路径,而管虎,则用了正面强攻的方式。
《八佰》可能是这几年有价值的电影题材,因为它不只是一个800人(实为400多)对抗比之强大无数倍的日军的故事;也是一个当时的政府将几百条人命当成棋子博取同情的故事,是把闸北四行仓库当成一个戏台,要将日本人的不义展现给全世界的故事。
它是一群怂蛋成长为英雄的故事,同时也是对正统的英雄进行解构的故事,因为英雄的最主要动因并非来自于对正义的追求,而是被别人看作英雄的渴望,
那种置身于聚光灯下的眩晕感,
这种对于英雄本质的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识的触及,让影片有那么一刻超脱于主旋律的束缚而走向了更深的地方。
影片的问题和《一秒钟》一样,同样来自于过于善良。
正如前面所说,影片整体构思宏大,它涉及到当时国际政治的残酷本质:中国的命运,实际上取决于或者部分取决于西方是否干涉日本的入侵行为;它涉及到战争本身的残酷,你必须选择勇敢,如果你选择成为懦夫,你首先会被自己的同袍杀戮。它还涉及到生而为人对于意义的贪婪,无关路人的几声无关痛痒的英雄的称呼,就会让一个人撒热血抛头颅。
但这部影片唯一不敢触动的地方,就是民众。
那些隔江而望的义愤填膺的民众,像极了鲁迅在《药》里面那些围着刑场的看客。
他们那么义愤填膺地渴望别人赴死,是因为自己不在战场上,自己身处安全的英租界,从来没有真正的生命之虞。
他们的义正辞严里,既有真诚的那一面,也有极其虚伪的那一面。
真诚的那面在于,只要不涉及自身的生命和利益,他们都是爱国斗士。虚伪的那一面在于,他们把别人的奋斗和流血,当成了自己在奋斗和流血。他们既是为同胞的英勇而感动,同时也是为自己的那种廉价的宏大情怀而自我感动。但这种感动极其脆弱,只要一丁点溢出的毒气就让他们作鸟兽散。
看客们的虚伪在于,他们为别人的牺牲感动,自己却不愿意牺牲
影片的问题之一,就是没有看透这种看客的虚伪,那种以别人的鲜血浇灌自己所谓宏大情怀的正义。这是一帮可怜人,所以说当影片最后用近乎雕塑似的画面去刻画他们迎接中国士兵的姿势时,就显得相当滥情。
也正是这是这种随时准备付出眼泪的激情,让影片离伟大的史诗电影有着相当的距离。
这种热血,蒙蔽了主创的双眼。让他们不能更清晰的去呈现那场集战争与游戏于一身的历史事件的复杂面貌。不能去呈现人性里高尚与龌龊并存的暧昧状态。也就不能体现出那看透人世间的丑恶却并不因此抛弃众生的悲悯。
当然这是对于电影主创比较严苛的要求,我们还是得感谢这两部电影的主创试图让历史更加丰富的努力。
这两部电影中都有着胶片,在《一秒钟》当中,最终胶片被风沙掩埋,而在《八佰》当中,记录着这800勇士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视频资料丢失。
这是两部电影主创对于历史悲愤而无奈的表达,在它被浓缩为
一个个名词一条条解释的背后,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被牺牲,被遮蔽。
关于现实的题材有两部值得一说,一部是万玛才旦的《气球》,另一部是纪录片《棒!少年》。
在万玛才旦的电影当中,《气球》是最复杂的那一部。
在万玛才旦前期的电影里,无论是《静静的嘛呢石》,还是《老狗》《寻找智美更登》,都是一种静观视角,那些静默的人物和世界的背后,是时代巨变所产生的幽深回响。以静见动,以小见大,以轻见重,是他一贯的思路。
而从《塔洛》开始,他的风格逐渐外显,对人物情绪状态的描摹逐渐加重,朴素内敛的气质被一种更铺张或者说灵动的风格所替代,《气球》也是如此。
任何风格的选择都是双刃剑。
万玛才旦之前那种沉静甚至是木讷的风格,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可看性不高,但这种影像风格甚至演员表演的静态,与隐在视觉焦点之外的时代的动势之间巨大的反差,构成了万玛才旦早期电影的主要魅力。
而到了后期,他电影中人物内心的风景,成了他最直接的表对象。这时事件本身,或者人物内心的丰富度,就成了影片魅力的最主要来源。
对这部影片来说,这种丰富度是不够的或者说过于散乱。
这部影片的主题涉及如下方面:再生一个孩子,与家庭贫困之间的矛盾。想打掉孩子,但孩子是爷爷的转世之间的矛盾。是相信孩子是爷爷的转世,还是相信科学的矛盾。当然还有一种即使所有生小孩的理由都成立,但孕妇本身是否愿意的矛盾。
这每一种矛盾都是一个重大的命题,都值得一整部电影的篇幅来叙述和描摹,但问题就在这里,
只有一部电影的篇幅
,于是所有的矛盾的描绘都蜻蜓点水。
篇幅有限,导演想要探讨的问题又太多,所以对每个主题的讨论都是蜻蜓点水
我们看不到这个家庭处在一种多么拮据的状态,也就不会对这个母亲因为再生一个孩子感到无力为继感同身受,更不会对一个儿子突然说出一句“我要退学”而感到唏嘘万千。
我们看不到爷爷和自己的子女或者孙子之间的巨大的情感,于是也就不能体会当他们听说要打掉这个据说是爷爷转世的婴儿的情感冲击。
我们看不到现代科技观念对于藏区信仰的逐渐瓦解,那种身处于古代信仰与现代认知之间的摇摆不定的尴尬,我们也就无从感知。
而最后一点,一个女人在自己生育问题上的选择权其实是一个相对现代的问题,也就是即使所有的困难都不存在,她是否具有主宰或者说一定程度决定自己是否生育的权利。如果要表现对这一点,就要去表现藏区家庭这一基本政治单位里面的权力结构,以及这个女性是如何被粗暴或者隐晦的排斥在这一权力中枢之外的。
影片在这些主题之间流转,就如同在影片视角在孩子、父亲、母亲之间流转一样,最终造成每一种情感关系都无法被有说服力的建立,每一种矛盾都无法真正触及灵魂。
也正因为如此,影片才不得不借助于一些非常意象性或者说概念化的东西,比如那只不能配种而被卖的羊,比如避孕套以及气球,但这些东西仍然无力将那些巨大无朋的主题粘合成一个整体。
另一部有关现实的电影是《棒!少年》。这是一部纪录片,但拍得像一部剧情片,甚至是过于戏剧化,以至于从某种程度它有着摆拍或者引导性地建构某种戏剧情境的嫌疑。
如果不管这些伦理问题,相较于《气球》,
它的优点在于它不刻意升华主题。
它将它的目光完全聚焦在两个小孩身上,当这两个小孩的精神世界被相对鲜活地呈现在银幕上时,我们从他们身上自然而然地看到了这个时代打在他们身上的烙印,和投在他们身上的巨大阴影。
那个桀骜不驯的孩子马虎是中国电影中少有的人物。
他就像一头未被驯服的小兽,他天然地相信暴力,也准备用暴力去解决一切,解决争端,获得别人的尊敬,获得别人的友情,但结果是众叛亲离。让人印象更深刻的是那种暴力背后的虚弱,晚上无人陪他睡觉时的胆怯,强行索要友情而不得时的自暴自弃。种种情况,让人莞尔,也让人叹息。
影片充满着那些我们在剧情片里难以看到的灵动细节,在这样一部细节满溢的电影里,相较《气球》,那些意象性的东西的出现,就显得空灵而恰当。
它们是悲伤的马虎眼中看到的那伴随着飞机轰鸣声飘舞的塑料袋,是那些队员行走在郊区拆迁的废墟上,伴随着他们脚步声的那疑似建筑工地打桩声的音效。
这是两个精妙的比喻,
映射出的是他们被强大的社会变革噪声所淹没的人生,和他们看似无望却执着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奋斗。
纪录片中的少年们或许已经比无数未被大众看到了留守儿童、孤儿们幸运
纯类型片中最值得说的也是两部,而这两部都由香港导演操刀完成。
一部是《除暴》,另一部是《拆弹专家2》。《除暴》是一部相当怪异的电影,它和《拆弹专家2》一样,是一部叙事和节奏密度相当高的电影,在情节的推进和反转方面,主创都有着娴熟而且扎实的能力。
有趣的地方在于人物,主创对于无论正邪两方都拒绝给出他们的人物背景,以及双方都如此勇敢的动因,
当然除了撕掉警察宣传画上面的牛皮癣广告所代表的那种为警察正名的赤裸裸的理念之外。
对于吴彦祖所饰演的劫匪,你不知道他的疯狂是一种生理性的变态,还是对于财富的贪婪,一种对社会不公的愤世嫉俗的报复,亦或是一种完全的反体制的行为;对于春夏这个角色也同样如此。影片既不提供让你恨他的理由,也不提供让你爱他的理由,他就无理由悬浮在那儿。
影片并未交代人物背景,难免让观众对他们对身份产生疑惑
那种怪异感,不只体现在人物上,也体现在影像上面。那种90年代初的做旧质感,和街道上过于空旷和干净的气氛交相辉映,让你有一种隐隐的不真实感。
但无论是人物还是环境的不真实,你又能明显看出这并非主创能力的缺陷,那更像是一种不作为。
从整体上看,它就像杜琪峰若干年前在内地拍摄的警匪片《毒战》,然后再加上一个极其纯净的主旋律外壳。
《毒战》的好,在于它把警匪之间的争斗,变成了一场动物世界般的宿命追逃。
它的好在于无关善恶,警察对于匪徒的兴趣,更像是一种猫见到老鼠后的本能的狂热。
它的好也在于善恶。古天乐所饰演的毒贩,为了活命,可以抛弃一切,包括亲情友情同僚之情,但最终又在宿命可笑而又冰冷的双手之中束手就擒。
杜琪峰那种冷到冻出冰碴子的残酷感和宿命感,让警匪双方都成了典型的存在主义人物:不明所以的活着,不明所以的狂热,不明所以的追逐,不明所以的曝尸荒野。
而《除暴》或者不敢或者不愿或者不能或者不会去触及到真正人性或者社会的层面,却又想保持一个酷酷的姿势,于是就变成了现在这副无法落地的尴尬样子。
与《除暴》的拒绝阐释相反,《拆弹专家2》更倾向于过度阐释。
主创的愤怒几乎要溢出银幕外,这种愤怒被负载在刘德华和谢君豪所饰演的潘乘风与马世军身上。
这是一种对于现存社会结构高度不信任的反社会情结,对整个官僚体系对其中成员用完即弃的悲愤,是要用自己的肉身来献祭变态理想的激情,以及要用全世界来为理想陪绑的残忍。
《拆弹专家2》中的角色因自身遭遇,对社会、体制充满了愤怒
这种愤怒赋予影片一种狂暴的激情:
当潘乘风被害怕担责任的警察拒绝,无法回到原岗位时;当潘乘风打出用完即弃的标语,却被众人拽脱义肢时;当潘乘风说出我不是疯我是痛时;当董卓文痛斥警察部门的长官和庞玲利用潘乘风的失忆时;当马世军与潘乘风从飞机上跳伞,说出一起毁灭旧世界打造新世界的豪言壮语时;以及核弹爆炸蘑菇云升腾,一切灰飞烟灭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