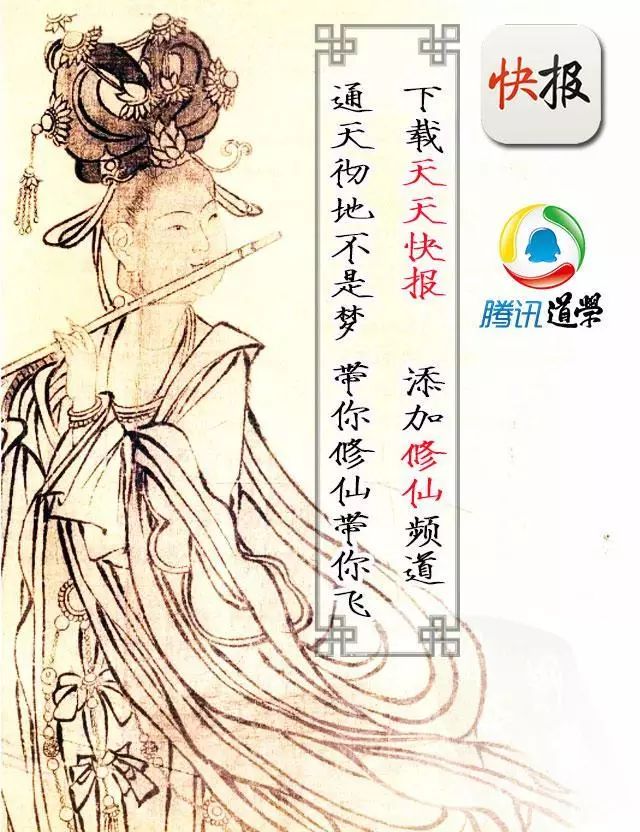白玉蟾把“玄德”解释为“教父”,并把“玄德”之深邃,归结为“道为万化之宗”,一方面阐明了“玄德”的功能;另一方面阐明了“玄德”的地位。
张丰乾,男, 1973年8月生,甘肃古浪人,哲学博士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研究兴趣为中国古代哲学与宗教,出版专著两本、编有文献辑校两本。近年致力于《道德经》、《周易》、《论语》、《诗经》、《坛经》等经典的阐释和讲授,并尝试对中国先贤所提出的哲学和宗教议题进行梳理和阐发。
白玉蟾真人(1134-1229)作为道教巨擘,“诞生海表,位列真灵。有宋以来,谈道者罔不推为正宗”。
他善于融会贯通而思想主旨鲜明,其《道法九要·序》开宗明义:“三教异门,源同一也。”
他有多篇“偈语”传世,和诸多禅师有应和,对儒家思想也多有吸收。
后人推许他在儒学方面造诣很高,且写文章既快又好,不落俗套
:“博洽儒术,出言成章,文不加点,时谓‘随身无片纸,落笔满四方’。其言皆囊括造化之语,儒者谓‘出入三氏,笼罩百家,有非世俗所能’也。”他
自己也一再推许“孔颜乐处”,强调儒道合一,但他的诗文均以阐述清静长生的道教思想为宗旨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别开生面而文采斐然,是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
白玉蟾对于终极理论上的“道”和修道实践中“法”同样看重,认为二者不可分离,相互符合,可以济世
:
夫老氏之教者,清静为真宗,长生为大道,悟至于象帝之先,达之于混元之始,不可得而名,强目曰“道”。自一化生,出法度人。法也者,可以盗天地之机,穷鬼神之理;可以助国安民,济生度死,本出乎道。道不可离法,法不可离道,道法相符,可以济世。(《道法九要·序》)

清静为真宗,长生为大道(资料图)
白玉蟾所理解的“老氏之教”,不仅仅局限于人世间或天地之间,而是通向“象帝之先”、 “混元之始”,亦即“道”的本初状态。换言之,“
老氏之教”就是“道” 的体现,由整体原始的“一”化生而来,非人力所为。
白玉蟾并没有接着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路讲述万物生成的过程,
而是指出了“老氏之教”的功用:“出法度人”。他所说的“清静”和“长生”,不是仅指个别人的修行成就,而是着眼于“人人得道,个个成真”的美妙目标
:
近世学法之士,不究道源,只参符咒。兹不得已,略述九事,编成一帙,名曰《九要》,以警学道之士,证入玄妙之门,不堕昏迷之路,人人得道,个个成真,岂不美歟!(《道法九要·序》)
白玉蟾所阐述的“法”也不是稀松平常的“法术”,而是出自于“道”,功能强大,内容丰富
,可以摄取天地奥妙,穷尽鬼神理数,助力国事安定民众,而没有所谓“出世”和“入世”的区别。
在《道法九要·行法第六》中,白玉蟾又特别指出了“法”的重要作用:
夫法者,洞晓阴阳造化,明达鬼神机关,呼风召雷,祈晴请雨,行符咒水,治病驱邪,积行累功,与道合真,超凡入圣。
他同时强调施行法术,“必先明心知理,了了分明,不在狐疑。
”
他也介绍了一些具体的法术,但突出施行法术的目的是“救民疾苦”,而施行法术的前提则是“德合天心”。
白玉蟾说:“驱邪之道,先立正己之心,毋生妄想,审究真伪。古云:若要降魔鬼,先降自己邪。”
“邪气侵则成病,以我正真之气,涤彼不正之邪,以我之真阳敌彼之阴。若患者执迷邪道,可方便化之,符水而治之。
” 凡此种种,对当代道教亦有重要借鉴意义。
他特别批评“不究道源,只参符咒”的功利做法和短视行为,以《道法九要》来警示学道之士
;但他的警示也不是挖苦讽刺,而是以深刻的思想、优美的文句加以劝导,既
着眼于根本理论的阐发,又注重具体方法的指引,可谓苦口婆心,面面俱到。
白玉蟾认为,他所阐述的“法”还体现在“颜回之乐”上:
人生天地之间,衣食自然分定,诚宜守之,常生惭愧之心,勿起贪恋之想,富者自富,贫者自贫,都缘夙世根基,不得心怀嫉妒。学道惟一温饱足矣。若不守分外求,则祸患必至。所谓颜子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者,贤人也。学道人若外取他求,则反招殃惑也。道不成而法不应。若依此修行,法在其中矣。(《道法九要·守分第三》)
“颜回之乐”为后世儒家所津津乐道,但
白玉蟾的侧重点却在于人的物质享受为天地之间的条件及个人的身份所限定,确实应该持守自己的身份,常常生发惭愧之心而不要兴起贪恋之向。
他同时也指出了不守本分而向外贪求,一定会招致祸患,“道”不会修成,“法”也不会响应。倘若像颜回那样安贫乐道,其中就蕴含了符合“道”的方法。
颜回早死令人惋惜,但是如果按照“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标准,颜回无疑是修行者的榜样。
白玉蟾不仅注重内在精神境界的养成,也
强调外在禁戒的不可或缺
,《道法九要》中有专门的“持戒”一节:
夫行持者,行之以道法,持之以禁戒。明其二字端的,方可以行持。先学受戒持斋,神明自然辅佐。萨真人云:“道法于身不等闲,思量戒行彻心寒。千载铁树开花易,一入酆都出世难。”岂不闻真人烧狞神庙,其神暗随左右,经一十二载,真人未尝有纤毫犯戒,其神皈降为辅将。真人若一犯戒,其神报仇必矣。今人岂可不持戒?更当布德施仁,济贫救苦。昔旌阳许真君,一困者为患,其家抱状投之于君,君闻得疾之因,乃缘贫乏不得志而已。真君以钱封之于符牒,祝曰:此符付患者开之。回家,患者开牒得钱,以周其急,其患顿愈。济贫布施则积阴德,行符之人则建功,皆出于无心,不可著相。著相为之,则不是矣。若功成果满,升举可期矣。
在白玉蟾看来,
“持戒”并非仅仅是洁身自好,以个人修养为目的,而应当进一步传播美德,施行仁爱。
同时,他也指出救济贫苦是积累阴德,行符治病是建立功业,都是出于无为之心,不可以执著于表象。
白玉蟾道教思想的基点,是突出“道”的神妙作用,同时注重“人道”的修为:
夫道者,入圣超凡,福资九祖,逍遥无碍之乡,逸乐有玄之境,聚则成形,散则为风,三清共论,玉帝同谈,不属五行,超离三界,此乃证虚无之妙道。欲登此道,先修人道,去除妄想,灭尽六识,明立玄牝根基,须分阴符阳火,如鸡抱卵,出有入无,功成行满,身外有身,仙丹妙宝,随意自取,玉室金楼,随心自化,呼风叱雨,坐役鬼神,嘘气可以治病,点石可以为金,不与凡同,奉膺天詔,证果真仙矣。(《道法九要·明道第五》)
白玉蟾对于“心”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格外突出。
前文已引,白玉蟾以“悟至于象帝之先”为学道目标,他在注解《老子》时,认为“心”是万物之宗,屡屡用“心”来贯通道体和功用:
道,冲而用之久或不盈,虚中。渊乎似万物之宗。心也。挫其锐,敛神解其纷,止念。和其光,藏心于心而不见。同其尘。混心于物。湛兮似若存。存神于无。吾不知谁之子,吾象帝之先。
载营魄安心抱一,能无离乎?甚处去来?专气致柔,纯清绝点能如婴儿乎?混然一片。涤除玄览,能无疵?无事于心,无心于事。爱民治国,怡神养气。能无为乎?无念无为,无思无虑。天门开阖,心地开明能无雌乎?一而不二明白四达,一理烛物,冰融月皎。能无知乎?终日如愚。生之,畜之,一心所存,包涵万象。生而不有,心同太虚。为而不恃,智周万物。长而不宰,泰然无我。是谓玄德。

涤除玄览(资料图)
对于“天门开阖”,《老子河上公章句》的解释是:“天门谓北极紫微宫。开阖谓终始五际也。治身:天门,谓鼻孔开,谓喘息阖,谓呼吸也。”
其中的“天门”在“天”的层面指“北极紫微宫”,而在人身体的层面则是指鼻孔,天门开阖即是通过鼻孔呼吸的过程,而白玉蟾则把“天门开阖”解释为“心地开明”。
故而,白玉蟾所阐发的
“藏心”、“混心”、“无心”、“存心”,恰恰是“开心”的重要途径。
白玉蟾所言“心同太虚”,在朱熹哪里也有共鸣:
设使此心如太虚然,则应接万务,各止其所,而我无所与,则便视而见,听而闻,食而真知其味矣。看此一段,只是要人不可先有此心耳。譬如衡之为器,本所以平物也,今若先有一物在上,则又如何称!(《朱子语类》卷十六)
朱熹之言,是解释《大学》“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太虚”出自《庄子》,而张载非常重视,
作为博洽儒术的白玉蟾,以“心同太虚”解释“生而不有”,把生化论引申为境界论,开人思路,启人心智。
白玉蟾在注解《老子》时,还提出了“即心即道”、“即道即心”、“心与道合”、“心无所始,亦无所终”;“即心是道”;
“道即心、心即道”以及“见物知道、知道见心”,“人能虚心,道自归之”;“平常心是道,不用生分别”
;“道为一心之体”;等说法,可谓“心道玄同论”。
以“心道玄同论”为基础,白玉蟾还提出了“万法从心生”、“心专则法验”的思想,其《鹤林传法明心颂二首》有云:
万法从心生,心心即是法。语嘿与动静,皆法所使然。无疑是直心,守一是正法。守一而无疑,法法皆心法。法是心之臣,心是法之主。无疑则心正,心正则法灵。守一则心专,心专则法验;非法之灵验,盖汝心所以。
在《道法九要》中,白玉蟾则专门阐释了“守一”的重要性:
近观行持者,间或不灵、呼召不应者,何故?初真行法者累验,广学者却不如之,此非法之不应也,缘学者多传广学,反使不能纯一,分散元阳,登坛之际,神不归一,法不灵应。岂不闻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人得一以灵。”今志于行持者,必当守一法,而自然通天彻地。不知守玄抱一为最上功夫,但耽于广学,反不能纯一矣。盖上古祖师,虽有盈箱满筪灵书,留之引导凡愚,开发后学。不知师心自有致一之妙,不教人见闻,鬼神亦不知其机,用之则有感通。且法印亦不可多,专以心主一印,治一司,专用一将,仍立坛靖,晨夕香火崇奉,出入威仪,动止恭敬,诚信相孚,自然灵应。切不可疑惑有无,昧于灵台。须是先以诚敬守之,必获灵验。斯为守一之道矣。
白玉蟾主张博学,但也重视由博返约,达至专一,在法术方面也是如此。他还特别强调诚敬的重要性。
白玉蟾《道法九要》以“立身”为第一 ,要求学道者由惭愧心出发,每日按照焚香稽首的仪式表达皈依之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白玉蟾把“陈以往之愆”即忏悔列为首要之事,使“修”和“学”有了切实的着手处:
学道之士,当先立身。自愧得生人道,每日焚香,稽首皈依太上大道三宝,首陈以往之愆,祈请自新之祐。披阅经典,广览玄文;屏除害人损物之心,克务好生济人之念;孜孜向善,事事求真;精严香火,孝顺父母,恭敬尊长;动止端庄,威仪整肃;勿生邪淫妄想,勿游花衢柳陌,勿临诛戮之场,勿亲尸秽之地。清静身心,远离恶党。始宜寻师访道,请问高人。此乃初真之士,当依此道行之。
白玉蟾非常重视道教经典和文献的学习,以此为基础,要求修道者“叩其两端”:
屏除害人损物的心思而努力实践热爱生命、帮助别人的理念
。白玉蟾强调向善没有懈怠,求真不遗余力;在香火仪式方面要一丝不苟,在日常生活中要孝顺父母,恭敬尊长,举止端庄讲究。
清净身心的具体方法包括思想上不要产生邪恶、放纵的妄念;行为上不要涉足污秽凶暴的场所,不要结识恶劣的群体。
做到这些,才适合去寻找师父,探求道理,向高人求教。可见,
白玉蟾主张的“立身”之道与“立身”之法,既有清晰明确的理念,又有切实可行的途径
。
如果说,“立身”之道的“身”,意为“自己”的话,那么与“心”并提的“身”则是指身体而言。道教特别注重修身炼形,白玉蟾特别指出:
玄修与释家不同,释家呼此形骸为臭皮囊。道家入门,全要保此形体
。
故形为载道之车,神去形即死,车败马即奔。心有真功夫者,貌必有好颜色。心犹君也,身犹天下。

身心一如,身外无余(资料图)
白玉蟾深得老庄意趣,他把《老子》中的“我独顽似鄙”解释为“身如槁木,心如死灰”,
身心玄同的最高境界从正面讲是“身心一如,身外无余”,从反面讲则是“放下身心。”
但“身心玄同”并不意味着“身心等同”,他强调心的主导功能,并指出“心能内观”:
心乃一身之主,故主人要时时在家。一时不在,则百骸乱矣,所以学道贵恒。始勤终怠,或作或辍,则自废也。
三界之中,以心为主。心能内观,即一时为尘垢所染,终久必悟大道。若心不能内观,究竟必落沉沦
。故《老子》首章曰“常有欲,以观其窍”者,观此窍也。“常无欲以观其妙”者,现此窍中之妙也。太上曰:“吾从无量劫中以来,存心内观,以至虚无妙道。”
学子既欲潜心,先去内观,待心中如秋潭浸明月,再谈进步。
凡人能治心,便是道中人。若全消俗障,何患乎不成?
白玉蟾总结说:
“学道先从识自心,自心深处最难寻。若还寻到无寻处,始信凡心即道心。”
白玉蟾多次引用宋儒的“变化气质”说及“气质之性”与“天命之性”的区别论,认为
“修道总是炼得一个性”
:
学道先以变化气质为主,再到与人接物上浑厚些,方是道器。
修道总是炼得一个性。有天命之性,有气质之性。本来虚灵,是天命之性;日用寻常,是气质之性。
今一个天命之性,都为气质之性所掩。
若炼去气质之性,自现出天命之性,而道得矣。
与宋儒不同的是
,白玉蟾提出了一系列“炼去气质之性,现出天命之性”的方法,最重要的是去掉心中之“意”和“识”
:
夫心之动,非心也,意也。神之驰,非神也,识也。意多欲,识多爱。去此二贼,真性圆明。不欲何贪?不爱何求?无贪无求,性如虚空,烦恼妄想,皆不为累。再加炼气,金丹可成,神仙可冀!
可见,
白玉蟾所论心、性之统一与净化,在于去除多欲之意和多爱之识,辅之以炼气化形,则真性得以圆明,金丹可以成就而神仙可以希冀。
与此相对照,他以“自昧固有之心,本来之性”来解释《老子》所言“大道废”。
《老子》第七章云:“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白
玉蟾在《蟾仙解老》中先后提出“此心长存”、“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同体”;“天地即我,我即天地”等思想,可视为与天地万物的玄同。
他还指出:
天之生人,人之所以生而不死者,“於穆不已”也。人若无此不已,则气绝矣。故天地以气机存,人亦以气机生。能炼住气机,便与天地同寿,便不息了。不息则久,《中庸》言之矣。
白玉蟾所说的人与天地“同寿”、“同根”及“不息”,
不是侧重于精神层面的“永垂不朽”,而是以“炼住气机”为具体的方法。
他用“性长存”来解释《老子》中的“不失其所这久”,用“神不死”来解释“死而不亡者寿”,亦可理解“同于其所者久,同于其神者寿”,亦即玄妙之同。

天地即我,我即天地(资料图)
白玉蟾在解释《老子》中的“域中有四大”时说“上无复色,下无复渊,灵然独存,玄之又玄”,
他紧接着用“同乎无始”来解释《老子》中的“天大”,用“同乎无终”来解释《老子》中的“地大”,使用了互文的修辞手法
,换言之,“天地”之所以“大”,均在于“无始无终”。基于此,白玉蟾把“人法地”解释为“有所依据”,而把“地法天”解释为“一灵妙有,法界圆通。
”所谓的“圆通”,亦可理解为“玄同”。
白玉蟾富有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其《道法九要》中有“济度”一节,要求
学道之人洞察明了自己的心理状况,不要喜好奢华,不要嫌弃贫贱,不要执著于为凡尘所累的地方,不要在爱欲之河中漂泊徘徊
;而代之以恬淡自然,逍遥无碍, 不是愤世嫉俗,而是与尘世和同。和同于尘世,并非是形式上的“打成一片”,而应当首先用道教特有的符来治疗疾病,成就万物而利益众人,这样就可以把救赎对象由自己的祖宗,扩展到其他生物:
学道之人,洞明心地,不乐奢华,不嫌贫贱,不著于尘累之乡,不漂于爱河之内;恬淡自然,逍遥无碍,尘世和同。先当行符治病,济物利人。此可拔赎沉沦,出离冥趣,先度祖宗,次及五道。以我之明,觉彼之滞;以我之真,化彼之妄;以我之阳,炼彼之阴;以我之饱,充彼之饥;超升出离,普度无穷,斯为济度矣。
白玉蟾
把学道之人的济度之法归结为推己及人
,以明觉滞,以真化妄,以阳炼阴,犹如以饱充饥,包括思想上的启发,心性上的改化,身体上的修炼以及精神上的扶持。
白玉蟾非常重视道法的传承,其《道法九要》的最后一节为“济度”,其中强调修道之人要感念天地、国王、父母、师友的恩德;
自己掌握道法,得心应手之后,就可以选择他人作为继承者,交付其理论和方法
,不能使道教的脉络在自己这里断绝。
学道之人,得遇明师,传授秘法,修之于身,行之于世,人天敬仰,末学皈依,愧非小事,当知感天地阴阳生育之恩,国王父母劬劳抚养之德,度师传道度法之惠,则天地国王父母师友,不可不敬,稍有违慢,则真道不成,神明不佑。道法既得于身,道成法应,可择人而付度之,不可断绝道脉。
但
白玉蟾也对道脉的传承非常审慎
,强调必须平时多加观察和磨炼,不是合适的人选,不能轻易传授道法。
须是平日揣磨,得其人可以付者付之。苟非其人,亦不可轻传也,罪有所归。若得人传授,但依祖师源流,不可增损字诀,忠孝之心相契,切勿生人我之心。弟子若负师,天地神明,昭然鑑察,毫分无失。师伪,弟子亦然。若无人可度,石匣藏于名山福地、海岛龙宫,劫运流行,自然出世。
对于这些主张,白玉蟾身体力行,他申述写作《道法九要》的宗旨:
予感天地父母生化之恩,诸师传道教训之德,将其所得,册成九事,以警后学。若修身立己,积德累功,上体天心,下利人物,行道成真,超凡入圣。
可见白玉蟾的理论是贯通人与我、天与人、人与物的,既重视个人的修炼,也重视功德的积累,强调实行道法成为真人,超越凡俗,优入圣域。
“玄同”之说,出自《老子》: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忿,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老子》第五十六章)
“玄同”是闭塞基于耳目和门户之见的选择性接受,容纳差异而超越差异之同。
不仅和于耀眼的光芒,也同于漂浮于空中的尘埃。亲疏、利害、贵贱均可以使一些人结成小团体而排斥另一些人,而
真正难得的是亲疏、利害、贵贱均没有可能左右其思想、心态和言行的人——这样的人和其他任何人的关系都是“玄同”。

大道废,有仁义(资料图)
虽然孔子认为: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子路》)但儒家的“大同”理想依旧人们所熟知及向往,这一理想集中表述于《礼记·礼运》之中: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一鼓舞人心的理想其前提是“大道之行”,但《老子》却冷峻地指出了“大道废”的一系列后果: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第十八章)
《庄子·胠箧》甚至主张:
“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
”白玉蟾的思想没有如此激烈,但也和老庄一脉相承。前文已引,
白玉蟾用“自昧固有之心,本来之性”来解释《老子》所言“大道废”,他还用“非其本真”来解释“有仁义”,“终非本然”来解释“智慧出”,
“即非自然”来解释“有大伪”,“自相分别”来解释“六亲不和”,“盖所当然”来解释“有孝慈”,“生死岸头”来解释“国家混乱”,“到此方知有所养也”解释“有忠臣”,更加凸显出
大道之废,是由于人类自己蒙昧了固有的自然之心和本来的淳朴之性。
白玉蟾把在《蟾仙解老》中把“玄同”解释为“圣凡一体”,可谓远见卓识,但“玄同”不是“等同”,“圣凡一体”的前提是“超凡入圣”,凡人不必妄自菲薄:
“人当以圣贤自待,不可小视自己,则上达矣。故天下未有不圣贤的神仙。
”
也不要得过且过,更不要自暴自弃,而是要有“入圣”的志向,从立身做起,皈依真师,谨受本分,持戒行法;
但也不要自命清高,隔绝于凡俗,满足于做一个“自了汉”,而应以“济物利人”为念,济度众生而承袭道脉。
前文已言,玄同是容纳差异而超越差异,化解差异而重构新的存在方式之同,《说文解字·玄部》:
“幽远也。黑而有赤色者为玄。象幽而入覆之也。
” “玄”的涵义是幽深长远,而不是浅显短促。作为一种颜色,“
玄”本身就是红与黑两种看似极端对立的颜色“玄同”的结果。
根据段玉裁《说为解字注》阐释说: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老子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高注《淮南子》曰:‘天也。’圣经不言玄妙,至伪《尚书》乃有‘玄德升闻’之语。”
“黑而有赤色者为玄。此别一义也。凡染、一入谓之縓。再入谓之赪。三入谓之纁。五入为緅。七入为缁。
”“至七入则赤不见矣。缁与玄通称。故礼家谓缁布衣为玄端。凡玄之属皆从玄。”
“玄同”也是道、佛两家共同推许的思维方式、行动原则及社会理想:
求美则不得美,不求美则美矣;求丑则不得丑,求不丑则有丑矣;不求美又不求丑,则无美无丑矣。是谓玄同。(《淮南子·说山》)
夫佛经自谓得道者,能玄同彼我,浑齐修短,涉生死之变,泯然无概;步祸福之地,而夷心不怛;乐天知命,安时处顺耳。其未体之者,哀哉慎终之心,乃所以增其笃也。(《弘明集》卷一)
达天网之宏疏,故期之于靡漏;悟运往之无间,混万劫于一朝;括三世而玄同,要终归于必至。(晋·郄超《奉法要》,见于《弘明集》卷十三)
日月交,铅汞合,故经曰:“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又曰:“复归其明,此之谓也。”(《云笈七签·卷七十二》)
知以无涯伤性,心以欲恶荡真,岂若守根净冲,栖研三神,所以弥贯万物,而玄同镜寂,泯然与泥丸为一,而内外均福也,可示虎牙。(《真诰·甄命授第二》)
“玄同”的实现,必依赖于“玄德”。“玄德”也是内涵深邃、包容差异对立而超越差异对立之德。如郑开所论:
“道家盛称‘玄德’,因为它不是当时人们所推崇的"明德",而是比‘明德’更具深远意味的价值概念。”

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资料图)
《老子》中用“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及“常知楷式”来界定“玄德”,白玉蟾亦做出了独到精要的解释: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无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生之畜之,一心所存,包含万象。生而不有,心同太虚。为而不恃,智周万物。长而不宰,泰然无我。是谓玄德。
道生之,神也。德畜之,性也。物形之,心也。势成之我也。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忘物。道之尊,忘我。德之贵,忘心。夫莫之命,忘性。而常自然。忘神。故道生之,神全。德畜之,性全。长之育之,心全。成之熟之,我全。养之覆之;物全生而不有,无也。为而不恃,无为。长而不宰,无我。是谓玄德。道也。
古之善为道者,我也。非以明民,不使其有知。将以愚之。昏昏默默。民之难治,以其智多。静则易浑,动则易散。故以智治国,国之贼;觉亦是念。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无所觉知而已。知此两者亦楷式。道贵如愚,愚中不愚。常知楷式,抱虚守冲。是谓玄德。教父。玄德深矣、邃矣,道为万化之宗。与物反矣,道在万化而非万化。然后乃至大顺。万化出乎道而入乎道。
白玉蟾把“玄德”解释为“教父”,并把“玄德”之深邃,归结为“道为万化之宗”,
一方面阐明了“玄德”的功能;另一方面阐明了“玄德”的地位,体现了他深厚的学养和精湛的思辨,以及美妙的表述
;也蕴含着他勤恳卓越的修炼经验。结合老子和白玉蟾的思想,笔者认为
“玄同”包括道与法、天与人、人与物、己与人、身与心、德与功等诸多方面,无论哪一方面的“玄同”,均以“玄德”为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所包含的“类”与 “同”其实有非常丰富的内涵,“人以类聚,物以群分”——
“类”和“群”的基础是什么?怎样对待“异类”和“不合群者”?“和而不同,不同而和”——“和”从何来?“同”与“不同”如何“玄同”?
《老子》有云: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白玉蟾解释说“不以我为我,乃见心中心。”“人心我心,同乎一性。”
关键所在,是突破二元对立及以“我”为中心而排斥他者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
(编辑:忆慈)
“道化天下 世界玄同”有奖征文活动投票环节开始啦!
欢迎投下您尊贵的一票。投票以后,
移步评论区留言
,就有机会在投票结束后获得
精装版《白玉蟾真人全集》一套哦,快来吧!
点击文末
阅读原文
,更多精彩道学参赛文章等你哦。
(本文为“道化天下 世界玄同”道学全球有奖征文比赛作品,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文:张丰乾,文章原标题为《道法相符以济世 学行并重成玄同——白玉蟾真人道教思想探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