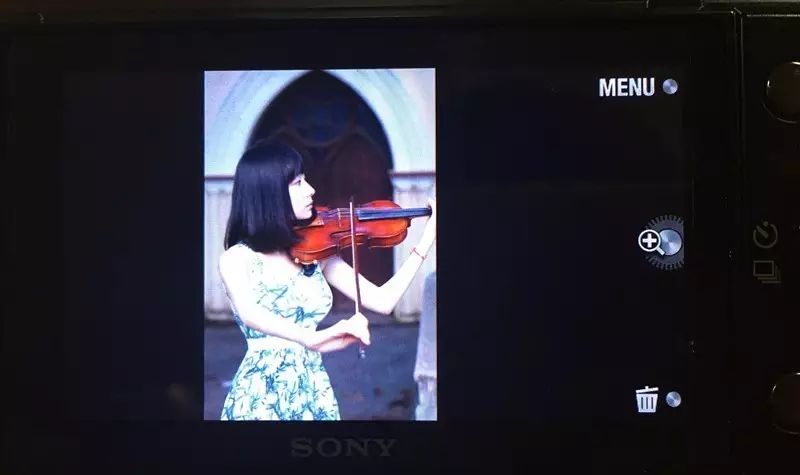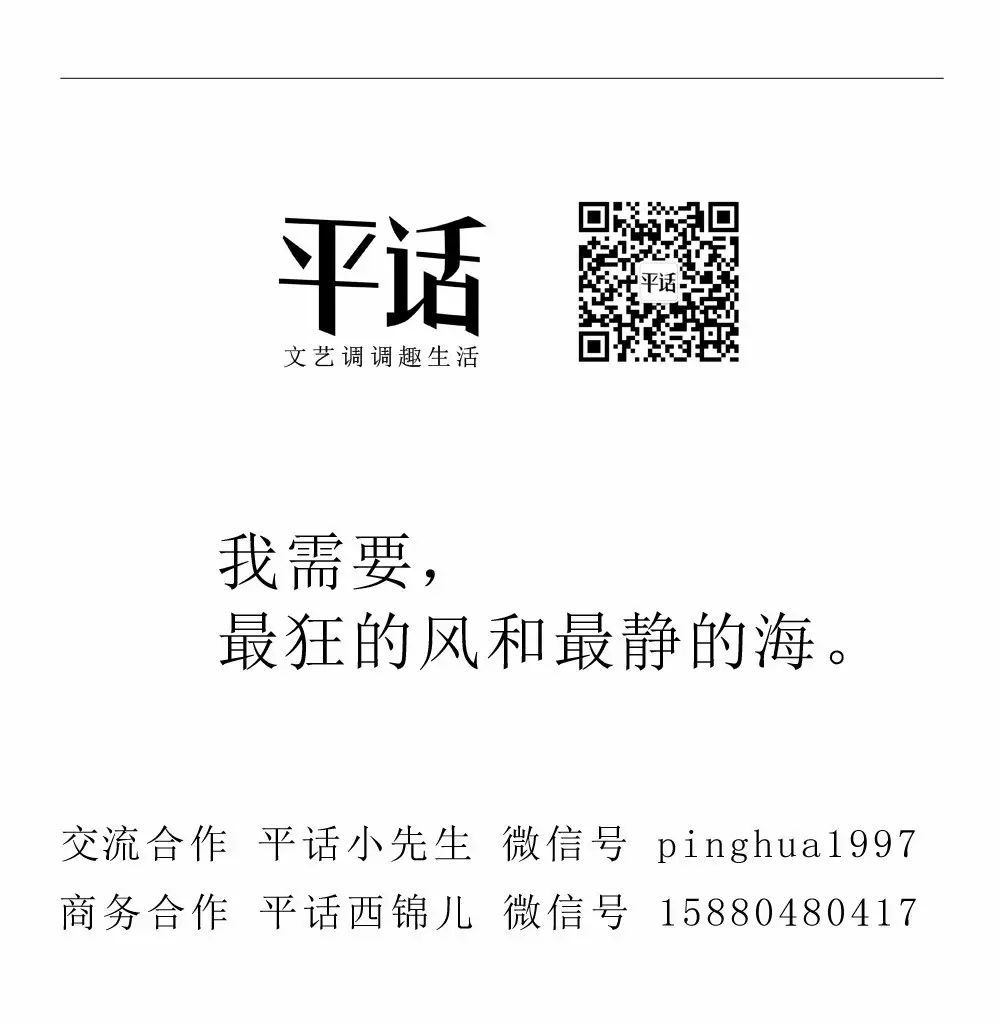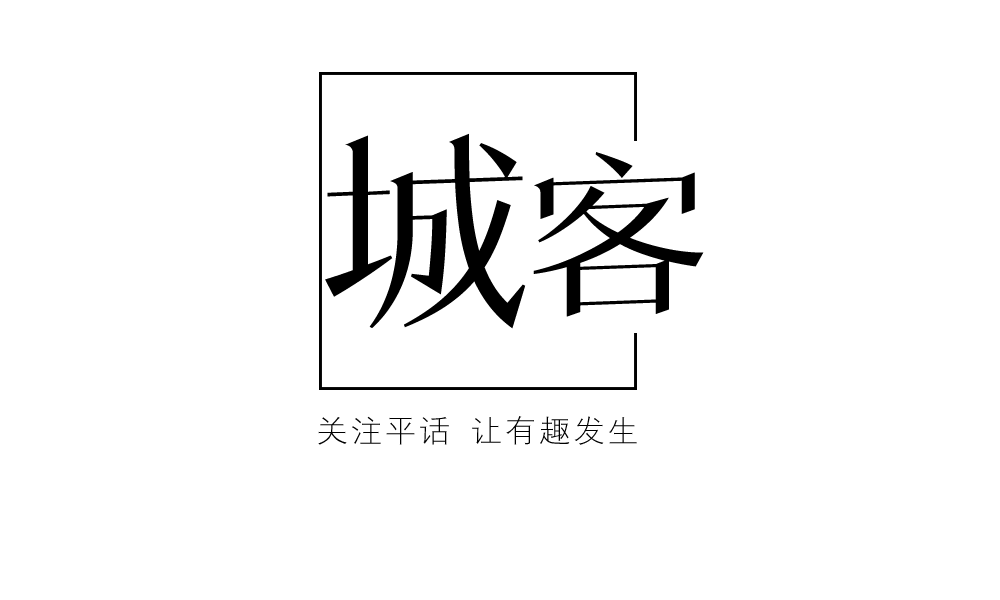
在这个十年里,福州越来越多的人组成了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不满足于这座城市的现状,在某个时候离开,把自己投入到一个节奏更快挑战更多视野更辽阔的世界里,然后去寻找一种“回家”的可能性。所以由始至终,他们的“离开”都是为了更好的回来。
叶子青是其中之一。
即便最后殊途同归,但离开时的那些故事却各自不同。

“每个人都觉得你的日子光鲜亮丽”
半年多前,我和她聊过一次“为什么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海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归’的女博士”这个话题。她说之所以会选择千里迢迢飞往英国,去念这个博士,只是是想毕业以后方便在福州找一份大学老师的工作。
我表示,比起星辰大海,这是我听过最实在最亲切的出国读博的理由。
“反正最后还是要回来的。”
也只有福州人“随时随地想回家”的种族天赋,加上半勺不甘虚度人生的野心,才会根须纠缠地长出这么一株非常闽地风味的植物。
和她聊起“离开”的生活,她最大的感受是,“不只是读博,我从硕士开始就在英国生活,每个人都觉得你的日子光鲜亮丽,但其实背井离乡去陌生的城市国家,和你熟悉的人昼夜相隔,很多孤独无助的时候,只有自己消化。”

“这不是你的城市,也一点儿不友好”
硕士那年,第一次“离开”,“一个月时间,这么多年建立起来的自信,全部推倒。”
赴英的第一个月,中日钓鱼岛事件爆发。“我有一门非常重要的课,老师是日本人,几乎每节课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冷嘲热讽,只针对我一个人——中国人都和你一样很爱耍小聪明吧?你究竟是怎么考到我们这儿来的啊?你不会觉得你真的能拿到我们大学的学位吧?”
她的小提琴老师,从皇家音乐学院外聘过来的教授,对学生严厉到近乎苛刻。她有好几次上着课差点儿被摔琴赶出去。有一次快下课了,又被劈头盖脸地一顿骂,末了教授还撂下一句话,说你这样是绝对不可能毕业的。

“那阵子英国天气非常差,下午三点天就黑了,我当时坐地铁回家,气氛阴阴沉沉的,地铁停靠又启动,各种各样的陌生面孔在你眼前来来去去。这不是你的城市,也一点儿不友好,你坐在那里,格格不入。当人试图去表达最脆弱的情感的时候,会非常依赖自己的母语,但在这里,甚至没有人听得懂我说什么,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无助极了。”
“我蹲在地铁出口,嚎啕大哭,那是冬天最冷的时候,手脚很快没了知觉,身后不断有人经过,大家穿着厚实暖和的衣服,却没有人停下问我一句你还好吗?后来在我的印象里,伦敦一直是一个很繁华但是也很无情的地方。后来哭了一个多小时,才想起来我还有论文没写,赶紧一咕噜爬起来擦了眼泪往家里赶。”

“一屋子向死而生的悲壮气魄”
圣诞的时候,叶子青把自己关在宿舍里没日没夜地写论文——日本老师的论文,“有很多谱子要看,奏折一样,摊开就是一间房间那么长。”
她的朋友来她家,推门发现走不进去,一地全是书,她就这么埋在书里,一屋子向死而生的悲壮气魄,“我当时甚至做好准备,如果我都这样了还挂科,我就去伦敦的议会起诉这个日本老师。”
意想不到的是,那门课的成绩出来以后,她的论文是最高分,比那些欧洲人还要高,“我对着成绩反复确认了好几次,名字真的是我,才长吁一口气。”
几个月后,在学校走廊,她又遇上那个日本老师,老师犹疑了片刻,还是上来和她寒暄,到临走了,日本老师又拍了她一下,说了一句,“你们中国人还是不错的。”
“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在伦敦的第二次嚎啕大哭憋回去。”

“同样,你也不是你的学位”
2015年,叶子青顺利拿到了谢菲尔德大学人种音乐学博士的入学通知。
在她申请博士的那段时间,类似女生读了博士就嫁不出了”的话几乎每天都能听到,甚至当她参加伯明翰大学的视频面试时,导师也饶有兴致地问她,“听说在你们国家,女博士是特别被歧视的群体,你为什么还要读博呢?”
在她看来,用标签去定义一个人是很蠢的行为。“你不是你钱包里的钱,不是你开的车,不是你住的房子,不是你买的家具,不是你穿的衣服。同样,你也不是你的学位。”
每天七点半自然醒,下楼散步,然后上课,晚上吃完晚饭拉拉琴,周末会去地铁大概四十分钟的一所学校,教小BBC们学汉语。这就是一个留洋女博士的全部生活,没有了硕士那年的跌宕波折,
架构平静而稳定。

“一切也不可能会更好了”
今年我再和她聊起近况的时候,知道她碰上了一个很好的机会,离“回来”只有一步之遥了,“福州一所高校的人文学院,对,当老师。”
“我最近一直在想,如果再把过去的日子重来一次,一切也不可能会更好了,因为我已经做到极致了。”从福州到伦敦再到谢菲尔德,再到福州,她始终让生活按部就班地循着她划出的轨道前进,每一步都有的放矢。
“我从来不觉得念书浪费了我的青春,不断地念书才让我打开了更大的世界——不过,最后还是要回来的。”
我能理解少小离家时对“回家”的孜孜以求,就像每一对热恋中的爱侣总会给对方的山盟海誓,彼时彼刻的真情实感,未必就能天长地久,多年以后回忆起来可能只有对年少轻狂的哂笑而已。但我那时候不理解,为什么当一个人感受过凌云踏海的壮阔,还愿意再回到小桥流水的旧城——她告诉我说,家的感觉是无可取代的。
出走半生仍愿归来,是因为归处有牵挂;渐入乱花初衷未改,是因为她比谁都知道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
一个她登了岸,数以千百计的他们正朔流而上,有的人会回来,有的人最终不会。当十年二十年以后,你看到有些他们生活在出生的地方,好像什么改变也不曾发生,但他们找寻“回来”的路时各自不同的故事,其实是这个城市灯火阑珊下最美好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