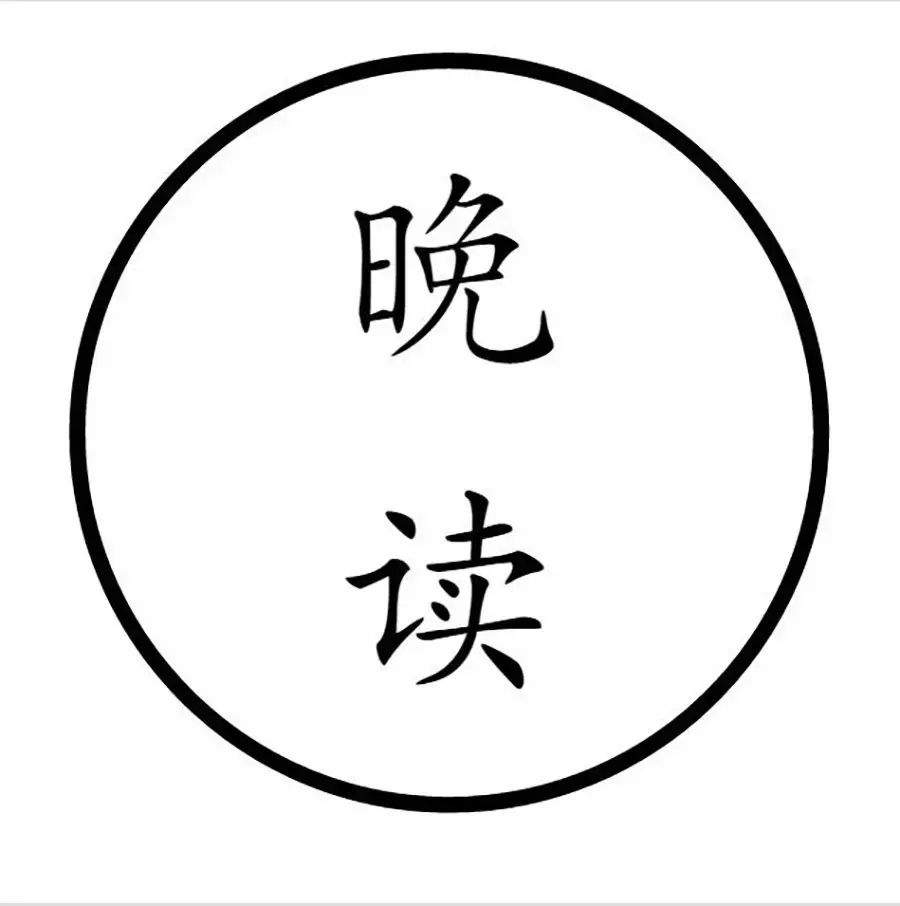北方有一句俗语叫“麦稍黄,女瞧娘”,大意就是在芒种前后、端午佳节将至时,出嫁的姑娘要回娘家看看。小时候最喜欢吃端午节才有的美食—绿豆糕。可转念一想,我这个外嫁十五年有余的姑娘,好像一次都不曾在端午回乡过。于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成形了。
来回差不多一周的回乡之旅结束了,时间真的很短,过得飞快,我还没有吃够老家的杏子,还没有品尝完家乡的美食,还没逛遍熟悉的街头巷尾……
家乡的变化太大,我还没仔细深入地熟悉,就如一个异乡过客一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想起我一直以来给自己的定义,一颗在世间随意漂浮的浮萍,一簇随处都能扎根生长的野草,一根随风飘荡的羽毛……可能因为家庭的关系,加上自身性格的原因,我总是觉得自己是这热闹世间的一个孤独漂泊的游荡侠,所有的喧闹、幸福都与我无关,我只是一个静静的看客。
到家的那个傍晚,我走出家门口,街道不再是尘土飞扬,家家户户都是结实整齐的楼房,可是每一户的漆红大门都紧闭着,街道上也空无一人。想起小时候,我们这一个巷子每家至少两个孩子,短短的街巷就有一二十个孩子,每天都是热热闹闹,我小时候从来没想过安静一会,好像每天都有释放不完的精力。不管是女孩子玩的跳皮筋、踢毽子、丢沙包……亦或是男孩子玩的爬树、打弹弓、翻墙……我通通不在话下,我好像是个假小子,对什么事情都好奇,又天生自带一股子不服输的倔劲,活泼好动,一刻不得闲,也常常挨揍。思绪到这时,我看到了对面车窗里映出我的身影,颀长有些偏瘦的身形,还算端庄秀丽的面容,真的很难跟我印象中的自己联系在一起,我难为情地笑了。听到一声开门声,隔壁的隔壁家婶婶出来在自家门口低头拔草,我大步走上前想问候她,我说婶婶,你知道我是谁吗?她都没抬头看我一眼就准确喊出我的名字,问我是什么时候到家的。我一边惊喜一边感慨,真不愧是几十年的老邻居,即便是听声,或是远远地望上一眼,就能准确地辨认出来。她老了,眼神不如以前清亮,行动也不如以前轻快。
第二天,我去了大姨家,舅舅家。大姨还是跟以前一样的大嗓门,思想固执,可能我们经常视频的原因,所以没有感觉到大姨身上明显的变化。只是,她在知道我回来后,早上七点多就给我打视频说做好了早餐让我去吃,我赖在床上说要睡懒觉,不高兴去吃,想吃什么会去县里下馆子,让她不要瞎操心,她就没再打来电话了。舅舅比以前话多了些,跟我们说人要多做善事,才会有福报之类的,舅妈一听他开腔就嫌弃地制止他,我说舅舅也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所以关注研究这些也是正常。说实话,舅舅大我还未超一轮,是我小时候的玩伴,在他众多外甥外甥女中,他应该最喜欢我,他从来没有批评过我,好像我做什么都是对的、好的。他说要给我烤肉吃,我以嫌麻烦为由拒绝了。的确,长到我这个年岁,看过了外面广阔的世界,品尝了各种美食珍馐,舅舅烤的烤肉,大姨烧的家常菜,已经无法激起我挑剔的口腹之欲。
除了老家的亲戚,有几个友谊存续了二十多年的朋友自然不能不见。我一直自认为很难和别人建立长久亲密的关系,事实也是如此,在异地,我没有一个亲密的朋友。在老家的几个朋友,说实话,平时很少联系,但是见面就分外亲切。有的放下工作,陪我玩,陪我聊天,让我倍感心安。葱花是特别热心和礼仪多,带我去网红店,点一大堆东西,知道我是一个人回来,立马就问,是不是吵架了?那种默契,那种知心,真的让我感动得想流泪。明明自己过得也很艰辛,可却为我的幸福祝福,为我的烦恼忧心。还有许久未见的高中同学,即便是将近二十年未见,一个消息发去,就定好了见面的地点,聊天时还是感觉她依然是二十年前那个开朗乐观的小美女,岁月永远无法在拥有着乐观善良的人身上留下痕迹。幸福的张太太自然无须赘述,她平和的语速,松弛的状态,已无形地昭示了她目前平静幸福的生活。憨态可掬的小儿子就是她快乐幸福的源泉,她是被全家人的爱包围着的小妇人,我同样祝福她。
回乡之旅虽然短暂,但是收获了很多,好像是给自己单调重复的日子按下了一个暂停键,在这短暂的暂停期,我放空自己,放任自己,让在异乡孤独的灵魂飘回到故乡,寻找一份安宁。
(佚名)